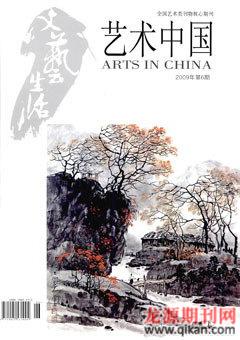我看文化和藝術的“雙棲人”阮榮春
錢海源
前些日子,上海大學藝術研究院院長阮榮春在電話中告訴我,他即將在北京中國美術館舉辦主題為“傳統與創造”的個人畫展,說是希望我能為他寫點東西。阮春榮是在當代中國美術界為我所敬重的眾多的人品好、學養水平高的有為的著名學者。他既在美術史論方面很有成就,又在山水畫創新方面頗有藝術建樹。經酌量,我想,文章的題目就叫做《我看文化和藝術的“雙棲人”阮榮春》好了。并且在文章的開頭,想先說幾句題外話。
前不久,老同學林墉兄在接受羊城晚報記者采訪時說:“我是越老越茫然!看了太多的書。才知道我自己有很多的害怕……別人是越來越覺得自己偉大,我則是越來越怕”,“有人稱呼我為大師,那是拿我開玩笑”。
林墉對羊城晚報記者所說的一番話,引發了我對一些問題的思考。
試看今日之中國美術界,真可謂是一個“人人為爭當大師”、而且是“互相攀比”的“大師滿天飛”的時代。如有人為了將自己自封為“超級大師”,而對前輩和與他同代老友橫加貶損;有些年紀輕輕的畫家,就忙著為自己籌建“藝術館”或“紀念館”;還有是某些畫家,雖然拿不出什么在全國有影響的作品,可是卻自我感覺特好。真可謂是“世界之大,無奇不有”。
我覺得林墉兄所說的“怕”,與古語所云“學而后知不足”是相吻合的,且很是耐人尋味。
林墉兄為了使自己不至于“再怕”,而特意刻了個圖章,叫“我怕”,并不斷地蓋,結果到處都是“我怕”、“我怕”。
在關于“怕”的問題上,我和林墉兄有著某種相似之處,也是“越老越感到茫然”。越老越感到在人類知識和文化的大海面前,自己是那樣的無知和幼稚可笑。為了克服“怕”的心理障礙,我除了認真向老前輩和同代業內老友學習以外,很樂意與美術界的年輕有為的學術精英們交朋友,以便從他們身上吸取有益的學養和新鮮經驗,以增添自己的朝氣,減少暮氣,不斷給自己“充電”。只有這樣做,才能跟上時代的步伐,不讓自己成為時代的落伍者。
阮榮春就是我這些年所結識的學術界眾多的年輕有為的朋友之一。要談到阮榮春是怎樣進入我的視野、成為我關注與看重的人物的過程,說起來是很有意思的。我與阮榮春是通過彼此的文章和美術作品互相認識的。我是他在許多著作和文章中所表達出來的我認為非常有學術水平的觀點的贊成者和擁護者,而阮先生也說他是我文章的知音。傳媒和通訊工具的發達,將相距千里之遙的我們很好地聯系在一起,使我們成為相交近兩年、卻至今未曾謀面的好朋友。在與比我年輕的阮榮春的交往之中,我從他身上學習和吸收了許多非常有益的學養。我對于阮榮春為振興中華文化和藝術所懷有的強烈責任感和使命感,深表敬意;我更對于阮榮春的學術眼光的敏銳,敢想、敢說和敢干的學術勇氣精神,深表敬意。我從阮榮春身上,看到了中國文化和藝術發展的希望。我慶幸人到老年,能結識眾多像阮榮春這樣年輕有為的著名學者和藝術家。
記得在20世紀60年代前期,我于廣州美術學院學習中國古代美術史的時候,著名美術史論家陳少豐先生,采用圖文并茂的方式給我們講授中國古代美術史,讓我們看到了自隋代展子虔初創的山水畫之后,唐宋元明清各朝各代杰出的山水畫大家所創作的藝術風格異采紛呈的山水畫名作。在20世紀80年代初,我有機會與多位畫家到敦煌莫高窟考察和臨摹一個多月,我不但臨摹了多件從隋到唐代的優秀雕塑。而且還臨摹了洞窟中的被頌揚為“古代繪畫史”上最早的山水畫《幻城喻品圖》等多幅壁畫精品。可是,這些年來,若將20世紀近百年來的山水畫作品與古代山水畫相作比較。就會感到在藝術風格和樣式方面的單調乏味。例如。我也認為黃賓虹的山水畫在筆墨方面確實好,有文氣和書卷氣。但我感到黃賓虹的山水畫作品幾乎張張的構圖和造景都差不多,有令人生厭的千篇一律的毛病。而更令人難于容忍的是,這些年來采用辦所謂“高研班”搞培訓的方式,大批量地“克隆黃賓虹”,大有使整個中國山水畫界由“黃賓虹模式”獨占鰲頭的架式。可是,中國山水畫界為何會出現這種怪現象以及山水畫界存在的問題癥結究竟在何方?作為山水畫門外漢的我,無法說得清楚的。我企盼會有個高人,能站出來化解中國山水畫界所存在的令我感到困惑的癥結問題。
兩年前,這個高人終于出現了。
在20世紀80年代,南京藝術學院德高望重的當代中國著名美術史論家林樹中教授的高足、90年代后又畢業于日本早稻田大學的文學博士阮榮春,就是我心目中所企盼出現的高人。阮榮春不但在美術史論方面已出版了《沈周研究》、《佛院世界》、《中華民國美術史》、《佛教南傳之路》、《絲綢之路與石窟藝術》、《中國美術史》、《中國美術考古學學史綱》、《中國近現代美術史》和《中國繪畫通論等》多部在國內外學術界產生了廣泛影響的有學術質量的著作;而且在這些年來他將中國近現代美術史作為主要研究方向,發表了在美術史論界反響熱烈的如《西洋畫的引進與西方繪畫藝術在中國的傳播》、《三足鼎峙的民初畫壇》和《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美術教育》等許多優秀論文。并在花鳥畫和人物畫,特別是在山水畫創作方面也頗有成就,是一位名符其實的優秀的學者型的山水畫家。
與這些年來中國山水畫界所流行的令人感到厭惡和倒胃口的“濃重粗野,荒寒冷寞,或邋遢,草率孤僻,造景千篇一律,在藝術上以炒現飯的重復性、陳陳相因”的模式化山水畫相作比較,我認為,阮榮春的山水畫在蒼莽雄健之中,蘊含著恬靜秀逸之美,在典雅和清遠之中,彰顯了大氣磅礴的胸襟和情懷,畫面在筆墨的點劃涂抹與色彩的渲染之間,以及在苦心營構畫面的設景造境中,往往收到了意料之外與情理之中的藝術妙趣,使他的山水畫作中的詩情與畫意相得益彰。我的一位山水畫家朋友,用贊嘆的口吻點評阮榮春的山水畫:“有五代荊浩和關仝的‘老辣蒼勁和‘崇高峻厚,有北宋范寬和巨然畫風的‘氣勢磅礴與‘秀潤清爽,以及元四家的‘蒼茫空靈、明四家的‘典雅閑趣藝術韻律之美。”并與我深有同感地說:“在當代中國山水畫界彌漫著”濃重粗野與草率簡略一邊倒的令人感到沉悶和單調乏味的畫風濁浪中,阮榮春的個性鮮明和富有創新精神的‘阮體山水畫,如一股春風那樣令人感到精神為之振奮。”
我覺得更難能可貴的是,有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文化的使命感、在山水畫創新方面取得了給人以耳目一新的阮榮春,以大無畏的學術勇氣,站出來解析中國山水畫界長期困擾人的問題的癥結,發表了題為《20世紀中國山水畫的歷史定位及畫風趨向》的重要文章。阮榮春在文章中尖銳地指出,“20世紀中國山水畫是一個低潮時期,這一時期的山水畫大師……或缺乏造景能力、千篇一律,或粗率簡略、一法蓋全;或有墨無筆,線條贏弱,是矮子里的將軍”。此語一出,在中國美術界內外產生了“一石激起千層浪”的強烈反響。如有媒體說阮榮春這是在“炮轟”那些在學術界業已蓋棺定論的山水畫大師,還有學者責罵阮榮春是“歷史的罪人”。其實,我讀阮榮春文章的感受
是,阮榮春并無否定20世紀山水畫大師的意思。他作為一位有責任感和使命感的美術史論家,作為一位長期致力于山水畫創作、在藝術上有想法有追求有成就的優秀山水畫家,在涉及至0對20世紀中國山水畫歷史和當代中國山水畫的現狀的問題,為了有利于促進山水畫發展的目的從學術層面談了一些不同意見而已。我認為,這并沒有什么不好。同時,我覺得這也是作為一個嚴肅學者的阮榮春所應當擁有的正當學術權利,理應受到尊重才是。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說得更遠一點是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在對待文化和藝術的問題上,我們總是在按照提倡一種“傾向”去壓倒另一種“傾向”的思維模式和領導方法去進行運作。例如,在20世紀50和60年代,美術界為了提倡“蘇式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而強求一切都必須按照“蘇式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模式去套。當時為了提倡符合“蘇式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革新中國畫”原則,竟然要求國畫家們都必須老老實實地“接受改造”,去畫素描和石膏像。學術批判的矛盾則是直指“四王”。在當時誰若要提出不同意見,就有可能被扣上“反蘇”和“右派”的帽子。所以,當今如果有人認為阮榮春對20世紀的中國山水畫提出異議是“犯了忌”的話,難道不就是在重犯20世紀50和60年代曾經出現過的那種極不正常的在學術上也搞“蘇派一邊倒”的有害傾向嗎?
在活躍而又混亂的中國當代美術界,由于受商品經濟的沖擊,某些畫家的一門心思不是放在追求文化藝術上,不是放在提高文化素養上,不是放在對藝術本體的追求上,而是將時間大量花費在如何弄錢、做“畫外功夫”之上。例如,據說南方某省會中等城市,近年來“如雨后春筍”般地冒出了二十多個新成立的、名字起得一個比一個好聽和響亮的“書畫院”和“藝術研究院”。欲問為何會出現這種令人稱奇的怪現象,這是因為某些畫家認為,只要擁有了“院長”或“副院長”的官銜,其畫作便可以提高價格。還有不少畫家只重視技術,而忽視文化和藝術素養的提高。
針對當代中國美術界的現狀,阮榮春在他發表的《我的審美取向》一文中,明確提出了“三氣”標準,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在當代中國畫壇,應該弘揚“正氣、文氣與靜氣”。按照我的理解,阮榮春所說的“正氣”,即如文天祥所言的天地之間的正氣,主張在畫壇要樹立正氣,主張畫家做人要有正氣,并要采取措施剎住中國畫壇的歪風邪氣;阮榮春所說的“文氣”,即主張畫家要注重提高自身的文化藝術修養,才能提高作品的藝術品位和文化含量,而不至于使作品停留于只有繪畫技術層面的匠氣或粗野之氣;阮榮春所言之“靜氣”,是主張畫家心態要好,要心氣平和,畫家要甘于寂寞,要耐得住寂寞,切不可以有浮躁之氣。我認為阮榮春提出的“三氣”標準,有助于中國畫壇糾歪風、樹正氣。我覺得觀賞阮榮春的山水畫佳作,正表明他正是按自己所提出的“三氣”理論主張去從事藝術創作的。他將凜然浩蕩之氣勢與精微細膩之筆墨相結合,將寫景造境與抒情達意相融匯,把中國傳統山水畫的造景與構圖形式,與西方繪畫中所強調的營造畫面的空間表達方式相糅合,將南方的秀潤與北方的偉岸相協調。創造出了一種屬于阮榮春的個性鮮明的阮體山水畫藝術風格。觀賞阮榮春的山水畫,能讓欣賞者享受到一種清新、典雅、充實、悅意、雄壯與曠達之美。
常言道:“有比較才能鑒別。”俗話又說“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如果將阮榮春的山水畫與中國歷代的山水畫佳作相作比較地進行解讀,和近一百年中所產生的山水畫進行對照和分析,特別是和這些年來所流行的粗率簡略和有墨無筆的山水畫去細心對比研究的話,就不能不承認阮榮春在山水畫創新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了。我認為,有著開闊的藝術視野、既對中國和東方深厚的文化藝術傳統深有研究、又對西方現代藝術流向了如指掌的海歸派阮榮春,從其山水畫作中既能看到他對中國古代優秀傳統山水畫藝術的文化精神和技術層面的繼承,又有屬于他自己的藝術創新貢獻。這也是為什么他的山水畫作品與當今流行的山水畫、能夠在藝術上完全拉開距離和層次的原因所在,阮榮春的山水畫藝術風格可以簡明扼要地用“秀美、典雅、清新、大氣雄渾”十個字來概括。阮榮春的山水畫體現了今日之祖國山河的秀麗和壯美、泱泱大國的精神風范,富有鮮明的時代特征。阮榮春的創新山水畫,有高品位和深厚的文化含量。
阮榮春提出的“三氣”理論,得到了學術界不少著名專家學者的認同與支持。這些年來,業內同行們經常議論,當代中國美術界的文化素養越來越差,從美術院校一屆一屆畢業出來的青年畫家的文化素養,只相當于文理工科大學畢業生的一半。每年大量生產出來的美術作品,整體的文化含量很低,精品力作不多。所以,素來以不怕得罪人、敢于講真話著稱的林墉兄,在接受羊城晚報記者采訪時尖銳指出:“廣東畫壇最大的問題是沒有文化!”有位老前輩說:繪畫或雕塑的技術,只要肯下功夫,三五年就可以解決問題,但一輩子能否在藝術上出精品和力作,關鍵是看藝術家自身的整體文化藝術素養、文史哲的水平是否高。
阮榮春正當盛年,我相信他會以不久在中國美術館舉辦個展的成功,作為其在文化研究和藝術創作的新的起點,在未來取得更加輝煌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