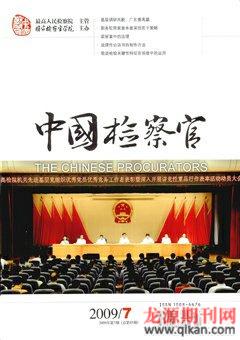論公然以平和方式取財行為的性質
沈 琪
根據刑法理論通說,盜竊是秘密竊取他人財物的行為;搶奪是公然奪取他人財物的行為。前者作為一種秘密的取財行為,其行為手段必然是平和的(即行為人不使用暴力脅迫手段),因為秘密與暴力本身是相對的;而后者作為一種公然的取財行為,其行為手段往往會表現出一定的強力性質,如趁被害人不備突然奪走其手中的提包。秘密與平和、公然與強力,是一般情況下兩種行為所具有的并據此相互區分的重要特征。但是,在現實的侵犯財產犯罪中,除了秘密平和和公然強力這兩種常見的行為類型之外,還存在第三種行為類型,即公然平和。
案例一:胡某、李某等人結成團伙準備大肆盜竊摩托車,他們租用一輛貨車,開到本市某小區的一停車棚內,一次“裝走”摩托車三輛。當時停車棚前面的長椅上坐著幾位小區居民在曬太陽,以為胡某等人是運走自己的車而未予制止。直到傍晚失主前來取車,才發現車子丟失。
案例二:張某為無業人員,某日潛入王某的新婚房內,撬開房內的抽屜、箱子等翻找財物。王某之母趙某聽見響聲,用鑰匙打開房門,見張某正在翻箱倒柜。趙某考慮到自己年邁,家舍無鄰,既沒有喊人捉賊也沒有采取其他措施對張某的行為予以制止,只是在一旁央求張某不要拿走自己兒子的東西。張某對趙某的突然出現,起初感到驚訝和恐慌,但當他發現趙某年邁體弱,一人在家,且家無鄰舍后,對趙某的央求毫不理睬,旁若無人地繼續翻箱倒柜,最后拿走現金5000元。
在兩例中,行為人都是當著他人的面公然取得財物,而且都沒有采用暴力脅迫方式,而是采用平和方式取得財物。那么,對于這種公然地以平和手段取得他人財物的行為該如何定性呢?
通過比較可發現,盡管兩例中的行為人都是公然以平和手段取得他人財物,但兩者存在一個重要區別,即案例一中的行為人是當著財物占有者之外的人的面取得財物,而案例二中的行為人是當著財物占有者的面取得財物。對于案例一中的行為,根據理論通說應當構成盜竊罪。通說認為,盜竊罪雖然必須具有秘密性,但盜竊罪的秘密并不是不為任何人知悉的絕對秘密,而是具有針對性,即是相對于財物的所有者、保管者而言,而并非對所有其他非同伙人而言的,如果行為人在竊取財物時為被害人以外的其他人發覺,但仍趁被害人未察覺而將財物取走,仍然是盜竊行為。[1]案例一中胡某、李某等人雖然是當著小區居民的面公然“裝走”摩托車,但小區居民并不是摩托車的所有者或保管者,而摩托車主人在摩托車被裝走時并未察覺,因此,胡某、李某等人的行為對財物的所有者來說具有秘密性,根據通說應當構成盜竊罪。對此,刑法理論和司法實務均沒有異議。
而對于案例二中的行為性質,理論上存在不同觀點。根據通說的觀點,案例二中張某的行為顯然不構成盜竊罪,因為張某的行為就連對財物占有者來說都不具有秘密性,根本不符合盜竊行為的“秘密”要件。一般認為,象這類行為應當構成搶奪罪,認為在這種情況下,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搶奪的故意,客觀實施的是公然奪取財物但并未侵犯他人人身權利的行為,完全符合搶奪罪的犯罪構成。[2]但反對通說的觀點卻認為,案例二中的行為應當構成盜竊罪而不是搶奪罪。因為,只有以對物暴力的方式強奪他人緊密占有的財物,具有致人傷亡可能性的行為,才構成搶奪罪,如果行為人僅僅采取平和的手段,違反被害人的意志,將財物轉移為自己或第三人占有,應當構成盜竊罪。[3]盜竊行為不應僅僅局限于“秘密竊取”,“竊取并不一定要求是秘密取走,只要行為人沒有使用暴力、脅迫手段而取走財物,就可以認為是竊取。”[4]另有學者也指出:“在未對財物施以暴力的情況下,行為人的行為并不符合搶奪罪‘對物暴力的本質特征,因而只能認定為盜竊罪,倘若定搶奪罪則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則的精神。”[5]
顯然,對于案例二中的行為性質,產生不同判斷的根本原因在于對盜竊罪和搶奪罪的構成要件存在不同認識。對此,本文的主張是,“秘密性”應當是盜竊罪的必要要件,公然性是搶奪罪區別于盜竊罪的根本特征,當著財物占有者的面公然以平和方式公取財的行為應當構成搶奪罪。
首先,正如持反對觀點的學者所承認的,“將盜竊限定為秘密竊取,是一種相當自然的文理解釋。”[6]刑法解釋應當堅持嚴格解釋原則,文理解釋應當在所有解釋方法中具有絕對的優先性,如果文理解釋的結論合理,就沒有必要采取其他論理解釋方法。把盜竊罪解釋為一種秘密竊取行為,是合理的文理解釋,其合理性就在于這種解釋符合國民對盜竊行為的普遍理解。“盜竊”這個詞,并不是一個特殊的規范用語,而是一個普通的日常用語,對法律規范中普通用語含義的闡釋應當最大限度地尊重國民的普遍理解。在漢語使用習慣中,盜竊自古以來就被認為是一種秘密竊取行為。中國古代刑法將盜竊稱為“竊盜”,和“強盜”共同作為“盜”的兩種行為方式,兩者的根本區別在于強盜是一種強取或公取財物的行為,相當于現代刑法中的搶劫,而“竊盜”則是一種竊取或秘取的行為。[7]繼承了古代刑法“竊盜”本義之精髓。現代刑法理論也一直將盜竊解釋為一種秘密竊取財物的行為。盜竊是一種秘密竊取行為,這種理解可謂深深地扎根于中國民眾的意識之中。筆者曾經就類似上述第二個案例中的行為應當構成何罪提問不同的人群,其中包括非法律人士、法律人士和法學院的在讀學生,得到的答案是,除了極個別人認為有可能構成盜竊罪之外,大多數人都認為應當構成搶奪罪。當被問及為何不構成盜竊罪時,所有人都回答因為這種行為不具有秘密性,而盜竊是一種秘密性行為。足見,在中國國民心目中,盜竊理所當然地是一種秘密竊取行為。對法律條文中的普通用語,國民的普遍理解應當是法律理論解釋其含義的智識基礎,“對刑法中普通用語的解釋,必須按照其普通意義進行解釋。”[8]
從侵犯財產犯罪的立法體例來看,我國刑法中的盜竊罪也應當被理解為是一種秘密的竊取行為。在德國、日本等國,刑法理論和審判實踐不要求盜竊罪具有秘密性,但這是和這些國家刑法對侵犯財產犯罪的立法體例有關的。德日等國刑法并沒有規定搶奪罪,而對公然以平和方式取財的行為又不可能以法無明文規定為由宣告無罪,在這種情況下,相對于將其認定為搶劫罪或詐騙罪等罪而言,排除盜竊罪的秘密性要件從而將這種行為認定為盜竊罪更具有可接受性。只有這樣,才能使盜竊罪具有更大的涵攝力從而實現對財產犯罪處罰的周延性。和德日等國刑法不同,我國刑法除了規定盜竊罪、搶劫罪等典型的侵犯財產罪之外,還單設了搶奪罪。從行為性質來看,盜竊、搶奪、搶劫同屬于違背被害人意志獲取財物的行為。從行為方式來劃分,所有違背被害人意志獲取財物的行為大致可以有以下四種組合:秘密-平和、公然-對人暴力、公然-對物暴力、公然-平和。其中,以秘密方式平和獲取他人財物無疑是盜竊罪所要處罰的行為類型,以公然對人實施暴力方式獲取他人財物是搶劫罪所要處罰的行為類型。問題是其余的兩種行為類型——公然以對物實施暴力方式獲取財物和公然以平和方式獲取財物——該如何歸類。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根據傳統理解,這兩種行為類型均不符合盜竊罪、搶劫罪抑或是詐騙罪等的構成要件。在這種情況下,刑法單獨設立一個罪名來處罰這兩種行為才是最為可行的做法。所以說,我國刑法之所以要單設搶奪罪,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在維護盜竊罪之秘密性要件的前提下不失對侵犯財產犯罪行為之處罰的周延性。現行俄羅斯刑法也在規定了搶奪罪的前提下,把盜竊罪限定為“秘密竊取他人財產的行為”,[9]堅持了盜竊罪的秘密性要件。可見,在刑事立法上規定或在刑法理論上解釋盜竊罪的手段時,要充分考慮到盜竊罪與其他財產犯罪尤其是與搶奪罪的關系問題。中國和俄羅斯刑法典中規定有搶奪罪,因而在考慮盜竊罪的手段時,就應考慮到盜竊罪與搶奪罪在犯罪手段上的聯系與區別。盜竊與搶奪的共同特征在于行為人取得財物都違背了被害人的意志,并且都未對被害人使用暴力或脅迫,而兩者的本質區別在于盜竊手段具有“秘密性”特征,而搶奪罪的手段不具有這種特征。
“各種搶奪行為必須‘公然發生。搶奪罪之所以可以單獨成立一個罪名,就在于其行為具有‘公然的特征。”[10]“公然”意味著行為人是當著被害人的面違背被害人意志強行解除被害人對財物的現時占有,它雖然沒有達到搶劫罪的傷害人身的程度,但相對于盜竊罪的“秘密性”而言,“公然”體現了行為人對現有財產權和社會秩序的更為惡劣的藐視態度,也體現了搶奪行為對社會更為嚴重的危害性,從而為搶奪行為獨立成罪奠定了客觀基礎,民眾也由此才產生對此種取財行為獨特的否定評價。正如俄羅斯刑法學者指出的那樣:“公開的、明目張膽的、周圍人一目了然的因而是非常粗暴的使財產脫離他人占有的方式是搶奪罪最突出的特點,是它的獨特之處。……這使他所實施的違法行為的危險性大為增加,同時加重了對其違法行為否定性的道德評價。”[11]
從上文的分析可知,搶奪包括公然以對物實施暴力方式和公然以平和方式獲取他人財物這兩種行為類型。對公然以對物實施暴力方式取得財物的行為構成搶奪罪,理論上不存在爭議,存在爭議的是公然以平和方式獲取財物的行為。筆者主張這種行為應當構成搶奪罪而不是盜竊罪,理由除了上文所述的盜竊罪應當具備“秘密性”要件之外,還在于以下事實:在這種情況下,行為人取得財物的手段雖屬平和,但卻是當著被害人的面違背被害人意志強行解除被害人對財物的現時占有,這種行為和公然以對物實施暴力方式取得財物的行為在本質上并無區別。因為,在后種行為類型中,行為人雖然是通過對物實施暴力方式獲取財物,但對物實施的“暴力”和搶劫罪中對人實施的“暴力”性質不同。搶劫罪中對人實施的“暴力”必須具有對人身的傷害性、破壞性或毀滅性,從而壓制被害人的反抗;而搶奪罪中對物實施的“暴力”一般不會對財物具有破壞性或毀滅性,而僅僅是對保護財物的現時力量的解除。如趁被害人不注意將其手上的手機奪走,行為人的目的是獲得手機而不是破壞手機,其所實施的突然奪取手機的行為只是為了解除手機的現時保護力量并將其轉移為自己占有,而不是為了破壞手機本身。所以說,行為人盡管是通過對物暴力方式獲取財物,但并沒有因為其暴力手段而侵害新的法益。刑法之所以把這種行為單獨作為一種犯罪來處罰,不是因為其暴力手段侵害了新的法益從而有別于盜竊罪,而是因為行為的“公然性”所體現出來的獨特的客觀危害和主觀惡性。對搶奪罪而言,重要的不是行為是否含有對物暴力性質,而是行為是否具有公然性質。刑法規定搶奪罪,就是為了處罰以公然的方式對他人財物行使有形力并從而非法占有該財物的行為,而至于這種有形力是對物暴力還是平和,并不具有重要的規范意義。因此,公然以平和方式取得財物的行為和公然以對物實施暴力方式取得財物的行為在法本質層面上具有完全的統一性,應當共同作為搶奪的兩種行為類型。
注釋:
[1]參見王作富主編:《刑法分則實務研究(中)》(第三版),中國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第1090頁。
[2]參見韓玉勝主編:《刑法學原理與案例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555頁。
[3]參見張明楷:“盜竊與搶奪的界限”,載《法學家》2006年第2期。
[4]張明楷:《外國刑法綱要》,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96頁。
[5]魏償東、楊磊:“盜竊罪的展開——基于中國傳統刑法理論的反思”,載《政治與法律》2008年第12期。
[6]張明楷:“盜竊與搶奪的界限”,載《法學家》2006年第2期。
[7]參見蔡樞衡:《中國刑法史》,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頁。
[8]張明楷:《刑法分則的解釋原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52頁。
[9]參見趙薇:《俄羅斯聯邦刑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36頁。
[10]王飛躍、李平:“搶奪罪客觀要件論”,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06年第4期。
[11][俄]斯庫拉托夫、列別捷夫主編:《俄羅斯聯邦刑法典釋義》,黃道秀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42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