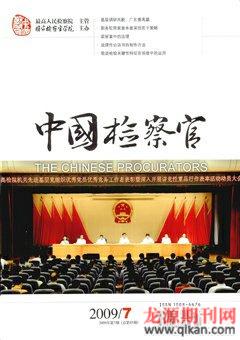梁麗給誰出了個難題
熊 智
參加完《中國檢察官》雜志社舉辦的“梁麗案”研討后,我陷入一種深深的思索始終沒能釋懷。也許,梁麗案真的給法界出了道難題。
既然,更多的認(rèn)識基于本案件所觸及到某種社會公德及公共秩序而判定梁麗的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繼而需要用刑罰處罰的形式予以警示后世。我想,這也許符合法哲學(xué)的某些功能性價值判斷,特別是當(dāng)人人都會恐懼“黃金門”行為可能被復(fù)制而泛濫成災(zāi),最終必然影響到公共價值的時候,法律的社會功能、預(yù)防與矯正價值似乎應(yīng)當(dāng)前傾。但是,或許人人都懈怠于對遺棄物的積極作為,甚至漠視,進(jìn)而導(dǎo)致社會有效資源被刻意置之狼藉的處境時,我們是否還應(yīng)當(dāng)思考法律本身能做些什么?抑或法律既有規(guī)范能調(diào)和些什么?是否可以思考法外評價的某些功能,避免讓法律萬能化。我們在重塑或維護(hù)一種價值觀的時候,遴選或確認(rèn)善惡是我們必須經(jīng)歷的內(nèi)心刺痛,處理本案也不例外。那么,我們作為法律人以哪一種精神作為價值判斷就顯得極為重要了。
如果我們確實看到距離法律核心價值的天國還存在空間,而又不能因為等待怠慢了民意或公德所需要法律的現(xiàn)實功效,我愿意選擇梁麗之行為的確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認(rèn)識,傾向去強(qiáng)調(diào)法律的另一種價值,即警示與教育價值。所以,科以其較之盜竊罪更輕的侵占罪,甚至,如與會專家提出作微罪不訴或免予刑罰處罰的懲戒,也不失為一種法律智慧的特別體現(xiàn)。然而,我所擔(dān)憂的是,公權(quán)力介入到當(dāng)前的程序時期,這樣的法律智慧真能解決本案件所存在的司法技術(shù)問題嗎?
梁麗一案到底如何定罪呢?以當(dāng)下涉嫌構(gòu)成盜竊罪為據(jù),兼以寬嚴(yán)相濟(jì)的刑事政策,予以減輕或免除處罰,似乎于理于社會都有個交代,還能為后世例為戒碑。
但是,盜竊行為作為一種結(jié)果性犯罪,竊取高達(dá)300萬元人民的特別巨大公私財物,并構(gòu)成既遂事實,在刑法上已經(jīng)屬于情節(jié)特別嚴(yán)重情形,就算是科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也不為過。那么,我們憑借什么對其法外開恩呢!難道僅僅就憑“寬嚴(yán)相濟(jì)”的四字罰則再加上一個慣常的自由裁量?顯然,這樣做是有問題的,至少現(xiàn)行刑法規(guī)定沒有給出這樣的參照依據(jù)。這樣一來,豈不是以犧牲現(xiàn)行法治原則為前提去換取區(qū)區(qū)一個個案的平息結(jié)果?如果真是這樣,法的精神無疑再一次遭受踐踏,其對法律的破壞程度比起判處梁麗無期徒刑更可怕。
那么,若判定梁麗構(gòu)成侵占罪,擬請檢察機(jī)關(guān)啟動微罪不訴或由法院作出有罪不罰的裁判,也許也能達(dá)到息事寧人之功效。
可是,侵占罪在現(xiàn)行刑法里被確立為親告罪。也就是說,公權(quán)力中的偵查與公訴均不宜出現(xiàn)在這個罪名里。從刑事法理論上講,一般侵占罪是到不了檢察機(jī)關(guān)這個程序的,那就不存在微罪不訴的問題。那么,是否可以尋求法院有罪不罰的司法救濟(jì)呢?顯然,也不可能。作為刑事自訴一方是否會向法院提起訴訟,我們是無法把控的,總不至于為了達(dá)到懲罰梁麗之目的,去鼓動所謂的受害人上法院起訴她吧。刑法既然將該罪名確立為親告罪范疇,目的就是給當(dāng)事人足夠的自由分配訴權(quán)的權(quán)利,這樣的設(shè)置,既符合當(dāng)下和諧精要又符合司法經(jīng)濟(jì)的原理。
也許,前述二罪都走不下去了,最后就只有“放人”!簡單兩個字,卻是很難做到的。這樣的決定需要司法機(jī)關(guān)莫大的勇氣和胸懷。再說,前后落差的驟然出現(xiàn),對已經(jīng)實施的公權(quán)力無疑是一個強(qiáng)烈的沖擊。人放了,或許民心得到安撫了,但公權(quán)力卻因草率遭到貶損。
在這樣的進(jìn)退兩難之下,使我們突然又寄希望于要是事態(tài)還在當(dāng)初該有多好!要是在當(dāng)初,我們將有足夠的時間和智慧來把握本案件各方的前途。
然而,問題也許就出在當(dāng)初。我們一直有個大大的疑團(tuán),作為設(shè)置在一個特定環(huán)境下的機(jī)場公安派出所,在有嚴(yán)密又完善的監(jiān)控設(shè)施之下,第一時間為何不鼓勵那個“拾金而昧”的梁麗交還財物呢?為什么要放任其自由控制、處置涉案財物長達(dá)一天呢?甚至于后來還欲擒故縱地一直追蹤到其下班,繼而前后十幾分鐘之差入室責(zé)令“盜竊嫌疑人”交還物品。從深圳機(jī)場完善的科學(xué)的監(jiān)控設(shè)施來看,這個“盜竊嫌疑人”從一開始都能被監(jiān)控并被跟蹤。我們不解的是,偵查機(jī)關(guān)把案件引導(dǎo)至今天的情形到底有什么社會價值?還是有更大的司法價值呢?
不管怎樣,公安機(jī)關(guān)既然這樣去行使賦予他手中的公共職權(quán),一定是有他的價值追求的。但是,我們想知道這個價值到底體現(xiàn)為什么樣的價值,是以最快、最便捷、最安全的方式保護(hù)受害人財產(chǎn)為價值前提呢?還是這本身就一種偵查常態(tài)?抑或,“盜竊嫌疑人”已是甕中之鱉,逐之捉之也有一種成就和快感!
沉思本身就是一種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