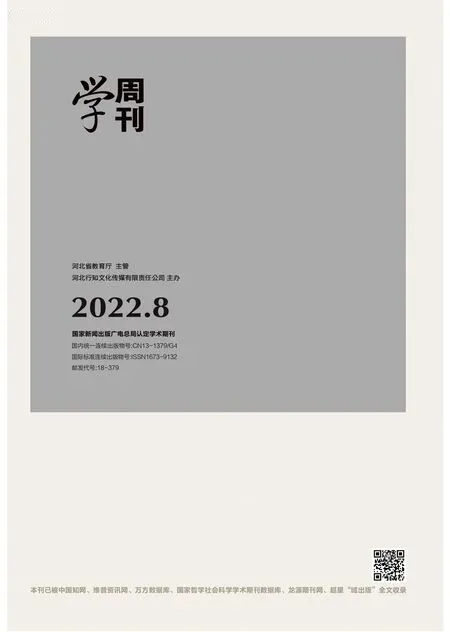當前語境下中國美術發展的失語
劉 勇
中西美學發展中的一個顯著的區別就是西方是偏重于再現的藝術而中國則偏重于表現,偏重于再現的更重于對事物的模仿而形成物本的藝術,偏重于表現的更傾向于對創作者內心感情的表達而追求人本的藝術,物本的藝術強調真實而重視實證,人本的藝術強調內心的灑脫注重“取以像外,得其環中”。中國是一個擁有上千年文化底蘊的文明古國,在中國上千年的發展中曾經創造過輝煌的文明,使中國一度處于文化的中心地位,但是鴉片戰爭的一聲炮響打擊了中國自以為是的傳統思想,我們不得不承認的是,中國的文化,中國的藝術發展就在此時起,開始慢慢地走向失語。在西方出現了具有靈感的創作者的創作群,而中國并不缺少具有靈感的藝術家,但中國缺少靈感的創作環境。在以再現主義為基調的物本和以表現主義為生命力的人本被認為是缺少了靈性之后,以靈感為基調的能本藝術融合兩者之所長,逐漸為先鋒藝術家們所掌握,但在中國20世紀藝術發展的經歷來看,卻只是曇花一現而已。
20世紀的中國藝術的發展,先以繪畫為例。“繪畫造型的‘寫實觀,在世紀初棄舊求新的浪潮中,成為一個在藝術形式上和思想觀念上最直觀的變革切入點。著名美學理論家孔新苗先生認為,20世紀以前中西美術的交流與融合是一種自發性活動,中國古典美術從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的轉變,使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從文化意識形態的角度“將西畫的意識形態的特征,與西方近代以前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發展成果相聯系;將中國明、清文人畫的藝術形式特征,與中國相對落后的生產力水平和封建文化相比附。從這一角度出發,西畫的寫實特征及其造型手法,在中國熱心變革的知識分子眼中,就具有了遠遠超出它自身內涵的重大文化變革意義。拿西畫來改良中國畫是融合派畫家們的初衷,而代表西畫最高成就的應屬西方的油畫了,西方自其古希臘時期就主張寫實。中國畫主要是借鑒了西方的寫實傳統,但是中國畫家們在這種寫實的基礎上究竟發展了哪些東西呢?中國不乏有靈感的畫家,在六七十年代的時候,涌現出了一批極具想象力的繪畫者,雖然從技術上來說,他們的創作還未成熟,但是他們邁出了以西洋畫書寫內心感情的第一步,《初踏黃金路》、《毛主席去安源》、《做人要做這樣的人》等等作品以油畫的形式表現了內心的理想與愿望。筆者認為,中西結合到目前為止成功的就是這樣的兩類,一是類用油畫的形式表現內心,另一類是用西方的材料來重新創作中國畫并有所突破,他代表著兩類靈感的創作群體,而中國的油畫的寫實性并未超出西方古典,而是將西方流行過的東西再次引起中國人的興趣而已(只限于當代)。試看《山村小店》和《塔吉克姑娘》,除了表現的內容是國人以外,其余全部是西方的。我們借鑒了,但是沒有發展。中國畫是重寫意的,將寫實的東西加進寫意的內容應當是中國畫的一種出路。
是什么因素困擾著當代的藝術家們呢?也許是一個簡單的字就能概括清楚的:靜。著名學者徐復觀先生在他的論著《中國藝術精神》的自序中曾經提到“我國三百年來,因過分重視筆墨趣味,而忽視作品中所表現的人生意境,以至兩者皆墮退,尤以畫論方面的墮退為甚。當代名家中,只有白石老人,拈出一個‘靜字,為真能道出他的體驗所至,接觸到藝術中某一方面的真實。 “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的書畫傳統已經受到西方的沖擊是不值得懷疑的,也是需要改進的,但是“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的思想一定要遵守,我們不需要因循守舊的墨守成規,但是胸有成竹的大氣決不能丟,市場決定了一部分藝術作品的走向,但的確也需要非功利性的藝術作品的回歸,在物欲橫流的商品社會下,“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的超脫依舊重要,“一間茅屋負青山,老松半間我半間”的超遠更加珍貴。只有當我們認識到萬忙之中一點“靜”的時候,也許就是中國藝術開始尋求靈感的時候。中國不缺少靈感的藝術家,只是缺少靈感得以發揮的環境。徐復觀先生的話也許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定位,中國藝術真正缺少的是不斷探索的、充滿創造力的先鋒群體,只有他們的靈感,他們的創造力,他們所竭力創作的“能本”作品,才應當代表著中國藝術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