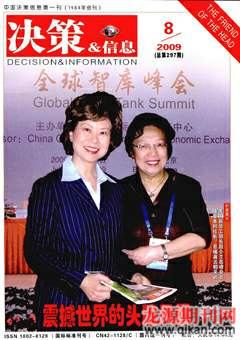智庫是跨越政治的溝通渠道
2009年3月,曾參與多個海外著名智庫發展的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受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下稱國經中心)理事長曾培炎親邀,成為了國經中心8名執行副理事長之一。
1997年開始,劉遵義任美國斯坦福大學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同時,還是斯坦福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和胡佛研究所名譽研究員。他研究的領域包括經濟學理論、應用微觀經濟學、計量經濟學、工業經濟和農業經濟等。

此外,他還是美國大學優等生榮譽學會會員,美國經濟學會、美國計量經濟學會、美國統計學會、美國農業經濟學會會員,美國收入和財富研究討論會成員,英國劍橋大學丘吉爾學院海外成員,美國古根海姆紀念基金會理事,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理事。
劉遵義在國際、政府機構和商業界擔任過許多職務。曾是美國能源部、美國聯邦儲備金監察小組、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蘭德(RAND)公司、聯合國計劃開發署、美國花旗銀行、中國銀行和其他大量公共和私人機構的顧問,同時還是美國加州政府經濟政策咨詢委員會成員。
近十多年來,劉遵義在中國參加了大量的學術活動,并同政府機構有廣泛的合作關系。
記者:您曾長期參與海外智庫的工作,您認為,智庫對經濟發展能夠起到哪些作用?您怎么看國經中心的定位?
劉遵義:第一,智庫應該更多考慮中長期規劃,很多政策要有長遠規劃。我想智庫可以擔負這樣的工作,因為它沒有常規行政工作;第二,在國外,智庫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可以很多元化。在美國,觀念異彩紛呈,有的保守,有的開明,有的贊成自由貿易,有的贊成保護主義,很多元化。從不同的角度和意識形態出發,大家都有自己的研究。
在中國,建立國經中心這樣大規模的智庫還是第一次。這個智庫定位在民間組織,有一定自由度,比較靈活和開放。能夠從不同的角度,跳出政府的圈子考慮問題。
智庫在中國的另外一個重要作用是,現在全球化的發展趨勢越來越快,國與國之間越來越密切,但是國與國之間有不同的利益關系。智庫與智庫之間可以有溝通有交流,不一定大家意見一致,但是可以看到不同國家的智庫對同一問題的看法。比如,保護主義大家是否應該聯手對抗。這是跨越政治的溝通渠道。
記者:就貿易保護來講,智庫能夠發揮哪些作用?
劉遵義:在經濟不景氣的環境下,保護主義容易抬頭,智庫中匯集的都是每個國家的精英知識分子,智庫可以出來告訴大家理智一下。但是不單單是貿易保護這一個問題,對于防止核擴散等問題,也是智庫需要發揮作用的。
智庫的研究非常廣泛。比如,地球環境保護的問題,發達國家跟發展中國家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利益,怎么樣能達成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看法,也是需要智庫努力的方向。
記者:在這個社會里,有幾種組織形式。有政府、有商、有學,智庫怎么能把這幾種組織協調到一起發揮作用呢?
劉遵義:智庫是做研究的,它本身都有自己的利益,它的支持者都有不同的角度。最主要的是有智庫這么一個平臺,大家能夠交換意見。
記者:所以對智庫來講,溝通非常重要。這也是全球智庫峰會的意義所在?
劉遵義:對,通過峰會,向外界宣布中國成立了這樣一個智庫機構,有什么問題大家可以多溝通。
記者:在您的經歷中,曾經在多個智庫機構擔任過職務。您覺得在您曾經參與過的智庫中,哪個智庫的形態、作用、功能是發揮得最好的?
劉遵義:我想不同的智庫,各有不同的特點。我覺得智庫最重要的是要維持研究的標準。就是說要尊重事實,尊重分析,不能假造一些東西,公信力是很重要的。大家的意見可能會不一樣,但是不能歪曲事實,這是很重要的。這樣大家才真正有一個溝通的平臺。
記者:您覺得國經中心的優勢和特點是什么呢?國外智庫與政府之間是什么樣的關系?
劉遵義:我想國經中心的優勢是,它有很多社會上的支持,有政府背景的、企業的,在調動資源和資料的過程中,應該有很大的優勢。在對外聯系方面,也有一定的公信力,這是很重要的資源。
亞洲有很多的智庫都與政府有聯系。但在美國比較少。因為在美國政黨有輪替,現在民主黨上臺,布魯金斯就熱了,但是過去8年就很冷清,以前8年是美國企業協會很紅,胡佛研究所很紅。這是有些輪替的辦法。由于總統的輪換,比如共和黨下了臺,很多人會先暫時到共和黨的保守智庫里,過幾年再看,等待機會。在韓國,有一個叫韓國發展研究院的機構,是政府直接提供幫助的。總之,有種種不同的形式。現在也出現了很多民間團體和財團設立的智庫。
記者:您覺得您在中心最重要的作用是承擔起溝通方面的工作?
劉遵義:是的。因為智庫剛開始運作的時候會比較困難。像布魯金斯學會,它已經建立很久了,大家會覺得它做出來的東西很有公信力。新成立的智庫在這方面就比較難。外界無法從經驗上預測它的研究是好是壞,可靠不可靠。因此,需要與外界進行必要的溝通工作。
記者:您是做經濟研究的,我想做經濟研究的學者最大的愿望是自己的研究成果對政府、政府政策起到幫助作用。您不想自己的研究通過智庫渠道能影響政策嗎?
劉遵義:這是中國式的想法。真正做研究的人還是希望發現什么是真的,什么是真理,與政府采用不采用無關。我覺得真正做研究不應該從這個角度出發。
另外,我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已經5年了,基本上用于學術研究的時間很少。
不過我覺得做研究就是因為有個假設引導你做下去。可能這個假設是對的,也可能是錯的。錯了要承認,不能說做錯了不承認。所以說做研究還是要有求真的心態。
記者:我記得您之前就提出過東南亞經濟的缺陷是依靠高投入和缺乏技術進步。中國也是這樣。這幾年中國這樣的情況越來越明顯。現在出現經濟危機,有人認為這是中國經濟轉型的一次機會,您怎么看?
劉遵義:中國經濟確實需要轉型,但要轉成對出口的依賴性進一步降低,要轉成內需為主。中國有些地方對出口的依賴性太大。
做出口本身就是容易賺錢的。一個訂單,不用自己的品牌廠做出去,就賺錢了。在國內做內需的話,要想做成功,需要花點精神。在國內沒有品牌是很難做成功的。臺灣有幾個企業,在中國做品牌做得是很不錯的,比如“康師傅”,最低技術的方便面,我們大家都會做,為什么人家可以做成功?為什么國內沒有這樣的成功案例?就是因為有品牌戰略。為什么他們在臺灣做不成功?是因為市場太小。有這么大的市場,在中國真正做內需還是能做成功的,只是這些年來外需更容易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