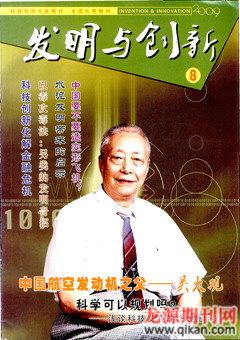科學可以規劃嗎?
李 俠
中國科學院2009年6月10日在京發布《創新2050:科技革命與中國的未來》系列報告,為我國描繪了面向2050年科技發展的路線圖。該路線圖認為,在今后的10年至20年,很有可能發生一場以綠色、智能和可持續為特征的新的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該路線圖對于2050年的中國給出了令人振奮的預測,到那時中國經濟總量將位居世界首位,整體進入世界中等發達國家行列,成為政治、物質、社會、精神、生態五大文明高度發達且高度開放的國家。相信每個中國人對于這份遠景都會充滿憧憬,并渴望這份路線圖能夠早日實現。但是理性地思考,我們也會發現在這份路線圖中還是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對于未來的研究通常采取三種視角:悲觀的角度、樂觀的角度與中性的角度。各種角度都有可取之處。但是,如果在當下科技發展所面臨的現實下,盲目選取樂觀角度就有些烏托邦的味道,對于科技發展的實際促進作用就會大打折扣。基于中國科技的實際,選取中性偏悲觀的角度更好一些。而對于公眾來講,從悲觀的角度來反思未來,也更具有持久的影響與現實的意義。
坦率地說,這份報告在概念構成上存在很大的語義模糊性,至少就筆者所看到的相關介紹,這份路線圖稱作技術發展路線圖更為合適一些,畢竟科學與技術是完全不同的兩類活動,對于技術進行預測是有可能的,而對于科學則是完全無法規劃的。至于對復雜的系統,預測的可能性更是小之又小,任何一個偶然的隨機變量都將使系統偏離原來的發展軌跡。比如從環境問題來看,由于中國正處于一個經濟快速發展階段,環境面臨的壓力逐漸加大,實在沒有多少過硬的證據可以保證2050年,我們的環境一定能夠達到預期目標,至于其他的復雜系統更是如此。拋開這些不談,筆者更為關心的問題是:科學是可以規劃的嗎?以及我們如何看待這些關于未來的路線圖?
科學本質上是探索未知的事業,而未知的最大特點就是充滿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既包括探索過程的不確定性,也包括探索結果的不確定性,還包括科學運行的社會環境的不確定性。在這種諸多不確定性的基礎上,要完全準確地計算出所有可能出現的情況及其后果,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科學是無法被“規劃”的。既然如此,我們為何還是熱衷于這種規劃呢?其實這是人類思維中的一種機械論式認知模式主導的,對于政策與戰略的制定來說,必須時刻警惕這種拉普拉斯機械論認知模式的影響。
既然有些規劃是不可能的,那么是否研究路線圖的努力就毫無意義了呢?顯然不是。雖然科學規劃的后果是不確定的,但這不意味著我們對科學活動束手無策,我們可以通過制度設計盡量為科學發展營造良好的環境,清理各種障礙,明晰科技發展目標與路徑選擇,并為科學發展提供合理的、公平的、有力的支持。今天的科學已經演化為一種重要的社會建制性活動,它的發展與成長離不開整個社會的支持,這就決定了規劃的真正內容應該集中在與科學發展密切相關的制度建設與環境培養上。細化一點來說,就是把國家的目標與意志同科學發展的規律結合起來,繼續穩步增加對科技的投入,為科學健康發展探索正確的發展道路,并提供公正的評審與獎懲機制,以此規范與引導科學共同體未來的行動。
如何給科技活動定位,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首先,它與國家的政治架構有關系。不同的政治架構將導致科學定位偏向于不同的目的。比如在市場機制國家,科學偏向于經濟活動,而在集權制國家,科學更傾向于政治目的,比如朝鮮。經濟活動與政治目的并沒有涇渭分明的界限,所以任何國家的科學活動都同時肩負這兩種使命,只是側重點有所不同而已。其次,對于科技活動的認知是基于機械論原則還是整體論原則,是任何一項科技戰略與政策制定時必須要認真清理的認知預設與背景信念。否則,一個錯誤路標帶來的后果是我們無法承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