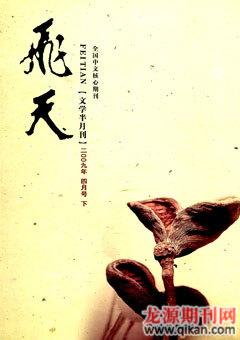論相關文化因素對德彪西鋼琴音樂的影響
何 慮
“印象主義”一詞來源于繪畫藝術。印象派繪畫強調畫家對客觀事物的感覺和印象,是畫家個人情緒的主觀反映。印象主義音樂同樣強調音樂是個人情緒的反映,印象主義音樂的最終目的是音響和音色。印象主義音樂作為一種文化形式,不可避免地與其他文化形式具有一樣的時代特征,在創作觀念、審美特征上具有一致性。德彪西正是充分吸取了來自于文學、繪畫、東方文化等各種藝術成分的精髓,化為已有,再以法國民族性格和精神氣質予以表現,在音樂手法上對傳統的形式與手法進行突破。作為印象派音樂的的代表德彪西,他的音樂理念,他的鋼琴音樂創作風格的形成受到了當時相關文化因素的影響。下面就這個問題進行闡述。
一、象征主義詩歌對德彪西的影響
德彪西雖是音樂家,卻對具有新意的其他藝術懷有崇高的敬意。他的很多朋友不是同行,而是畫家和詩人,他通過每周二晚間在象征主義詩人馬拉美住所舉辦的藝術沙龍,結交了許多藝術家,并與馬拉美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誼。在藝術沙龍里,經常舉行非正式的詩歌和藝術討論會,來自于不同領域的藝術家在這里交流著彼此的創作觀念。在這里,德彪西接受了象征主義的藝術觀念。象征主義詩人主張用象征性的事物暗示主題和投射創作者微妙的內心世界,他們在語言中并不尋求字句的理智的和客觀的功能,他們尋求的是詞語的感官的、音樂的和造型的功能。象征主義詩人通過象征、暗示、聯覺、通感甚至音樂化的手法,以達到他們對于朦朧、神秘的藝術意境的追求。這樣的觀念不可避免地影響著德彪西。與象征主義詩人一樣,德彪西注重于從音樂中引出一種詩意,這種詩意是從感覺、感情、形象的聯系下產生的,在音樂上轉化為多彩的和聲、朦朧的音色、靈動的節奏、意味深長的旋律。
二、印象派繪畫對德彪西的影響
“印象主義”一詞來源于繪畫。印象派興起于19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法國。1874年4月以馬奈、莫奈和雷諾阿為代表的年輕畫家,在巴黎舉辦了一個名為《畫家、雕塑家和版畫家等無名藝術家展覽會》的畫展,其中有一幅風景畫是莫奈的《日出印象》。這次畫展由于它的反傳統性,遭到很多的非議和攻擊,一些人根據莫奈的這幅畫,把這些年輕畫家稱為“印象主義者”。
印象派繪畫具有“寫實主義”的特征。印象主義音樂在這一點上受到印象派繪畫的影響,顯示在兩者追求反映“真實印象”的一致性。印象派想要表達的是大自然在人的視覺上留下來的印象,他們反映客觀世界,但他們不要照相技術那樣的精確,他們追求的是整體效果,他們在追尋閃爍的陽光和流動大氣中的“真實”。
德彪西對于繪畫藝術的興趣同對象征主義詩歌一樣濃厚,顯然敏感的他也注意到了印象派“寫實主義”的存在。在當時,可以說日本浮世繪影響著印象派畫家,而德彪西深受印象派繪畫的影響。他的不少作品與繪畫有緊密的聯系,鋼琴曲《化妝舞會》和《快樂島》的創作靈感都來自于18世紀畫家華托最著名的作品。1902年和1903年訪問倫敦期間在國立畫展上,德彪西看到了特納所作的海洋風景畫,這些畫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畫家畫的海洋風景畫給創作《海》的構思提供過最初的強烈刺激。德彪西的管弦樂作品《夜曲》也是德彪西受印象派影響而創作的,創作這部作品的意圖實際上是嘗試用形形色色方法配器甚至也可以用一種單色來安排的一次實驗——就像繪畫里純用灰色色調畫成的習作。標題之所以取名為《夜曲》,是德彪西受畫家惠斯勒的一組標題相同的繪畫的啟示。
德彪西的作品《德爾斐的舞女》讓人想到擅長畫舞女的印象派畫家德加;《水中倒影》的靈感則是來自于莫奈的同名作品,可以說德彪西的《水中倒影》是莫奈的《水中倒影》色彩語言的移調;《帆》顯示了德彪西對視覺形象進行音響處理的能力,作曲家用簡練的手法就描繪出了航船停泊在港灣中的感覺;《雪中足跡》中,德彪西認為應該表現一幅冰天雪地、令人感傷的畫面;《霧》則是一幅具有惠斯勒繪畫風格的音樂素描。
三、甘美蘭音樂對德彪西的影響
1889年,在巴黎世界博覽會上,來自印度尼西亞爪哇島的甘美蘭音樂給德彪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來自于東方的奇特怪異的音程、音階以及和聲激發了德彪西的想象力,并對他的鋼琴音樂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甘美蘭樂隊中有很多是打擊樂器,因此被稱為打擊樂隊。它的音樂織體具有復調特點,但又區別于西方音樂中的復調音樂。其旋律按層次編排。甘美蘭音樂經常有多條不同的旋律線,每一條都是演奏同一個主旋律,有的聲部旋律相同但速度不同,有的聲部在不同的八度演奏。它的對位旋律只是以加快一倍速度,或者減慢一倍速度演奏主旋律,其余聲部進行即興演奏。雖然甘美蘭音樂的聲部眾多,但在聽覺上仍然是清晰的。德彪西對于甘美蘭打擊樂非常欣賞,他這樣寫道:“如果你不帶任何偏見地去聆聽甘美蘭的打擊樂,你不得不承認,和它比起來我們的打擊樂只不過是馬戲團的噪音。”
甘美蘭的旋律使用兩種主要的音階或調式:五聲調式“斯蘭德羅”,它由基本等距離的音程構成;七聲調式“佩羅格”,它由大小不等的音程構成。對于西方人來說,這樣的音樂是無法與西方傳統的大小調式音階相對應的,甚至是不和諧的,而正是這些不和諧的音響,反而給西方人帶來一種神秘的感覺。德彪西通過運用五聲音階來傳達這種東方的神秘氣氛。德彪西鋼琴音樂中的五聲音階可能是模仿甘美蘭的斯蘭德羅音階的手法。
任何一個音都可以在它的基礎上發出一系列的泛音。泛音現象是甘美蘭音樂的一個重要特征,甘美蘭樂隊中有很多銅制樂器,如鑼、鐘、鈴等,這些銅制樂器在演奏時靠敲擊振動發聲,可以發出所有的泛音。在泛音列中有一些音無法被人的聽覺所感知,因此,甘美蘭音樂的音響效果奇特而富有暗示性。顯然德彪西被這種音響效果吸引,也在他的作品中運用了泛音移位的手法。德彪西具有非常敏銳的聽覺,他只是按照自己對音色和音響的感覺進行創作,可以說他的和聲大多數是從他的聲學經驗中而來,從這個角度看,他的和聲具有聲學意義,與甘美蘭音樂一樣聽起來深邃、朦朧、充滿神秘氣息。
四、民族樂派對德彪西的影響
19世紀是發現異國美的世紀,是曖昧的、神秘的、悲觀的哲學盛行的世紀。就在這個世紀里出現了文學藝術中的民族主義問題,這個世紀的整個的藝術產品都帶有民族主義的色彩。在歐洲一些古老的國家中,由于它們在地緣上位于歐洲的邊緣地區,在音樂風格上較少受到德奧音樂的影響,保持著自身的特質。這些國家的音樂旋律特殊,節奏特別,和聲語言也不同于已被共同接受的原則。民族樂派的作曲家力求發展本國的音樂語言,這樣的做法極大地豐富了音樂表現方法,而通過新的表現方法也增加了表達精神感受的可能性。
(一)移索爾斯基的影響
對德彪西產生過深刻影響的有俄羅斯民族樂
派,尤其是“強力集團”。“強力集團”重視從民間音樂中汲取養分,并以此作為創作的基礎,在強調民族民間特色的同時,也不排斥對西歐傳統技巧的繼承和對東方民族的民間音樂因素的采用,在創作上,他們強調藝術的創新,反對保守,他們的一些作品已經帶有印象主義的元素。
而穆索爾斯基對德彪西的影響是更為深刻的,德彪西對穆索爾斯基推崇備至:“誰也未曾使用過比他更為溫柔而深刻的特定方式來表達出我們內心最美好的感情……穆索爾斯基的藝術聽起來毫無造作之處,而且已經完全擺脫了僵死教條的束縛……他的音樂表現形式之多種多樣,竟然到了無論如何也決不可能和任何既有的,也許可以說‘法定的形式會有什么共同之處的地步,因為決定并構成那些形式的素材,是一些由天生本能就能察覺的,用十分微妙的神思所連接起來的,連續而瞬間的感觸。”
德彪西和穆索爾斯基都具有強烈的創新意識,他們并不受傳統的音樂規則的束縛。“強力集團”的成員都沒有受過音樂學院的正規訓練,穆索爾斯基只是時常把自己的作品給巴拉基列夫看,并由后者予以批改。穆索爾斯基并不認同當時俄國音樂學院教授音樂的方式,他注重的是從民間音樂中汲取養分,是把文學的、戲劇的題材在音樂上予以表現。他在音樂手法上大膽地進行嘗試,手法簡潔而透徹,音樂形象的表達準確而鮮明。穆索爾斯基對德彪西的影響主要在兩個方面。
1寫實和理想的統一。穆索爾斯基的創作帶有寫實主義的特征,他的作品通常聚焦于表現普通人真實的生活,他偏愛自然主義的、日常的、實在的甚至是丑陋的主題和形象。但他的創作目的并不是簡單的、膚淺的模仿自然,穆索爾斯基認為不能僅用藝術來描繪物質美,通過音樂語言來投射作曲家內心世界對外部世界的感受才是穆索爾斯基的藝術追求。“我的音樂是對人類語言的藝術再現,包括其中的最細微之處。”顯然,穆索爾斯基希望的不是“真實中的音樂”而是“音樂中的真實”。這樣的美學思想在德彪西手中得以發揚,德彪西強調音樂對于自然界的依賴,但又不是簡單意義上的自然主義的模擬,而是音樂化的描繪。這時的音樂成了德彪西自我表現的新方式,不是自我感情的表現而是自我感官的表現。神秘的、朦朧的、夢幻的情緒印象成為德彪西音樂的特點,結構和主題被音響和音色所替代。在德彪西筆下,多彩而空靈的和聲,細碎而靈動的節奏,飄逸而意味悠長的旋律構成了一幅幅充滿光感,可以真切地用聽覺就可以感受到的畫面。
穆索爾斯基鋼琴組曲《圖畫展覽會》、歌劇《包里斯·戈都諾夫》和歌曲給德彪西非常深刻的印象。穆索爾斯基對于作曲的一些創新顯然也影響著德彪西。穆索爾斯基對和聲的運用大膽而富于創新精神,他的和弦結構常常是叛逆性的,通過對增三和弦的運用弱化和聲的功能性,使調性的感覺變得模糊。穆索爾斯基并不按照西方傳統作曲方法的要求進行創作,他不喜愛對一個主題動機用各種音樂手法予以發展的傳統寫法,他重視變化莫測的發展,注重從一個普通的音調里開發出新穎的變化發展。與德彪西相類似,穆索爾斯基喜愛用音樂語言對現實生活做畫面式的描繪,這時,創作不再受到規則的束縛,而是作曲家的內心情緒的真實反映。
穆索爾斯基的這些手法在當時是超前的。德彪西抓住了這些新穎,大膽的因素,并且繼續予以發展。德彪西更加強調和聲的色彩性,削弱功能性,把和聲從規則的束縛下解放出來。這樣他得到了更大量的和聲色彩,他可以變換、對比、混合這些色彩,用這些閃爍著色彩的聲音構筑他美妙的光感世界。
2造型與表情的統一。穆索爾斯基是一位擅長音樂造型與表情統一的大師,他在鋼琴組曲《圖畫展覽會》中對展覽會上的圖畫作全景式的描繪,從美學角度看,其音樂本身具有可感可觸的影像。德彪西也注意到了這一點,曾與德彪西長期合作的法國女鋼琴家瑪格麗特·隆就說過:“與其說德彪西的音樂是描繪了自然景色,不如說他是通過自然景色的描繪來刻畫人的感情。”
穆索爾斯基的《育兒室套曲》具有視覺性的現實場景的音樂描繪。從創作角度上來看,穆索爾斯基完全是從一個孩子的視角進行構思,喜愛孩子的穆索爾斯基仔細觀察孩子說話時語調上的變化,利用旋律、節奏、休止、力度的變化等音樂語言進行模仿,以傳達孩子的疑慮、驚喜、興奮等情緒。準確地說,這部作品更像是“孩子們的交談”。德彪西給予穆索爾斯基的《育兒室套曲》高度評價,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這個作品在造型與表情方面達到了完美的統一。由于對這部作品的欣賞,因而于1908年產生了《兒童園地》,在這部作品中,德彪西從一個寬容的父親的角度來看待兒童的天地,成功地刻畫了小孩子天真活潑的形象,富有情趣。在《木偶的步態舞》里,德彪西運用爵士樂的節奏,活靈活現地刻畫出了一個搖擺走動的黑人木偶的感覺。
(二)格里格的影響
另一位對德彪西產生影響的民族樂派作曲家是格里格。格里格的音樂語言是十分個性化的,在審美上追求的是挪威式的質樸無華、淡而甘醇、情深意長的風格,即“運用古老的自然調式,特別是里第亞大調,帶升高的四級音,各種功能的和弦之間的多樣化混合,長固定音型,多方使用的持續音,強有力而尖銳的節奏處理……作品中多樣化和聲手法使他接近法國同時代人——印象派代表人物德彪西”。德彪西從格里格的作品中借鑒了很多和聲手法,“從邏輯化、力度型的半音和聲,到調式化、色彩型以及自由化、線條型的半音和聲,表現了格里格的半音技法繼承、創新、開拓未來的歷史作用,對其后印象主義和聲語言的形成和發展具有重要影響。”
德彪西在對民族樂派贊美的同時,也看到了民族樂派在運用民間音樂來發展專業創作上的一些弊病。德彪西正是在總結前人的教訓的基礎之上,最終開創了印象主義風格。
德彪西的鋼琴作品標題多以視覺性語言來表達音樂的內涵,在各種不同情況下做各種暗示或略帶含蓄的表露,從而給人留下視覺形象重于情感敘述的印象。“聽覺的一視覺的”一直是德彪西的追求,用音樂來表現自然景物應該說是德彪西的所長。德彪西盡力從詩歌、繪畫以及其他音樂家那里汲取養分、化為已有,再用帶有法國民族氣質的音樂加以表現。無疑,德彪西的實踐是成功的,盡管他所表現的法國精神是不完全的,而且音樂中也明顯地包含著其他民族文化的某些特點,但法國人民都尊稱他為“法蘭西的靈魂”。
參考文獻
[1]朱伯雄,世界美術史:第九卷[M],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1987
[2]高天明,日本美術史話[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98
[3]余虹,歐美象征主義詩歌賞析[M],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1991
[4]查爾斯·查德維克,象征主義[M],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