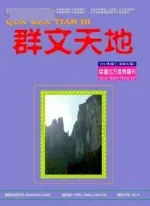從西漢與匈奴和親看民族發(fā)展
張 進
和親政策的出臺是從漢高祖劉邦與匈奴冒頓單于開始的。由于西漢與匈奴政治經(jīng)濟形勢的好壞與軍事力量的強弱不斷變化,西漢與匈奴前期與后期和親的情況也有所不同。但無疑都對兩民族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發(fā)展起到了促進作用,更是對民族的融合與發(fā)展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西漢與匈奴的和親,不僅奠定了漢匈文化大交融的基礎(chǔ),也為民族大融合以及中華民族的發(fā)展做了物質(zhì)與精神上的準(zhǔn)備。
一、西漢與匈奴和親概況
(一)漢高祖至漢武帝時期
這一時期,漢朝集中力量恢復(fù)秦末和楚漢戰(zhàn)爭以來的被嚴(yán)重破壞的經(jīng)濟,緩和農(nóng)民的反抗,著力解決諸侯王地方割據(jù)勢力與中央專制政權(quán)的矛盾,所以對匈奴無暇以顧。而這時的匈奴正是冒頓單于、老上單于、君臣單于執(zhí)政的強盛時期,他們對周邊其他民族征戰(zhàn),掠奪奴隸和財物,實力甚為雄厚。在這種情況下,匈奴不斷侵?jǐn)_中原地區(qū),就連漢高祖劉邦也曾被匈奴圍困在白登山七日之久,終以劉敬的“和親”之策結(jié)束了漢匈的對峙。雖然匈奴實力強大,但西漢還有一定的能力足以自衛(wèi),給予有力的反擊,所以才維持了漢匈的和親關(guān)系。筆者看來,這一時期漢匈的聯(lián)姻請求基本都是漢朝提出的,如:“白登之圍”后高帝嫁宗室女于冒頓單于;景帝時,“復(fù)與匈奴和親”,“遣翁主如故約”;武帝初期,與匈奴“明和親,約束厚遇,關(guān)市饒給之”。在這期間,匈奴雖然有時“小入盜也”,但“無大寇”。
(二)漢武帝后期至西漢末
這一時期,漢匈實力對比發(fā)生轉(zhuǎn)變。經(jīng)過漢初幾十年的“休養(yǎng)生息”來鞏固發(fā)展,政治穩(wěn)定、經(jīng)濟、軍事實力大大提高。與此同時,匈奴統(tǒng)治集團頻頻發(fā)生內(nèi)訌,政局混亂,之前附屬匈奴的民族,如丁零、烏桓、烏孫以及西域各族紛紛起兵反抗。在漢武帝的英明決策下,停止以往的妥協(xié)政策,積極主動地對戰(zhàn)匈奴。漢武帝初期與匈奴的戰(zhàn)爭是正義的,符合人民的意愿和歷史的發(fā)展趨勢。當(dāng)匈奴向西漢請婚想借此緩和戰(zhàn)事時,西漢拒絕請求,繼續(xù)進行軍事進攻就帶有一定的侵略色彩。漢武帝后期,由于常年征戰(zhàn),兵力、馬匹、物資嚴(yán)重受損,再加上人民負(fù)擔(dān)的沉重,漢武帝決定與民休息,“不復(fù)出軍”,恢復(fù)與發(fā)展經(jīng)濟。正是在這種形勢下,宣帝才與匈奴“復(fù)修和親”。到了漢元帝時期,昭君出塞更是把和親帶到頂峰,漢匈關(guān)系空前友好。從以上漢匈實力對比我們可以看出和親與否的主動權(quán)已轉(zhuǎn)向西漢,武帝時匈奴“遣使好辭以和親”被拒絕;昭帝時,匈奴又?jǐn)?shù)次請求和親;宣帝時,匈奴派使臣入漢“請和親”,宣帝同意,于是雙方斷絕了長達70余年的和親關(guān)系又得到了恢復(fù);元帝時,呼韓邪“愿婿漢氏”,元帝賜“良家子”王昭君給呼韓邪為閼氏。昭君出塞為漢匈兩族的融合與發(fā)展做出的貢獻更是空前絕后。
二、和親對匈奴族、漢族發(fā)展的貢獻
(一)和親對匈奴族發(fā)展的貢獻
西漢作為一個比較完善的封建政權(quán),相對于匈奴這個奴隸制政權(quán)來說,其在物質(zhì)、經(jīng)濟、文化等各方面都先進于匈奴。西漢初年與匈奴的和親,不僅僅是西漢單方面的暫時妥協(xié)政策,也是因為匈奴單于貪戀漢朝財物,西漢王朝的慷慨大方對匈奴的發(fā)展做出了巨大貢獻。漢高祖劉邦“白登之圍”后,使劉敬往結(jié)和親之約,并開放關(guān)市。除了把公主嫁給單于為閼氏外,還一次贈給匈奴金千金,并“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shù)”。文帝六年, 曾遣中大夫意、謁者肩送單于“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褥、錦袷袍各一, 比余一, 黃金飾具帶一, 黃金胥比一, 繡十匹, 錦三十匹, 赤綈、綠繒各四十匹”。由于匈奴游牧經(jīng)濟的不穩(wěn)定性,逐水草而居,民族的興旺與否受到氣候的制約。故每逢“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shù)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饑疫,死耗太半”時,漢朝都會送糧食和棉被到匈奴,幫助他們渡過難關(guān)。大量的隨嫁品與賞賜品被送到匈奴,不僅改善和豐富了匈奴貴族們的物質(zhì)生活,而且對改善漢匈關(guān)系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通過和親,漢朝公主帶給了匈奴豐富的財物、生產(chǎn)工具、先進技術(shù)和人才。如:昭君遠嫁匈奴后,與匈奴人民一起用勤勞的雙手,開發(fā)了祖國的北疆。她率領(lǐng)著當(dāng)?shù)氐膵D女們從事農(nóng)耕、紡織,把先進的生產(chǎn)技術(shù)傳入匈奴,使得匈奴人有逐水草而定居的放牧,更有一部分人從事了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改變了匈奴人“隨畜牧而轉(zhuǎn)移”、“逐水草遷徙”、“涉狐兔,用為食”的生活方式,過上了半農(nóng)半牧的生活。而且隨這些公主出行的一些漢朝官員,也對匈奴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據(jù)《史記》和《漢書》記載,文帝時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單于為閼氏,中行說作為宦官隨行。中行說到匈奴,甚得單于親信,如他“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眾畜物”,教單于遺漢書的式樣,“牘以尺二寸”,比漢遺單于書“牘一尺一寸”還大。除此之外,匈奴人筑城、鑿井的技術(shù)雖然是水胡人衛(wèi)律教的,但衛(wèi)律在漢朝居官多年,是個漢化了的胡人,故筑城、鑿井的方法是間接從漢人那里學(xué)會的。
(二)和親對西漢發(fā)展的貢獻
和親不僅漢朝對匈奴的發(fā)展有貢獻,而且匈奴對漢朝的發(fā)展的貢獻也很突出。一種有趣的現(xiàn)象,似乎中國古代強大的中原王朝都與擁有大量的馬匹有一定的關(guān)系。對于西漢王朝來說,尤其漢武帝時期對匈奴的長期征戰(zhàn),導(dǎo)致了馬匹匱乏,影響了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而匈奴這一“馬背上的民族”,牲畜的多少決定著這一民族的興衰。關(guān)于匈奴馬匹數(shù)量、種類的驚人,我們從《史記·匈奴列傳》中就可以看到,“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龍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骍馬”。從以上文字我們可以看出匈奴可以把馬按照顏色的不同編隊管理,從東、南、西、北四個方向把漢軍包圍,可見匈奴的馬匹數(shù)量、種類之多。而在漢匈開放的關(guān)市中,“北單于復(fù)欲與吏人合市……驅(qū)牛馬萬余頭來與漢賈客交易”,使匈奴的大量馬匹輸入中原,大大提高了西漢的軍事戰(zhàn)斗力和綜合實力。匈奴的牛、驢、騾等牲畜大量輸入中原后,對中原的農(nóng)業(yè)發(fā)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提高了農(nóng)耕民族的社會生產(chǎn)力水平。
漢初,因連年征戰(zhàn),社會出現(xiàn)了“丈夫從軍旅,老弱轉(zhuǎn)糧鑲,作業(yè)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的現(xiàn)象。但是自漢高祖使劉敬與匈奴“約為昆弟以和親”后,漢朝就開始“寢兵、休士卒、養(yǎng)馬”,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漢朝直到“孝惠、高后之間,衣食滋殖”,到了漢武帝時,更是國富民強。“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余財”。甚至當(dāng)時,“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腐敗不可食”,出現(xiàn)了“眾庶街巷有馬。,千百之間成群”的情景。按照漢匈和親前后社會狀況的對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可以說漢朝的富強,是與漢匈和親創(chuàng)造出的安定的社會環(huán)境分不開的。
(三)西漢與匈奴和親對民族融合的貢獻
對和親雙方來講,強調(diào)的是政治原因,是雙方簽訂政治盟約的一種形式,是為政治服務(wù)的一種手段,其結(jié)果導(dǎo)致中央政權(quán)與邊疆少數(shù)民族政權(quán)間,漢族與少數(shù)民族間的和好。和親促進雙方經(jīng)濟文化的發(fā)展,并對少數(shù)民族的生活各方面都起著很大的影響。正所謂“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統(tǒng)治階級之間的和親促成的經(jīng)濟、文化交流,也必然引起勞動人民間的聯(lián)姻及廣泛的經(jīng)濟、文化交往,這就進一步加速了民族間的融合。
在漢匈長期交往的過程中,漢朝先進的文化逐漸把匈奴落后的文化吞噬,而匈奴也自愿向漢朝先進文化靠攏。如:復(fù)株累單于入漢,見漢帝的謚號為“孝”字,非常羨慕,匈奴稱孝為“若鞮”,從復(fù)株累單于后,皆用“若鞮”二字。而且每當(dāng)新的匈奴單于繼位后,都遣自己的兒子入漢庭做質(zhì)子,“他們在漢朝學(xué)習(xí)漢文典籍,通曉漢朝的禮節(jié)禮儀,并與漢朝的世家子弟和朝廷名士素有交往”。匈奴人長時間受漢文化的熏陶并且入塞中原長期居住,迅速地接受并適應(yīng)漢文化,長久往來已與漢族人無異。穩(wěn)定是發(fā)展的前提,漢匈和親帶來了安定、融合的社會環(huán)境,緩和了漢匈關(guān)系,創(chuàng)造了發(fā)展的可能性。使兩族人民化干戈為玉帛,避免民族沖突和戰(zhàn)爭,緩和民族矛盾,沖淡了民族偏見,增進了民族情感,促進了民族融合。
(四)西漢與匈奴的和親對中華民族發(fā)展的貢獻
如果沒有匈奴的馬匹進入中原,就不會有漢朝軍事戰(zhàn)斗力的提高,也不會帶來農(nóng)業(yè)的快速發(fā)展;如果沒有漢族農(nóng)耕技術(shù)和工具傳入匈奴,就不會有匈奴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如果只有漢朝的進步,而匈奴仍然因循守舊、不求進取,那么匈奴的落后也必然會阻礙漢朝的發(fā)展速度。就是因為漢匈雙方的互幫互助,才能構(gòu)建和諧社會,促進雙方共同繁榮、共同發(fā)展。通過漢匈的和親,兩民族開始接觸、混雜、聯(lián)結(jié)和融合,同時也有分裂和消亡,匈奴從經(jīng)濟、生活、文化到社會政治制度都受漢文化的影響被逐漸“漢化”,而“漢化”的結(jié)果,是使匈奴人民加入漢族大家庭的懷抱,成為漢族大家庭的一分子,不斷為漢民族注入新鮮血液,奠定了中華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歷史的格局,為中華民族的發(fā)展做出了獨特的貢獻。
從西漢與匈奴和親的史實來看,和親為百姓帶來了安定,為邊疆人民換來了和平,對維持和發(fā)展兩個政權(quán)的關(guān)系等方面起了到積極作用。在古代的歷史條件下,用和親這種獨特的和平方式來處理民族關(guān)系,既避免了雙方的軍事沖突,得以“息兵、休卒、養(yǎng)馬,世世昌樂”,使“天下大安”、“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又實現(xiàn)了經(jīng)濟、文化的交流,即“以漢所余,易彼所鮮”。這樣無疑是有利于各民族之間的友好往來的。和親政策促成了周邊少數(shù)民族與中原地區(qū)的統(tǒng)一,它維系著兩個民族世世代代的友好團結(jié),推動著兩個民族社會文化生產(chǎn)和生活的發(fā)展,促進了民族團結(jié)與融合,更有利于祖國大一統(tǒng)局面的形成。和親是民族關(guān)系史上的里程碑。
參考文獻:
[1]司馬遷.史記·匈奴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
[2]漢書·匈奴傳.中華書局.
[3]后漢書·南匈奴傳.中華書局.
[4]中國民族關(guān)系史論文集,下.民族出版社,1982.
[5]晉書·外戚王恂傳.中華書局.
[6]史記·平準(zhǔn)書.中華書局.
[7]漢書·食貨志.中華書局.
[8]閻明恕.中國古代和親史.貴州人民出版社,2003.
(作者簡介:張進(1986-4)河北石家莊人,中南民族大學(xué)民社院2008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少數(shù)民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