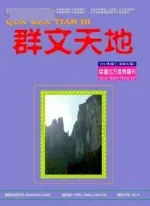古代少數民族遷徙對文化和環境的影響
自從炎帝族第一次從西方逐步東移,進入渭河流域和黃河中游后,便開啟了中國少數民族遷徙的歷史。從此各民族的遷徙趨于活躍,遷徙活動頻繁,但一個民族的遷徙不僅僅是一個民族的事,它往往會引起與之有關民族的連鎖反應。各民族間通過遷徙而相互影響、相互作用,逐漸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割的聯系。由于文化是在特定環境下逐步發展而來的,所以這些遷徙民族的文化在這一特定過程和環境中,不斷地與其他民族文化發生碰撞,它們互相聯系、互相影響、互相作用,隨著交往的加深,慢慢發生變遷,形成了新的民族文化。斯圖爾德也曾說過“環境在塑造文化過程中扮演著動態的、創造性的角色。”而且他們在這些遷徙過程中,為了滿足更好的生存需求,經過不斷的適應、改造、利用遷入地的自然環境,形成了人與環境的有益互動,使人類在發展的同時擁有更加和諧的環境。本文主要論述古代少數民族遷徙對民族文化的影響,并從文化生態的角度來談古代少數民族的遷徙與自然環境的相互影響。
一、古代少數民族遷徙對民族文化的影響
民族是文化的載體,是由文化維系的人們共同體,世界上沒有文化的民族和沒有民族歸宿的“超然文化”都不存在。所以民族的遷徙實際上就是文化的流動和交流。不同的民族遷徙,使原本毫無聯系的民族形成了交錯雜居的格局,在他們經過吸收、融化、調和后,其民族文化的內容和形式發生了變化,最后逐漸形成一個新的文化體系。因為當少數民族大量遷入新的居住地后,他們離開了熟悉的自然環境,而面臨著全新的環境,生存環境的巨大變遷,使以往的生活方式在新的環境下無法繼續,于是為了生存,他們與當地民族之間不斷進行長期的、持續的接觸,使各個民族之間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受到相互影響,民族文化在相互的接觸和交流中互相吸收、融合,促進了民族文化的發展。并隨著交流的增多、聯系的加深,必然導致這些民族在居住、生產工具、服飾和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上的變遷。
尤其是少數民族的內遷,這些內遷的少數民族為了更好地生存,在內地封建化強烈影響下,他們的文化受到了巨大的沖擊,于是他們開始模仿當地漢族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并在當時統治階級的引導下,逐漸改變了原有的生產結構,致使本民族的文化因子慢慢減弱,逐漸融合到漢族中。如氐族的遷徙,尤其是向關外遷徙的氐族,與漢族等民族雜居,使他們接受了較為先進的漢文化,最后他們逐漸被融入到漢民族中。而有的甚至導致民族的消亡,如已經在歷史上消失了的川南都掌蠻,在明代,他們與漢族的交往甚密,受漢族文化影響較深,逐步喪失本民族文化,融入到漢族文化中,到最后在他們遭遇強硬的同化政策時,他們唯一的選擇就是隱退于歷史中,并走向了民族消亡。而有的則與當地原有民族文化融合,從而整合成不同的民族文化。如遷徙的羌人族群為了適應不同的自然生態和文化環境,而不斷地與其他民族的文化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最終形成了新的文化體系。
文化變遷的具體內容包括物質文化變遷和精神文化變遷。
(一)物質文化變遷
物質文化的變遷主要指居所、飲食習俗、服飾發式、交通工具等的變遷。由于各民族所處的自然地理條件不同,其表現出來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以及經濟文化類型和生活方式也各不相同,但隨著他們的大量遷徙,不斷地受到遷入地經濟、生活方式的影響,并與當地不同的民族文化相互發生碰撞,各個文化之間相互整合或融合,以往的習俗也隨著環境的變遷和周圍民族生活方式的影響而發生了變遷。如早期的羌人以畜牧和狩獵為主,其主食自然是奶、酪和牛、羊肉。但在東漢以后,隨著羌人的內遷,飲食結構發生了變化,在以過去的飲食結構為主的同時,糧食也占了一定的比例,尤其是到十六國時,其飲食進一步農業化,與內地民族的飲食基本無異。在居住上,早期的羌人是居無定所的,主要以廬帳為居,當他們遷入內地后,居住習慣發生了變化,大多數都改以土屋為居。服飾發式上也發生了變遷,比如羌族婦女由內遷前的披發掩面變為內遷后的辮發等。
(二)精神文化的變遷
精神文化是人類精神生產的全部成果,一個民族的精神文化形式和內容決定于一定民族的社會、經濟和生活方式。精神文化的變遷主要包括民族語言的變化和風俗習慣的變遷。在古代,少數民族大多都是有語言而無文字的,但由于頻繁的遷徙,使民族語言受到遷入地民族語言、文字的巨大影響,這些遷徙民族的語言慢慢發生了變遷,最后導致有的語言與其他民族語言相互結合,形成新的語言。而有的語言則隨著民族融合而消失,尤其是內遷的少數民族,他們長期與漢民族接觸,游牧生活也改為了定居生活,受漢族較高文化的影響較深,忽視了本民族的語言。如氐族,在公元二到三世紀是有自己本民族語言的,但到了南北朝時期,隨著氐族的頻繁遷徙,氐族的語言的使用范圍大大縮小,反而漢語在氐族中流行起來。
風俗習慣也是一種重要的文化現象,是一個民族在衣、食、住、行、生產勞動、婚姻、喪葬等方面的風尚和習俗。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風俗習慣,而且地理環境和社會環境的不同也會使風俗習慣表現出一定的差異,其具有鮮明的民族性和地方性的特點。所以,隨著民族的大遷徙,地理環境和社會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民族風俗習慣也必然會發生重大變遷。如羌族、氐族和黨項等最初皆是火葬,但隨著他們的大量內遷,受內地漢文化的影響,逐漸由火葬改為土葬等。另一方面,由于少數民族處在不斷的遷徙過程中,使他們生活在不同的環境下,接觸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因而視野也變得更加開闊,并能夠廣泛接納各種文化,對于任何外來文化尤其是宗教信仰都不排斥,從而使遷入地成為民族文化的交匯地,而且各民族間不同文化在此交相輝映,形成了今天豐富的民族文化體系。
二、少數民族遷徙與自然環境的相互影響
關于人與環境的關系,一直以來都備受關注,環境是人類存在的自然基礎和社會發展的必要物質條件,但人類又具有改變、復制、破壞甚至有時超越自然環境限制的獨特能力。所以生態人類學在考察自然環境對人類影響時,一般都認為文化與環境存在著一種動態平衡和適應關系,古代少數民族的遷徙就是此點的印證。他們的文化與環境不斷相互適應,帶來了環境的大變遷,而環境對他們的遷徙也產生巨大的影響和作用。長久以來,關于它們對人類的影響,一直存在兩種觀點,即“保守主義者”和“保護主義者”,前者希望保留自然資源,為人類所用,而后者則意識到人類對自然本身的一種責任感,希望保護自然,避免人類的破壞。我們認為社會的發展與環境的發展是具有一致性的,社會的變化必然在環境中得到相應的反映,所以我們對古代少數民族的遷徙活動與環境的相互影響進行分析,對我們今天的實踐具有極其重要的指導意義。比如前不久的生態移民,其實質就是人與環境關系的重新調整,其中就涉及了牧區的生態移民以及民族生產生活方式的改變等一系列問題。
(一)自然環境對民族遷徙的影響
最初的人類遷徙是為了順其自然、求得生存的需要。在古代社會,生產技術不發達,自然環境的惡劣和嚴重的自然災害威脅著各民族的生存,特別是那些對自然依賴性很大的游牧民族來說更是如此。為了生存,人們不斷地向自然索取物質,在環境中實現自己的目的,使其朝著自己的愿望發展,但是他們往往忽視了當這些行為超過自然承受力時,便會對環境產生的不利影響,甚至導致環境的變遷。所以當他們意識到生活場所、自然環境遭到破壞了,其向外尋找新的游牧地就成為他們必然的選擇,從這個角度說自然環境的惡化是少數民族遷徙的最初動因。
雖然地理環境對社會發展不起決定性作用,但它是社會發展的自然前提,尤其是在早期人類生產力低下的情況下,一定的地理環境是有利于一些生產方式的發展,而不利于另一些生產形式的發展的。也正由于此點,決定了各民族的遷徙必須遵從一定的條件,其遷徙路徑和方向必然受環境的影響。所以當各民族大遷徙時,人們必須充分考慮自然環境的客觀性。如大興安嶺的原始森林,那里出現的必然是以狩獵為主的鄂倫春等民族。再如回紇的遷徙,因為河西走廊土地肥沃,水草豐美,多為適于農耕的土地,當地的農業發達,為此他們選擇了遷徙到當地。當他們到河西走廊后,在繼續以經營畜牧業為主的同時,逐漸學會了農耕,并轉向半農辦牧的生產方式,而他們的生活方式也由以前的半定居轉變為定居生活。所以在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較低、生產技術落后的古代,地理環境對民族的發展尤為重要。因為社會的發展主要依賴生產的發展,而生產的發展又離不開一定的地理條件。
(二)民族遷移對自然環境的影響
只有頻繁的遷徙,才能不斷打破那種大雜居、小聚居的格局,形成雜居的局面,從而創造民族融合最佳的地理環境和條件,當古代少數民族隨著民族的遷徙,其居住地自然環境、社會環境都發生了改變,民族之間交往逐步擴大,經濟文化交流漸漸增多,促進了民族融合,加速了少數民族文化和經濟的變遷,對遷入地和遷出地的民族和社會、環境等都帶來了一系列的影響。環境改變了,生活方式也得必然跟著發生變化。而生活方式大變化又會相應地影響自然環境,好的、合理的方式會大大改善自然環境,使其更加有利于人類的生存。所以說民族的遷徙客觀上有利于自然生態環境的保護。
自然環境為人類提供了基本生存條件,是人類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來源,而人類是自然界長期發展的產物,是不斷適應自然的結果,人被看做是與環境中的所有因素相互作用而適應環境并不斷發展的。從某種意義上講,人對于環境的變遷有時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因為改變環境使之更加有效地滿足人的需要、促進人的發展是人類生生不息的追求。但并非所有因適應環境、改造環境而出現的各種文化類型和文化習俗都是合理的,都是符合生態原則的。所以我們要在總結以往經驗基礎上,因地制宜,充分考慮地域的特殊性,吸收合理的成分,在自然環境與人類的相互作用中,彼此適應,使環境、經濟、社會更加和諧的發展。
參考文獻:
[1]楊庭碩等主編.民族、文化與生境.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
[2]凱·米爾頓.環境決定論與文化文化理論——對環境話語中的人類學角色的探討.民族出版社,2007.
[3]林耀華主編.民族學通論.中央民族大學出版,1997.
[4]屈川.都掌蠻—一個消亡民族的歷史與文化.四川人民出版,2004.
(作者簡介:張小燕(1984—)河南鄭州人,中南民族大學民社院2008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與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