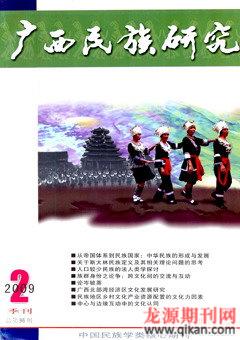從瑤族石牌律看法律的起源
莫金山 陳建強
摘要:世界既是統一的,又是多樣的。瑤族石牌律的產生與人們論述法律和國家的產生有不少共同之處,但又有其獨特性。本文研究的目的,就是給人們提供一個距今僅五六百年,既有典型性、系統性,又有清晰發展邏輯的少數民族法律的起源形式,為世人研究法律和國家的起源提供一個去古不遠的參考標本。
關鍵詞:瑤族;法律;國家;起源
作者:莫金山,廣西民族大學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南寧,530006;陳建強,廣西來賓市審計局局長。來賓,546100
中圖分類號:C95;1391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454x(2009)02-0139-007
法律作為規定人們行為規范和維護社會關系、社會秩序的力量,其起源問題,一直是人們熱心探討的古老而又常新的話題。例如,法律究竟是在人類歷史發展的哪個階段孕育產生的?法律產生的根源和動因是什么?法律產生的過程如何?最初的法律的表現方式怎樣?其共同的規律是什么?等等,便是法學史聚訟多年的熱門話題。
由于法律的起源距離我們今天已十分遙遠,法律產生的最初情景,無疑早已消失在人類文明歷史大道幽深的盡頭,不可能重現。于是,從19世紀下半葉起,西方的一些學者對人類早期社會的研究逐漸從依靠史料、文獻和考古,開始向“人類活化石”的考察轉移,并卓有成效地通過對仍然生活在當今世界的一些原始部族的制度、習俗的考察,來窺探人類早期社會情形,由此也給人們探討人類早期社會法律提供了新的思路。
新中國成立后,不少的學者也認為,用少數民族社會材料和習慣法的產生來解釋法律的起源。將便于我們從渾沌模糊的冥想中縷出一條清晰的思路來。于是,不少學者深入西南、西北少數民族中去尋找答案。但由于這些地區的民族法,要么是口頭習慣法,或零碎的不系統的成文法,要么是封建割據政權王法,或階級剝削很明確的奴隸制、農奴制的法律,都不是國家初始狀態的法律,因此對法律和國家的起源研究并無多大的幫助。
在這里,我們向大家介紹往昔人們并不太注意的金秀大瑤山的瑤族石牌律,它的產生、發展過程與人們理論上描述的法律和國家的產生情景很相似。對它的研究可為人們探討法律和國家的產生,提供一些具體真實的片斷,并希望為人們勾畫出人類文明社會的曙光。
廣西金秀大瑤山是中國瑤族最重要的聚居地。它位于廣西的中部,現金秀瑤族自治縣是其主體部分。這里山高坡陡,谷深林密,交通極為不便。元末明初,瑤民從湖南、廣東等向此地遷移,并在此生長繁衍。從那時起,這塊二千多平方公里的山區,在明、清和民國時期雖然名義上被周圍七縣所“分治”,但實際上卻是一塊政治死角。這里既無官府衙門,又無土司、瑤官之類的封建官府代理人。瑤民既不抽丁當差,也不繳納所謂的“皇糧國稅”,自耕自食,日出而作,日落而食,是一塊名副其實的“化外”之地。因此,這里的瑤族文化保存得較為豐厚。
當然,大瑤山也不是一塊凈土,并非人間的桃花源。明清以來,隨著瑤族社會內部的私有制、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的發展,大瑤山里的雞鳴狗盜,恃強凌弱,以眾暴寡,爭山霸田,搶劫財物等現象也不時發生。明王朝為鎮壓大藤山瑤民起義,先后動用十幾萬大軍,對瑤民進行清剿。在這樣險境下,大瑤山瑤族為了生存發展,創立了自己的習慣法形式——“石牌律”。
所謂石牌律,即是瑤族把有關維護社會生產活動,保障社會秩序正常運行和人們行為準則的條律,刻寫在石板上(或寫在木牌上),立于村口或大路旁,希望大家共同遵守。目前,人們能看到的大瑤山石牌律有38件和“料話”(律文解說詞)6件,共45件。
據了解,大瑤山石牌律形成于明朝初期,目前所見最早的石牌律是《成二、下故都等村石牌》(明崇禎四年,1631年),經過六百多年的發展,到20世紀30年代因國民黨新桂系實行鄉村建設運動而衰落。1940年農歷七月十四日,國民黨金秀警備區署強行“開化”大瑤山,瑤族人民“大啟石牌”,奮起反抗,用砂槍阻擊金秀警備區署進入大瑤山,遭國民黨軍警血醒鎮壓,槍殺十余人,戰斗最激烈的田村被化為灰燼。1942年,金秀警備區署改名為金秀設治局,把大瑤山劃分為13鄉,委任鄉長、村長,實行保甲制度,以治民事,石牌制度實際上被廢止。
從明初到1940年,在石牌制五六百年的發展過程中,金秀瑤族曾召開了四次規模較大的石牌大會。第一次是光緒九年(1884年),以金秀村為首的11個茶山瑤村寨與黃元維等人為代表的過山瑤訂立了《莫村石牌》。第二次是光緒二十二年(1897年),以金秀四村為首的7個茶山瑤村與23個盤瑤村寨共同制定的有1800人參加的“兩瑤大團石牌大會”。第三次是1914年召開“六十村石牌大會”,第四次是1918年召開的“三十六瑤七十二村石牌大會”。
那么,大瑤山瑤族石牌律又是怎樣產生的呢?
一、從瑤族石牌律的產生看法律的起源
首先,瑤族的社會生產生活是石牌律產生的源泉。生產勞動是人類生存發展的基礎,也是各種社會文化現象產生的源泉。大瑤山的瑤族在進山之初,由于生產力低下,瑤族先民為了戰勝洪水猛獸和其他自然災害,只能過著父家長大家庭生活,一個父親帶領妻兒老小共同生活,依靠集體的力量與大自然作斗爭。因此,當時沒有個體家庭私有經濟,大家過著共產制的生活,人口不多,矛盾糾紛也少。那時,有習俗,但沒有形成習慣法。
隨著生產的發展、人口的增長和勞動產品增多,個體小家庭離開大家庭也能生存,共產制大家庭于是解體了,個體家庭私有經濟形成了。村落不斷增多,人們之間交往日益密切,矛盾糾紛增多,調解矛盾糾紛的習慣法也形成了。
其次,民族習慣和民族共同意識是石牌律產生的社會基礎。現今所見的石牌律其文開頭大多都說“瑤還瑤,朝還朝(漢)。先有瑤,后有朝”。其意是說,瑤族與漢族不同,各有區別,不能融合。世上先有瑤族,后才有漢族,瑤先于漢。在這個口號下,在婚姻上瑤族提出“雞不攏鴨,狼不伴狗”的說法,宣揚瑤族不與漢族通婚,實行族內婚制;在這個口號下,瑤族進一步提出“瑤山是瑤人的瑤山”,“朝廷管國事,瑤人管瑤山”,瑤漢互不相干。同時,石牌律鼓吹“石牌大過天”,將石牌法凌駕于官府王法之上,反映了瑤族對封建王朝統治的蔑視和對石牌法的敬畏。這些民族共同意識的形成為法律和國家的建立作了思想輿論準備。
其三,抵御兵匪攻擾和解決內部矛盾是石牌律產生的直接原因。歷史上瑤民為了擺脫封建統治者壓迫剝削,“入山惟恐不高,入林猶憂不密”,居住在荒無人煙的高山野嶺上,官府不管,“王法”不護。他們三家為村,五戶為寨,聚族而居,封閉落后。由于力量弱小,外來強勢的兵匪對他們的侵擾成為經常的事情。顯然,憑借著自己村寨微弱之力是無法與外來兵匪強力相抗衡的,只有聯合起來,結成村寨之間的聯盟,才能抵御外來力量的侵犯,石牌制于是誕生了。
大瑤山瑤族個體家庭出現后,私人的財產成為社會保護的對象,人們用各種戒律來加以保護,任何一種損人利己、偷摸扒竊、不勞而獲的行為,都被視為不道德的。大家都認為,必須制定一些
法律規則對違犯者進行處罰,讓其承擔行為責任,才能保證社會秩序和社會安寧,于是各種強制性、懲罰性的習慣法便應運而生了。
其四,禁忌是石牌律的前身。禁忌是一種伴隨著人類產生而來的歷史現象,在人類的早期階段,由于生產力水平低下,人類對自身的來源、大自然多種災難和奇異現象不能正確解釋,產生了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圖騰崇拜和鬼神崇拜,形成對崇拜對象的敬畏和恐懼,不可觸犯,于是產生禁忌。習慣法是遠古時代遺留下來的禁忌的發展,它的出現已將人們被動地遵循禁忌,變成人們日常的習慣行為和自覺行為。例如,盤瑤石牌律中的“同姓不婚制”,“共祖不過五代不婚”,“姊妹二代不婚”,便是由生育禁忌演變而成的習慣法。原始禁忌和習慣蘊含著石牌法的最一般的規定,邏輯地構成了石牌律的前身。
其五,社老判案制是石牌制的歷史來源。社老是主持社廟事務的神職人員,瑤民信神怕鬼,社老作為溝通人神之間的中介,在瑤族社會里享有很高地位。后來隨著人們鬼神觀念的淡化,社老的神職作用也在弱化,但他們處理糾紛和判案的作用卻日益增加,深受人們尊敬,社老是公正的化身。社老在判案過程中不斷積累案例,從中歸納出一些共同的認識,形成“條規”“戒律”,并把這些戒律一代代相傳,成為“老班規矩”和歷史慣例。這些規矩慣例是石牌制度產生的歷史來源。
其六,石牌律是封建王法在大瑤山虛位的產物。從元明之際瑤族遷入大瑤山,至1940年國民黨廣西省政府武力開化大瑤山的五六百年的時間里,由于山高路陡,金秀大瑤山幾乎是“王不轄,官不管”的政治死角,是一處“化外之地”。但是,大瑤山周圍又是高度文明的地區,處于在漢族、壯族的文化包圍之下,瑤族與漢族、壯族經常發生民族矛盾糾紛。在大瑤山里,各族系之間也因爭山林、土地、河流而發生糾紛沖突。即使是同一村寨的同姓人之間也因經濟地位的差異而形成階級差別,所有這一切都需要有政治法律制度來調整解決。為了便于統一認識,集中意志,處理各種問題,裁定糾紛,有效地管理社會,必須有自己的政治法律制度,石牌制正是在這樣社會的需要中創造出來的。
二、從石牌的組織結構及其功能看國家的起源
摩爾根和恩格斯通過對印第安人易洛魁部落的考察研究,得出印弟安人有氏族、胞族、部落和部落聯盟四種社會組織,為人們探討原始社會組織作出了重要貢獻。大瑤山石牌組織與印弟安人的社會組織有類似之處。它有如下幾種組織類型:
1.家族石牌。大瑤山的瑤族通常是由一個祖先帶著妻兒來此蠻荒之地安家落戶,其后子孫繁衍而形成村寨。這種出自同一祖先的同村人,被稱為“家族”。后來,家族由于子孫繁衍,血緣漸遠,人數眾多,容易產生矛盾糾紛。產生矛盾糾紛時,用血親方式來調解又難以奏效,于是就建立石牌。六巷村的藍姓,1930年建立的《六巷石牌》,這就是家族石牌的代表。由于家庭大多聚族而居,同村共寨,低頭不見抬頭見,產生矛盾糾紛時還是較易于解決,因此,在大瑤山石牌組織中這種鐫字的家族石牌為數并不多。不過,它多以“口頭石牌法”的形式普遍地存在于各村屯之中。這種家族石牌其實就是摩爾根和恩格斯所說的氏族組織。
2.胞族石牌。胞族是指有“兄弟關系”的同族人。大瑤山瑤族形成的另一個特點,是幾個同胞兄弟同時相伴進山,然后分地而居,各自建村立寨。例如寨堡村、楊柳村和將軍村是由莫金一、莫金二、莫金三,這三兄弟分別建立起來的。現存的《寨堡、楊柳、將軍三村石牌》(1786年)等,便是此類石牌。這種胞族石牌其實就是摩爾根和恩格斯所說的胞族組織。
3.姻親石牌。氏族嚴禁內婚(茶山瑤有例外),實行族外婚。這種婚姻溝通了不同血統村寨的聯系。瑤族婚姻的范圍一般較小,同支系的鄰村常是首先考慮的對象。這種婚姻的世代重復,使村寨之間建立起長久的姻親關系,六段、三片、寨堡的蘇、陶、莫三姓便是如此。《滕構石牌》(1906年)和《六拉村三姓石牌》(1911年),便屬此類石牌。
4.支系石牌。大瑤山瑤族分為五個支系,即茶山瑤、坳瑤、花藍瑤、山子瑤和盤瑤,他們在族源、語言和風俗習慣上都有很大的差別。由于存在語言文化的差異,他們在婚姻上也多實行支系內婚制,男女各在自己的支系里找伴侶。近代以來,瑤山經常受到兵匪的攻擾,同時各支系之間為爭奪山林、土地、河流也經常發生爭執械斗。這種隋形一旦發生,人多力量大,家族石牌、胞族石牌和姻親石牌往往起不到應有的作用,于是很有必要建立范圍更寬、人數更多、力量更大的支系石牌。《班愆石牌》(1840年)、《上下泉兩村石牌》(1849)、《坪免石牌》(1867)等便是此類石牌。這種支系石牌其實就是摩爾根和恩格斯所說的部落組織。
5.地緣石牌。前面幾種石牌主要是以血緣親戚關系來組成和劃分的,這種地緣石牌則不同,它是由不同血緣、不同姓氏人們組成的社會聯合。大瑤山瑤族居住的特點是“小聚居,大雜居”,就具體的村寨而言是聚族而居,但就整個大瑤山而言則是大雜居,各種不同血統的人或毗鄰而居,或同村雜居。石牌為保一方平安,必須對居住在同一地域內的所有村寨和各種血統的人加以管理約束。土匪進山攻擾,危害的是整個瑤族的利益,必須動員和組織全體社會力量起來抗爭,否則便達不到確保平安,維護一方社會治安秩序的目的。《六十村石牌》(1914年)、《三十六瑤七十二村大石牌》(1918年)等,便屬于此類石牌。這種地緣石牌其實就是摩爾根和恩格斯所說的部落聯盟組織。
綜上所述,大瑤山石牌組織與摩爾根和恩格斯所描述對易洛魁人的社會組織既有類似之處,又有許多的差別。大瑤山有五種石牌組織,它們組成了倒金字塔型的組織結構,最小的是基層的家族石牌。越往上規模越大,人戶越多,作用亦越大。最高的是《三十六瑤七十二村石牌》。管轄整個大瑤山,其規條是制訂其他石牌法律的藍本,具有大瑤山“憲法”的色彩。這種由小到大,由低到高的社會組織結構,與易洛魁人的社會組織結構也是相似的。
石牌頭人是瑤族群眾對石牌制定者、領導者、監督者的稱呼。“頭人”一詞,始于何時,現難詳考。在《上下卜泉兩村石牌》(1849年)和《低水、平亞、莫村三村石牌》(1853年)中已有“頭人”的稱謂,可知“石牌頭人”的稱謂當不晚于此時。在“村有銘刻,寨有石牌”的年代,各村寨均有頭人。規模大的稱“大石牌頭人”,規模小的稱為“小石牌頭人”。
石牌頭人是如何產生的呢?一是由宗教(道教)的師公和道公轉變而來。二是由公眾推舉有“才德”者來擔任。三是由老頭人培養而成。在近代,由老頭人培養的方式較為常見,老頭人見同村或同姓中有比較聰明,會說話而又有膽識的青年,便帶他去替別人調處爭端,使他熟悉為人排難解紛的辦法和過程之后,就讓他單獨地去替別人辦事,從小事辦起,逐漸到辦大事。時日久了。也就成為頭人。這種由老頭人培養的方式,到后來就有了變化。由于“石牌頭人”是個有權力的職位,于是有的老頭人便“傳內而不傳外”,六拉村劉勝周老頭人便培養了自己的胞弟劉勝紅和孫子劉勝壽當石牌頭人,故當地群眾有“劉家出王”的俗語,這種老頭人培養方式由于私有觀念的發展
已呈現向世襲發展的傾向。
石牌頭人在大瑤山的地位和作用頗為顯赫重要,從制定石牌律,執行石牌意志,調解判案。懲盜御匪,到安排生產,組織宗教祭祀等活動,均由頭人召集主事。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的存在就是石牌制度的存在,他們是石牌的化身,是石牌的人格化。
石牌實行“多元石牌頭人制”,尚未出現“一長制首長”,這是原始社會末期“軍事民主制”的反映。但由于各頭人能力有大小,聲望有高低,所以其地位和作用并不一樣。20世紀20~30年代,六拉村大石牌頭人陶進達威望很高,他刻有一枚“金秀瑤陶進達”的大印章,判案時他口述判決書,別人記錄,然后蓋上他的大印章,說“天靈地準”,不可更改,于是他的聲名遠揚,有“瑤王”之譽,是眾望所歸的領袖人物。1927年,他為組織石牌兵對犯罪的金扶故一家三口的懲罰,向“坪免石牌”各戶征收3塊東毫作為判案費。1940年他組織石牌兵與國民黨軍警開戰,參戰者每人賞5元東毫,賞罰權由他一人定奪,專制王權已露端倪。
石牌頭人初始是義務無償為群眾解決矛盾糾紛的,但是在辦事成功之后,影響傳開,威信樹立,四方群眾請他辦案的多了,他的辦案就由“無償勞動”變成“有償服務”,甚至是“吃了原告吃被告”,收取賄賂,不論哪方輸贏,他皆獲利。有的人甚至利用手中權力,私吞罰款所得。在獲得巨利之后,又用這些錢財買山買田,雇工剝削,成為剝削階級分子。所以,在土地改革中,石牌頭人大多被劃為地主和富農。在六段村8個地主中,有7個是石牌頭人。瑤族石牌頭人集團的蛻化變質是瑤族社會內部階級分化的直接反映。
石牌對違犯石牌律的行為有一套懲治的刑法,輕則教育罰款,重則捆打斃命。早期的石牌律并無刑罰規定。到了清朝道光年問始見處罰條規。此后,石牌的處罰條規越來越明了,懲罰的種類也越來越多,主要有:經濟罰款、游村喊寨、逐出村寨、沒收家產、棍捧毒打、繩索捆吊和死刑。其中經濟罰款是最基本、最常見的懲罰手段。這種情況與中國古代先有刑,后有法,是有差別的,但它更符合法律的演進過程。
石牌行刑有三種方式,一是用石牌兵行刑,二是令受害者本人或其親屬行刑,三是“血親行刑”,由犯人的親屬將犯人處死。其中“血親行刑”在大瑤山較為流行。社會學家指出,血親行刑意味著法律軟弱,表示公共權力軟弱,無力執行其使命。
馬克思主義認為,法律與國家孿生相伴,二者關系密不可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指出,國家制度不同于氏族制度的地方,一是按地區來劃分和組織居民,二是公共權力的設置,三是征收捐稅。
地緣石牌將同一地區的不同血統居民統一起來,實行有效管理,其原則確實是“按地區來劃分它的居民”。軍隊、法律是強制機關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公共權力的重要標志。石牌兵是執行石牌強制職能的重要手段,石牌對盜賊歹徒的懲罰是公共權力行使的直接表現。石牌議事會由各村寨的頭人來組成,對石牌一切重要問題(如審案、宣戰、媾和等)作最后的決定。議事會內部又有具體分工,有負責軍事、財務、后勤、聯絡、司法的“官員”。例如,1939年召開的“反對國民黨開化大瑤山的石牌大會”,全金標負責軍事,陶勝和負責財務,陶玄天負責后勤,金麗生負責聯絡,陶勝文負責執法,陶進達則主持全面工作。該石牌議事會其實行使著中央機關的職能。金秀村是大瑤山瑤族最大的村寨,當時共有57戶人,是全瑤山的政治經濟中心。瑤族俗語“漢人的衙門設在桂林(當時是廣西省的首府在桂林),管得全廣西。瑤人的大石牌設在金秀村,管得全瑤山”,石牌大會經常在此舉行,該村其實是“三十六瑤七十二村石牌”的“首府”。
至于“公民繳納費用——捐稅”,更是早已有之,向過山瑤山丁征收地租,已成慣例。石牌判案中向當事人征收的“草鞋費”、“和解費”,除扣頭人酬勞外,其余歸石牌公有。1927年在懲罰金扶故一家案件中,“坪免石牌議事會”向各戶征收3塊東毫作判安費,1940年與國民黨軍警開戰時,則征收每戶5塊東毫的戰爭費。
我們認為,在清末民初,建立《六十村石牌》(1914年)、《三十六瑤七十二村大石牌》(1918年)之時,石牌組織織已發展到原始社會組織的最高形式——部落聯盟階段,金秀瑤族已處于建立政權的邊緣,已臨近國家的門檻,建立政權的各種條件日益成熟,“石牌政府”已呼之欲出。如果沒有國民黨軍警政權的強行進入大瑤山,隨著大瑤山瑤族社會的私有制、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加劇,按照本民族歷史發展軌跡發展下去,也許它也會造出自己的具備政權機構基本功能的民間機構乃至政權機構。
三、從石牌制的特點看法律和國家產生的初始狀況
石牌制既是軍政組織,又是法律制度,因此它的特點和作用是多方面的。從軍事上看,石牌制是一種軍事聯盟。明清時期,金秀瑤族各集團之間、村與村之間,以及瑤族與漢、壯族之間,由于某種原因,經常發生矛盾糾紛和械斗,抵抗匪幫侵擾的戰斗也經常發生。在這過程中,石牌為了擴大力量,就會召開有關村寨的石牌大會,組織力量,統一意志和行動。石牌組織的規模就在瑤族共同抵御兵匪攻擾的需要中不斷得到擴大。石牌組織越大,這種軍事同盟性質就越明顯。石牌的軍事聯盟和民主制度使它涂上了濃厚的“軍事民主制”色彩。
從政治上看,有如下的特點:
全民性、民主性。在新中國成立之前,金秀大瑤山瑤族階級分化緩慢,并未產生權傾一方的豪強地主,遇事大家商量,石牌的民主性便是在這個基礎上產生。在石牌條文的制定、執行時,無論是富人、窮人,或頭人、民丁,也不分男女老少,人人都可以發表意見,個個可以提出修改方案。對于違法者,大多是采取召集民眾大會,通過民主議事的方式決定處罰。議事時,石牌頭人沒有獨裁的權力,他要充分聽取民眾的意見,按大多數人的意見辦事。如果私行其事。不合眾意,很可能招致民眾的懲處。
排他性、利己性。馬克思主義法學原理告訴我們,法律不是全體社會成員的意志,在階級社會里,并不是每個階級的意志都可以表現為法律,法律只能是在階級斗爭中取得勝利,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占優勢和統治地位的那個階級的意志體現。大瑤山社會的情形也如此。石牌律在制定時,盡管形式民主,人人可以提出自己的見解,個個直抒胸臆,但我們不能由此說石牌法律是“絕對民主”的,“超階級性”的。相反,它的階級性倒是明顯存在的。因為并不是每個人的意見都能刻上石碑,成為條律。能列入條律的大多是山主們的意見,體現山主的意志。就山主們而言,并非所有的山主村寨的意見都能表現為法律,石牌所體現的是山主中的大村重寨的意見。在大村重寨里,說得上話。有威信,有影響的,大多是石牌頭人和地富階級。這一小部分人的意志往往就是石牌的意志。
階級性、剝削性。石牌的階級性有時是赤裸裸地表現為單個地主家庭對農民的剝削壓迫,但更多的是通過族群集團剝削壓迫表現出來。
居住在金秀瑤山五種不同集團的瑤族,他們進山的時間是不相同的。茶山瑤、花藍瑤、坳瑤(這三者被稱為長毛瑤)進山較早,或在元明之際,或在明朝中期即進大瑤山。盤瑤和山子瑤(這
二者被稱為過山瑤)進山時間較晚,大約清嘉慶道光年間才進入大瑤山的。由于他們進入瑤山時間先后的不同,所占有的生產資料和生活空間便不一樣。長毛瑤進山早,利用這一時間優勢不但占有大片的土地、原始森林,而且占據了瑤山里地勢比較開闊、河流比較寬大的山谷河壩,開出大片土質肥厚的水田,并出租山地給過山瑤耕種,他們因此又被稱為“山主”。盤瑤和山子瑤進山較晚,當他們進山時,瑤山的山林河流絕大多數已為長毛瑤號占管轄,他們沒有土地,為了生存只得向山主批租土地耕種,向山主們交租,他們被稱為“山丁”。在20世紀30年代,山主集團和山丁集團的人口幾乎相當,各約八千人。
長毛瑤的水田大多數是自耕,只有少部分出租。山地占有分為三種形式,即全村公有、房族公有和個體家庭私有。這二者公有地被稱為大小“公堂山”。這部分的面積很大,20世紀50年代的調查資料記載:“在全部的山地中,據統計私人占有的形式是少數,而大部分的山地是被各種公有制的形式所占有。”這部分公有土地大多出租給過山瑤耕種,收取一定數量的地租。這部分地租如何處理呢?《廣西金秀大瑤山瑤族社會歷史調查》一書指出:“公堂山每年所收的地租平時很少分配。大部分用在祭祀祖先或作宗教儀式的費用。”公堂山一般由族長或石牌頭人來管理。有的村寨石牌頭人一年有四個月在過山瑤村寨敲榨勒索,但他并不完全是為自己個人搜括,而是為族眾舉行的清明節、春社節、秋社節、游神、過年等活動籌備錢糧。在節日活動舉行時,整個族人不分男女老幼俱來吃食。山租錢糧大多就這樣花銷了。石牌制度保護這種剝削制度,《兩瑤大團石牌》規定:“板(盤)瑤莫怪山主,山丁耕種山主之地,租錢糧納山主收。”這種族群集團剝削,說到底就是階級剝削。原始社會末期出現的階級剝削,或許就是從族眾集團的剝削到家庭的剝削而發展起來的。
從以上石牌政治諸特點分析中可知,石牌制既有全民性、民主性、又有排他性、利己性,還有階級性、剝削性。石牌制是這幾種性質的混合物。這恰好是石牌制的定位,即它是介于原始習慣法與國家法律之間的過渡形態而必然具有的內在屬性。
從法律上看,石牌法具有四個特點:
其一,石牌法是成文法。中國少數民族習慣法大多是“法不成文”,靠口耳相傳,以風俗習慣作為表征。據有的學者研究,云南省25個少數民族,“他們在歷史上創造的法文化成果,就像他們自己一樣豐富多彩”,但除了傣族有部分成文法外,大多是“零散不全”,沒有成文的民族習慣法。金秀瑤族石牌律不是這樣,它的法律條文經民眾討論同意認可之后,用漢字刻(書)寫于石碑、木板和沙紙上,因此它是成文法,它的法律已準法典化了。
其二,石牌法是制定法。中國少數民族習慣法大多具有自發性,其產生、形成是約定俗成的。是在社會生活中逐漸地、自然地形成的。金秀瑤族石牌律不是這樣,它是各村寨的人民在遇到共同問題時,召開村民大會(石牌大會),經頭人提議,眾人討論通過的法律。它是特定群體共同意志的體現,是有意識、有組織制定的行為規范,因此它是制定法。
其三,石牌法是實體法。許多少數民族習慣法在“法無成文”的同時,其組織機構也是懸空的。而金秀石牌不同,它不僅有法律條文,而且還有石牌頭人、石牌會議、石牌兵等組織機構和石牌經費,并時常結合一年農事節慶來顯示自己的存在。石牌制的組織機構及其法律實體性是其他少數民族習慣法所難以比擬的。
這些石牌法特點說明,石牌律不是一般的村規民約,也不是普通的民族習慣法,它是少數民族習慣法的最高階段產物,同時也是國家制定法的初始階段的產物。
最后,我們結合大瑤山瑤族石牌律的情況來回答本文開篇所提出的幾個問題:國家法律(不是民間法)是在原始社會末期的部落聯盟階段產生的。法律產生的主要原因和動力是人們的生活資料生產與再生產,是由于私有制的形成,階級分化,人們在爭奪生活資料和生存空間過程中逐步形成的。法律最初形式是習俗,它經歷了由習俗一習慣法一成文法一制定法的發展過程。最初人們行為規范大都是由習俗來規定的,習俗是文明社會法律的胚胎。在人們對習俗進行了一定的選擇之后,將習俗上升為普遍遵守的規范,并賦予強制力,這時的習俗就具有了法律性質,人們稱之為習慣法。因此,習慣法可以看作是法律的初級形式。隨著社會發展變化,在習慣法無法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時,人們便在此基礎上有針對性地制定新的規則,這些由政治組織或國家有意識地制定出的。借助武裝力量為強制力,以保證法律施行就是國家成文法和制定法。中國法律史是循著這一條軌跡發展演變的。因此,對石牌法律的來源、發展和特點的研究,有利于我們加深對中國法律史發展規律的認識。
參考文獻:
[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M],《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2][法]孟德斯鳩著、張雁深譯:《論法的精神》[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
[3][法]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
[4][英]梅因:《古代法》[M],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
[5][美]霍內爾著、周勇譯:《初民的法律》[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杜,1993年版
[6]張晉藩主編:《中國法制史》[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杜,2007年
[7]周長齡:《法律的起源》[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7年
責任編輯:邵志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