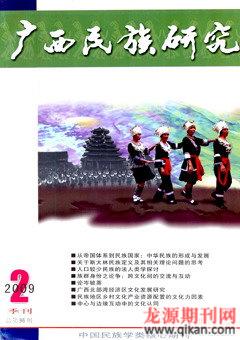中心與邊緣互動中的文化認同
摘要:中心與邊緣是一個相對概念,它體現了一個社會存在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不平衡狀態。本文以羌族旅游為研究個案,通過中心/現代性與邊緣/傳統性的語境分析,再現了在旅游過程中,羌族作為地方傳統性的異族形象不斷被來自中心的旅游者所強化和認同,另一方面羌族自身又在不斷吸納現代性的過程中有意識地強化傳統性的異族形象的復雜過程,從而揭示出中心與邊緣在推進現代性與保持傳統性的矛盾過程中對羌族文化傳承與發展所帶來的雙重影響。
關鍵詞:中心一邊緣;羌族旅游;文化認同
作者:吳其付,四川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成都,610066
中圖分類號:F590.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454X(2009)02-0191-008
中心與邊緣是一個相對概念,它體現了一個社會存在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不平衡狀態。美國社會學家希爾斯和安東尼奧葛蘭西指出,每個社會都有一個發出強大影響的文化中心,中心有著霸權地位,有著話語權力,它支配著社會的符號秩序、價值和信仰,代表的是一種獨一無二的心理、政治、經濟、文化優勢。中心通過社會整合的方式不斷將中心的文化價值滲透到邊緣,從而將邊緣納入到中心的勢力范圍。
由于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不平衡,中國也存在著一種相對意義上的中心與邊緣。如經濟發達的東部地區是中心,而西部欠發達地區便是邊緣;漢族的強大也決定了漢族及其代表的文化在社會上的中心地位,而少數民族及其代表的文化就處于一種邊緣地位。李偉教授認為我國少數民族文化的現實存在形態便是一種文化邊緣地帶狀態。他指出文化邊緣地帶并非借用了后現代主義具有反對文化殖民主義色彩的“中心文化”與“邊緣文化”概念,而是從區位視角說明我國民族文化格局的特質性含義,一是文化邊緣地帶表明我國少數民族在地域上的分布狀態;二是文化邊緣地帶強調少數民族與主體民族之間現實的文化區別,特別是指其經濟相對封閉落后的發展狀態,空間上遠離發達地區,時間上遠離現代文明;三是文化邊緣地帶試圖概括各民族歷時性文化演進中的地位比較特征。
本文從民族旅游的角度來研究文化接觸引起的地方文化變遷與傳承,有一個基本的判斷前提,那就是外來文化與地方文化之間必然存在著文化的強勢與弱勢之分,存在著中心與邊緣的相對地位。在這里,中心代表的是經濟發達的中心城市及其強勢文化,更多的是與現代性和全球化相連,而邊緣代表的是經濟較為落后的民族地區及其弱勢文化,更多的是與傳統性和地方性相連。具體到羌族的旅游研究而言,旅游者便是中心,代表著現代性,羌族便是邊緣,代表著傳統性。
隨著羌族旅游的開發,由旅游者帶來的現代性必將對羌族的傳統性形成強有力的沖擊,旅游業將調動政府、市場、大眾文化等力量將現代性的影響推進到羌族社會的各個角落,從而將羌族不斷納入到現代化的進程之中。但正如現代化在推進政治經濟一體化的同時,也在強調文化的多元化一樣,作為現代性的旅游也同樣具有這樣的特點,一方面要求地方提供各種現代化的娛樂休閑設施和舒適安逸的現代生活,另一方面又要求地方保持傳統性和原始性,為旅游者提供一種不同于自己日常生活的異域文化體驗。所以,正是民族旅游這種矛盾性形成了一種中心與邊緣互動下的羌族文化認同,即一方面作為邊緣地方的羌族要吸收外來文化的現代性成分,另一方面又要極力保持自己傳統文化的母質和特色,抵御現代性帶來的文化同化,從而形成一種新的文化形態——次生文化。
本文將通過中心/現代性與邊緣/傳統性的語境分析,揭示出中心與邊緣在推進現代性與保持傳統性的矛盾過程中對羌族文化傳承與發展的雙重影響及其引起的文化認同的強化。
一、現代性與民族旅游
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生產力的發展,社會不斷向著現代性的趨勢前進。現代性在改善著我們生活的同時,也在摧殘著我們的人性與自由。現代性將我們帶向了兩個極端化的生存境況之中,一個是拉著我們不停地“往前走”,另一個是促使著我們不斷地“向回望”。“向前走”的境況要求我們要以新的工業化、集約化、規模化、標準化等力量摧毀社會里阻礙現代性發展的各種傳統文化元素;“向回望”的境況又要求我們對往昔過去進行追憶和珍愛,以及對即將逝去的傳統文化的留戀與維持。“向前走”與“向回望”構成了我們對現代性生存條件的好惡交織。正如王寧所說,現代性所帶來的“副作用”或負面效應,諸如自然的消失、環境污染的加劇、生活節奏的加快,隨技術分工而來的工作性質的程式化、大眾社會中人情的淡漠以及矯飾和虛情假意的盛行等,使人們對現代性有所憎恨。而旅游這種逃逸日常生活價值中心的方式恰好成為了我們對于現代性好惡交織的發泄與解脫,以致于成為了現代社會中人們一種普遍的生活方式。
在現代社會里,工業化、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使人們長期處于一種單調、疲憊、壓抑的環境之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之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得日益緊張和淡漠,人的內心變得越來越孤獨和失落。人們無法通過彼此之間的溝通和交流來改善自身的生存境況,因此只好選擇外出旅游來尋求解脫。旅游將人們帶離自己日常工作生活的地方,去遠處尋找另一種生活的價值和意義。實現自我的回歸。在旅游過程中,人們通過日常生活場景的轉換,能夠尋求到日常生活中所缺乏的自然、簡樸和真我的精神環境,以及異于日常生活的另一種生活方式和節奏。
現代社會存在著不同形式的旅游模式,瓦倫·史密斯將其劃分為民族旅游、文化旅游、環境旅游、歷史旅游、娛樂型旅游等五種形式,其中最受人們青睞的是民族旅游模式。當原生農耕文明架構下的許多文化形態在現代性的推進下漸漸遠去和消失的時候,負載著傳統民俗和文化多樣性的偏遠民族地區便成為了人們懷舊體驗的主要歸宿。民族地區有保存完好的自然生態環境,村落與自然構成了一種天人合一的生存關系。人們生活在這樣優美和諧的人文環境中,感到心曠神怡、精神得到極大放松;各種傳統習俗在村落中保存完好,如傳統的生產方式、民居建筑、宗教儀式、節日慶典、民俗生活等,這些具有獨特價值的民族文化遺產,能夠給人們帶來對往昔的追憶與回味。對傳統的留戀與珍愛。民族地區有著鮮明的異族文化特色,如宗教信仰、巫術儀式、語言文字、服飾歌舞、飲食起居、生產工具等,向人們展示了一個與自己文化完全不同的“異文化”形態,與旅游者的文化體系形成了迥然不同的對照。
在民族地區,優美的山水風光、傳統古老的農耕生活、迥然不同的民情風俗,對生活在現代性中的人們產生著巨大的吸引力。劉丹萍通過“雅虎中國”調查旅游者的消費行為發現,中國西部那些社會經濟相對落后,傳統農耕文化、少數民族文化等保存相對完好的民族村寨,吸引的往往就是那些平常工作生活在大都市里、深受現代性影響的“先鋒旅游者”。
民族旅游主要是以地方族群的“異”文化為主要旅游吸引物,由于民族地區大都是山區,自然生態環境和傳統文化都保存得相對完好,因此能夠滿足人們多方面的旅游需求,如享受良好的生態環境,感受傳統的農村生活,體驗獨特的民情風俗。民族地區潔凈的空氣和寧靜的山水、熱情的氛
圍和純樸的村民,豐富多彩的民俗節慶,獨具特色的民族景觀,以及各種備受尊重的接待禮儀等,彌補了人們日常生活中所缺失的生態環境和人情友誼,消除了人們的緊張心理,帶給了人們快樂與激情。人們在旅游中尋求到了真實的自我,以及暫時擺脫了現代性的壓迫。
在民族旅游中,旅游者還可以通過各種神話傳說、英雄故事、文化遺跡等去探尋遠古的歷史、追憶民族開天辟地的壯舉。同時,他們還可以選擇當地美麗的風景、傳統的民族服飾等將自己的旅行體驗浪漫化、異國情調化和理想化,由此將旅游地居民塑造成與自己截然不同的“他者”形象。總之,民族旅游制造了能夠把人們暫時帶回昨天的生活中去的幻想,制造了人們心目中故鄉的影像,也為人們再現了一個在現代化和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依然存在的男耕女織的田園景觀。
羌族生活在川西高原地區,由于山高路陡,地理環境封閉,經濟不發達,仍舊保留著傳統、古樸的文化習俗與宗教信仰。這些處于邊遠地區的邊緣民族,正是生活在工業化時代,深受現代文明影響的旅游者極力尋求的具有原真性、神秘性、獨特性的異域風情的他者,是旅游者逃逸枯燥生活,渴求異質文化體驗的旅游圖景。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以桃坪羌寨為代表的旅游開發。將羌族古老歷史和獨特建筑展現在旅游者的面前,激起了他們對羌族神秘、傳統、原始的邊緣文化的追捧。
二、中心對邊緣的審視一羌寨中的旅游
羌族主要分布在岷江上游地區,是古代羌人的后代,至今還保留著許多傳統的古羌人習俗。羌族有著悠久的歷史,在幾千年的演變過程中,創造了許多偉大的業績,也充滿了許多苦難的歷史和不老的傳說。古羌人與華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族源關系又賦予了羌族更多的神秘色彩。在現代化不斷沖擊著人們傳統生活方式的今天,古老的宗教信仰、傳統的民間節慶儀式、風格獨特的民族服飾、熱情多姿的莎朗歌舞,以及巍峨高大的石砌碉樓,仍舊在羌民日常生活中保持完好,昭顯出羌寨傳統、神秘的異族風情。這種異族風情激發了身處繁華、現代都市旅游者的獵奇心理,吸引著中心的他們向邊緣的羌地移動。
在羌族地區,理縣的桃坪羌寨和汶川的蘿卜寨,在羌族傳統文化的保存和挖掘展示方面受到了旅游者的關注。其中來自香港、臺灣、新加坡、日本、韓國等現代化程度很高的游客成為了羌寨主要的觀光客。對于這些長期生活在現代文明之中的海外游客而言,美麗的鄉村、芳香的泥土、神奇的端公、艷麗的服飾、熱情的村民、以及傳統的生活,構成了一幅他們難以想象的“異國風情”。
這些海外游客,大都具有身份上的共性,身著名牌服飾、頭戴遮陽帽,胸前掛著數碼相機。有的還帶著墨鏡,操著很難聽懂的漢語,相互交談時還夾雜著潮州語,一些小游客還操著流利的外語與當地的小孩打招呼,這一切都似乎昭顯著他們“現代性與先進性”的優越感。而羌寨里黃泥巴顏色的土坯房、精通巫術的端公、種田荷鋤的老農、穿著羌族服飾的村婦、吃草啄食的老牛與雞鴨,在他們眼中構成是一種“傳統與落后”的邊緣圖景。深受現代性影響的他們,對羌寨里“傳統與原始”表現出的是“一無所知”的好奇心。他們的神情和言語顯示出的是中心對邊緣的固有印象和刻板認知,即邊緣代表著貧窮、愚昧、落后、野蠻,也代表著純樸、原始、神秘、傳統。當現代性的他們走入傳統性的寨子時,現代性又開始對傳統性進行新的詮釋和想象。
這些海外游客們在羌族導游的帶領下,沿著長長的碎石路進入村寨。當他們經過長滿玉米稈的黃土地時,一個碩大的土堆,以及土堆前擺放著各色精美漂亮的大花環,引起了他們的注意,于是他們開始詢問導游是些什么東西。當他們得知這是羌人死后埋葬的墳墓,并且里面還真正的埋著死去的人,他們覺得非常驚訝,更是一種難以置信的表情。此時,他們開始依據現代化的生活經歷對羌族的奇異進行著比對。他們認為人死后都是經過火化的,放在靈堂里供奉著的,而不是埋在地里的。在進行了一番駐足觀賞之后,他們紛紛拿起手中的相機,對著這個彰顯著“傳統古老”生存方式的土堆一陣猛拍。作為長期生活在競爭、欺詐、冷漠的現代性環境中的這些旅游者來說,村寨居民的過分熱情和勤勞美德也成了他們懷疑與警惕的對象。當村寨里擺攤出售工藝品的婦女,一邊熱情地與他們打著招呼,一邊不停的做著針線活時,他們充滿疑惑的詢問導游,這些是不是景區經過精心排練過,故意表演給他們看的生活場景。他們知道羊是羌族的圣物,羌族是牧羊人的代稱,但他們將這種古老的文化內涵與現實生活進行了想象與聯系,他們以為現在每戶羌民家里都圈養有許許多多的羊。因此,當他們進入羌民家里參觀時,首先想到的就是詢問導游羊在哪兒,能看看嗎?當導游告訴他們,羊不在家里,而是在山上時,他們臉上露出的是相當遺憾的表情。或許他們在旅途中,已經在想象在羌民心中具有神圣意義的羊到底有什么神奇之處,可是在羌寨沒有看到一頭羊的旅游經歷或多或少讓他們感到遺憾。羌民家里日常做飯的灶臺和大鍋被他們當成了一種文物和古董,當導游告訴他們這些東西是羌民日常做飯的工具時,他們露出了難以置信的表情,連續的問導游,今天早上才做過的嗎?當得到明確的答復后,他們又沿著灶沿仔細的看了看,摸了摸,并用相機使勁地拍照,最后發出感嘆:沒想到家里還很干凈。對掛在灶沿上的老臘肉,他們更是驚奇,那一塊塊長條形的豬膘,在煙火的熏陶下變得黝黑發亮,發出陣陣香味,他們就問這就是村民日常吃的東西嗎?在他們看來,這些東西如同博物館里展示的文物一樣,是用來看,不是用來吃的。當得知這些東西是村民日常的生活食品時,他們對著老臘肉互相交頭接耳,評頭論足,又將隨身攜帶的相機、攝像機對著這些東西一陣猛拍。這些海外旅游者對中國古代的歷史有一些模糊的了解,他們知道中國歷史上的炎帝和治水的大禹,但卻并不知道他們今天所到的羌寨,所看到的羌民就是炎帝和大禹的后代。當導游將羌族的祖先傳說與他們所認知的炎帝與大禹對接后,他們對羌族的游牧與遷徙、對羌族與華夏和炎黃的關系有了新的認識,同時也增加了他們這次旅游的符號意義。因為他們參觀了中國最古老、最偉大的民族生活之地,而且這里依舊保留著古老民族幾千年不變的歷史習俗。
旅游者逃逸現代生活的心理需求和不斷尋求“傳統落后”的民族風情的旅游行為,促使他們不斷的從經濟文化發達的中心向傳統神秘的邊緣擴散。她們對傳統的刻板印象在他們的旅游行為不斷得到詮釋,強化著現代性對傳統性的理解、認知和想象。對旅游者而言,邊緣的傳統與落后又強化他們概念中我族的現代、進步、都市、理性和主流地位。
三、邊緣自身認同的強化——羌寨中的文化展演
旅游者在民族地區所要尋求的是現代性所缺失的純樸、寧靜、輕松的環境和異域的民族風情,觀賞到古老、落后、鄉間、迷信、少數、獨特的“傳統文化”。旅游者是為了體驗羌族文化的異質性和真實性而到羌寨旅游的。因此,對于地方民族的羌族來說,保持傳統性的習俗,突出具有標志性的文化符號景觀,對強化羌族“邊緣性”的異族身份特別重要。
碉樓是傳統羌寨重要的歷史文化景觀,是旅游者眼中的羌寨符號標志,它體現了羌人的建筑智
慧。游客被吸引到羌寨旅游,很多是因羌寨中矗立的碉樓傳遞出的古老、神秘意境引起了他們的獵奇心。桃坪羌寨如果沒有了碉樓,對旅游者而言便沒有了吸引力,同樣對于黑虎羌寨也是如此,如果沒有那么多的碉樓,坐落在半山腰的羌寨也是不會引起游客的注意。所以,對桃坪羌寨和黑虎羌寨而言,保護好碉樓景觀就是一種傳承羌族文化、體現我族認同的表現。桃坪羌寨現有的四座碉樓,有二座是重新修建的。為了保持羌寨原有的景觀標志,政府支持村民重新修復碉樓。桃坪羌寨和黑虎羌寨正在以其獨特的建筑文化景觀——碉樓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目前已經納入了國家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預備名單。在2000年,桃坪羌寨還邀請了世界遺產保護委員會專家到羌寨實地考察。這些保護文化遺產的舉措都是反映了羌族力圖依托羌族古老悠久的文化底蘊,走進公眾的視野。展示出獨具魅力的異族形象。
羌族傳統的住宅都是用石塊建造成的碉房,它是羌族古老的居住模式,體現了羌族對自然環境的理解與認知。因此,延續和傳承羌族文化,保持羌寨原有的石砌碉房是一種必不可少的手段。雖然隨著時代的發展,碉房在功能上已經難以滿足現實的需求,但長期以來形成的外觀已經在人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對于地方政府和村民來說,不管對碉房的內部進行如何的裝飾與改造,其外觀和樣式都要保持原有的風格。而一旦出現居民不自覺的破壞這種建筑格調,政府也將堅決給與拆除,否則難保羌寨特色。桃坪羌寨新村的建設也是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進行的,其建筑布局、建筑材料、建筑樣式都與老寨子嚴格保持一致,互現映襯。并且在對羌族傳統文化的體現上更為注重,元素更為豐富,如羌族古老的文化符號如白石、羊頭等在房屋的建筑外墻和內部裝飾上都得到有意識的展示。新村的寨門也以羌族的碉樓作為最有標志性的建筑景觀,羌族的羊圖騰崇拜非常醒目的鐫刻在寨門上。
羌裝是羌族身份的外在標志,但在旅游開發前,政府并沒有著重強調羌民必須穿羌族服裝。但是旅游開發后,政府有意識的要求各羌寨村民要擁有自己的羌族服裝,要主動穿羌族服裝。并且有些地方,由政府出錢給每戶羌民制作羌族服裝。除了政府有意識強化羌族身份外,旅游村寨的羌民也在日常的旅游服務接待過程中身著羌族服裝,有意識的強化自己的羌族身份。其中婦女又是這種身份強化的主體,在很多羌寨,都可以看到許多羌族婦女穿著各種顏色的羌族服裝。她們不僅是身份的體現者,也是羌族服裝傳統制作手藝的繼承者和創新者,不管是在擺攤的地方,還是在路上,都能看見羌族婦女制作服裝、繡制鞋襪的場景。對于羌族歌舞表演者而言,他們的羌族服裝更具有傳統特色,不僅做工精細,而且在裝飾品、顏色等搭配上更為講究,因為他們要經常外出演出。因此更需要通過本族服飾展示強化在外族心目中的羌族形象。
羌族的傳統歌舞是莎朗,是羌民平時自娛自樂的活動,表演性和觀賞性不強。為了形成與藏族鍋莊有明顯差異的羌族特色歌舞,政府和專家對民間的莎朗在舞姿和曲調上都進行了整理和發掘。專門編排了一系列舞蹈曲目,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羌族歌舞,每個曲目都力爭表現出羌族悠久的歷史與文化。政府還將這套完整的羌族歌舞在羌區推廣,形成羌寨居民都能跳出傳統地道的羌族莎朗的意象。各旅游村寨成立了專門用于演出的歌舞表演隊,招聘年輕人和老年人進行排練和演出。
羌笛是羌族最為古老的樂器,充滿滄桑與悲涼。不過,隨著歷史的變遷,羌笛在羌族地區已很難看到和聽到,也很少有人能夠制作和演奏羌笛了。但是旅游的需求又使得羌笛的制作和演奏技巧得到重新傳承與延續,并且經過地方的積極努力保護,羌笛被國家評為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羌笛也在各種重大的節慶活動中作為羌族原生態的文化得到了展演。
羌歷年是羌族的傳統民族節日,每年十月初一,羌族地區都要在羌歷年舉辦不同程度的慶祝活動。隨著旅游開發的需要,政府對羌歷年越來越重視,把它作為了一個宣傳羌族文化特色,強化本族凝聚力的一種方式。不僅縣上要舉行慶祝活動,各鄉、鎮也都要舉行傳統的轉山、祭山活動。在慶祝活動動上,將羌族的端公、舞龍、器樂、歌舞等傳統的民間儀式和習俗進行展演,并在慶祝活動中邀請各級媒體參與拍攝、宣傳,最大限度的向外界展示出羌族的異族風情。羌族地區不僅通過傳統的民族節慶強化本族特色,而且還通過各種旅游文化節來喚起外界對羌族文化的關注,如蘿卜寨舉辦的高原古羌文化旅游節,桃坪羌寨舉辦的花兒納吉節,理縣的紅葉節等,政府希望通過這些節慶活動的舉辦,提升羌族文化的知名度。地方還善于借助各種傳媒手段來強化羌族熱情、純樸、傳統等形象。如理縣的羌寨姑娘爾瑪依娜成為網絡紅人天仙妹妹后,激起了人們對羌族風情的追捧,理縣政府邀請天仙妹妹作為羌族的旅游形象大使,現在在各種網絡、流行期刊、報紙等都能看到天仙妹妹的身影,而且還入選了北京2008年奧運火炬接力手的選拔。
在村寨日常生活中,各寨各村羌族民眾的衣食起居、季節性生產活動、宗教儀式等民間儀式、節慶活動也在不斷進行強化。如茂縣牛尾巴寨正月初七“人過年”的儀式中,年輕女子蕩秋千,年輕女子舞龍,村中長老開酒罐請客神,男女環繞跳鍋莊舞,以及男子儀式性的演示出征,戰爭過程勝利歸來,婦女倒酒敬戰士等場景經常出現。現在,羌族的很多民間節慶都被國家評為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如瓦爾俄足節、卡斯達溫舞。雖然是為了保護傳統文化,但正是通過這種申報方式激起了外界對羌族文化的重視與關注。
各村寨的歌舞表演對強化羌文化在外族中的印象也十分重要,通過她們的表演,獲得中心對傳統的認可與贊賞。如北川五龍寨的舞蹈隊,其原生態的節目在省內外很有名氣,經常被邀請參加省上、市上的各種活動。如中國地方志評審工作會在成都舉行,省上專門邀請五龍寨的姑娘小伙子到成都去進行專場表演,會場標語對聯“全國修志精英匯聚蜀都,北川羌族兒女獻藝蓉城”顯示了外界對于羌族文化的贊賞。又如四川省在西南民族大學召開禹羌文化和旅游文化研討會,又邀請五龍寨的表演隊去獻藝,展示古羌文化。2007年春天,綿陽市的古羌茶園舉行采茶開園儀式,五龍寨地表演隊又去向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游客表演羌山采茶舞。五龍寨的歌舞隊參加全國在山西舉行的古樂古舞展演,獲得了山花入圍獎。
正是通過以上方式,地方在向旅游者展演羌族傳統燦爛的文化同時,也在旅游者心目中強化出了羌族古老神秘、堅守傳統不隨波逐流的我族意象。
四、邊緣與中心的互動——次生文化的形成
民族旅游制造了一個中心與邊緣、現代與傳統交流對話的平臺,這種對話交流在民族地區形成了一種新的文化形態,那就是次生文化。次生文化是以邊緣民族的原生文化為基礎,集邊緣文化與中心文化要素于一身的新文化形態。
次生文化在民族地區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源于民族旅游的矛盾性。這種矛盾性表現為旅游既要讓地方接受來自中心的“標準化和現代化”,又要讓地方保持邊緣的“傳統性與異質性”。“標準化和現代化,,表現為來自中心的旅游者常常以某種標準化的“硬件”和“軟件”去要求民族旅游村寨提供安全舒適的服務和享受。“傳統性與異質性”表現為地方要能經受住外來文化的沖擊,保持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