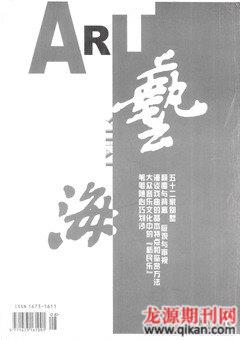花鼓戲音樂創作的繼承、借鑒與革新
胡勁松
湖南花鼓戲傳統音樂因地域、人情、生活習慣等因素,形成了以打儺腔、洞腔、川調、民間小調為主的聲調體系,各個聲腔又衍生了多種地方性風格的曲調、曲牌,每個曲調,又由不同調式、不同旋律組成。這些傳統音樂從民間的民歌、山歌、地花鼓等音調中吸收了無比豐富的營養,也是歷代戲曲藝人在繼承與突破中,以口頭傳承的方式,世代累積的結果。在風格上有的氣氛粗獷、喧囂熱鬧;有的清淡秀雅、悠揚流暢;有時輕快活潑、喜慶跳躍;有的音調如訴如泣,極富感染力。花鼓戲傳統音樂的選材大部分來自民間,因與群眾的生活息息相關,形成了濃厚的地方風味和生活氣息,所以深受湖南人民的喜愛。
湖南各地城市中、老年人和農村的大部分農民,他們喜歡傳統的花鼓戲曲調中有板有眼、結構極其規整的上下句和冗長跌宕、粗獷、高亢的各種拖腔,在勞作中、閑之余吟唱花鼓調子,被視為主要的精神享受。
隨著社會的發展,時代的進步,花鼓戲音樂正經受著時代的挑戰、要求和影響,觀眾對花鼓戲音樂的審美標準、審美情趣有了變化,他們的審美習慣有了新的選擇和要求。同一個戲,在不同的地方(相對城市與農村)演出,所產生的演出效果迥然不同。城市中的青年人、知識分子擁戴奔騰和歡快的跳蕩節奏和優美抒情、清新典雅的曲調旋律,觀眾多層次的審美需求,產生了縱向隸屬傳統與橫向聯系的沖突。如何讓花鼓戲音樂表現當代生活,適應時代發展步伐;如何擺脫戲曲觀眾結構的老齡化,讓更多年輕人群體加入到戲曲殿堂;如何創作出旋律美、韻味美、個性美并受群眾歡迎的花鼓戲音樂,對從事花鼓戲音樂創作者提出了新的課題,花鼓戲音樂的改革成了必然趨勢。
花鼓戲音樂的改革將現時的花鼓戲音樂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固守傳統、不求變異不對,拋棄傳統而求突變也不對,湖南花鼓戲應在發展傳統音調的基礎上體現時代特色,在體現時代特色的前提下,革新傳統音調。新中國成立以來,花鼓戲前輩們的音樂創作對花鼓戲的革新有著借鑒和集成的價值,它的創作技法的革新是成功的。在創作中既沒有輕率地拋棄傳統、照搬西洋及其它劇種的模式與創作技法,也沒有死抱傳統、排斥西洋與兄弟劇種的先進技法,而是有主見地、不拘一格地兼容并蓄。新的技巧手法,在前輩們的實踐創作中也得到了良好的體現,創作了許多膾炙人口、在湖南乃至全國廣為流傳的經典曲目、經典唱段。
創作劇目《喜脈案》,在繼承和發揚傳統曲調“花石調”其結構功能的基礎上,運用西洋作曲技法中主題旋律發展的方法,設計人物主題音樂,將它們貫穿全劇,使全劇音樂風格十分統一,而人物唱腔音樂既有花鼓特色,又具有優美抒情、清新靈動、個性鮮明的特點、再用移位、離調、轉調、旋律擴展等手法,依次發展出眾多的變體形式,以貫串在劇中唱腔、過門及場景音樂中。
轉調技法作為構成音樂色彩對比、推動旋律發展、曲式變化的手段之一,在花鼓戲音樂創作中得到了很好的運用。現代戲《野鴨洲》中“金堤柳林披薄紗”唱段,首先用明朗的C調描寫荷花充滿喜悅的心情尋找柳正剛,然后轉入屬調G調,以突出荷花看到了柳正剛在勞累一天后還忘我地學習而產生強烈的愛慕之情,最后又轉回C調,以表達荷花對柳正剛堅定的愛念。通過轉調,拓展了樂思的發展空間,準確的描寫了荷花起伏不平的內心變化,豐富了音樂的表現力。這無異于在花鼓戲音樂創作技巧中打開了一扇新的窗戶。
《補鍋》中的“手拉風箱”唱段,唱腔旋律取材于本劇種的洞腔,通過吸收湘南的民歌音調融會貫通于唱腔中,新的曲調不僅散發著濃郁的花鼓風格,而且旋律充滿了新的活力,曲調面貌煥然一新。
《花燭恨》中王大人唱段,在板式結構上,打破了傳統的上下句格式,借鑒兄弟劇種多樣的結構,并糅合“還魂調”、“勸夫調”、“南數板”傳統曲調,發展出散板、快板、慢板、數板、垛板、散板全新的板式結構,使音樂更好地為劇情、人物服務。
在前輩們花鼓戲音樂的創作中,還有很多手法和技巧,如通過改變傳統曲調調式骨干音的“換骨十字調”;糅合多個傳統曲調組成新的曲調;運用民間音調創立新的曲調等。通過他們幾十年努力,逐步形成了湖南花鼓戲劇院的音樂改革路子,為我們今后花鼓戲音樂創作積累了很多可借鑒的寶貴經驗。實踐證明:新技法的不斷使用,在傳統的基礎上連綿出新,也可以形成新的傳統,使之保存下來。
花鼓戲音樂的革新,只有在把握傳統“根”的基礎上,廣泛吸收其它藝術門類的養份,大膽借鑒西洋現代作曲技法,才能使花鼓戲音樂這顆生命之樹,枝繁葉茂,碩果累累!
(作者單位:湖南省花鼓戲劇院)
責任編輯: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