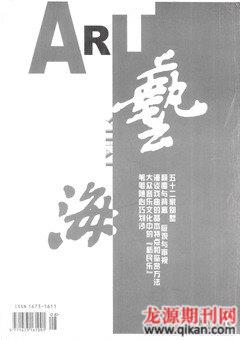云南母語音樂教育的現實困境與理論對策
馬 卿
文化的交流是一種雙向的運動,而不應該是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強行輸入,亦或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被動接受。回顧中國近現代音樂教育發展史,我們不難看出,由于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原因,在我們還沒有做好準備的時候,西方的音樂文化就以一種勢如破竹之勢占據我國音樂教育的主流地位。從某種層面來說,西方一元音樂文化的輸入給我國音樂教育的發展注入了活力,使我國的音樂教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從另一方面來講,我們在享受這些豐碩成果的同時,又不得不面對這種音樂文化的輸入給我國音樂教育留下的“軟傷”和“硬傷”。隨著文化價值相對論的提出以及國內外音樂教育相關政策的出臺,人們開始重新審視本民族內部的文化傳統。
一、 國內外母語音樂教育歷史及其現狀
母語音樂作為本民族自身文化的產物,逐漸受到各個國家的青睞。國內音樂教育界的相關學者大都發現,在面對西方和音樂文化的同時,我們自己的音樂文化在哪里?1995年的“第六屆國民音樂教育改革研討會”專門以“中華文化為母語的音樂教育”為題進行了研討。到會的民族音樂理論及表演藝術方面的專家、學者就中華文化為母語音樂教育的意義與界定、母語音樂教育的困境及建構、規劃、實施等問題進行了探討。如王耀華教授曾提出“中華文化為母語的音樂教育應提供大課堂(社會的民族音樂環境)、中課堂(學校課外民族音樂活動)、小課堂(民族音樂各種課的教學)的結合。中華文化為母語的音樂教育應包括中國音樂的哲學基礎、思維方式、美學、形態學、價值觀念等。”李妲娜認為:“中華文化為母語的國民音樂教育應把體現民族文化氣質和民族音樂形式的曲目納入音樂教材”等等。
在此基礎上,各高校也都有了母語音樂教育的實踐嘗試。如貴州大學藝術學院開設了侗族大歌班,呼倫貝爾學院音樂系設立蒙古長調大專班、云南民族學院民族藝術系也對本土音樂文化的傳承進行探索,福建師范大學與泉州師范學院正在開設的南音演唱傳習班,江西贛州學院和梅州嘉應學院先后將客家山歌和廣東漢樂引進課堂等等,我國的《中小學音樂教育課程標準》也做出了“弘揚民族音樂”等明確的規定,各地中小學也在不斷的開發適合本地區的校本課程。諸如此類的實踐嘗試無疑都是很好的開端。
然而,我國大雜居、小聚居、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具體國情,決定了實施母語音樂教育不會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統一模式,不同地區、不同民族在母語音樂教育的實施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會遇到各種不盡相同的困難與處境。云南這一地處祖國邊陲的多民族省份,在母語音樂教育實施的過程中,也就不可避免的遇到了諸多的現實困境。
二、 云南實施母語音樂教育的現實困境分析
1、云南音樂文化多樣性難以有效闡釋的困境
云南有26個民族,25個少數民族,各民族豐富多彩的風俗民情是一個活的歷史博物館。每一個民族的衣、食、住、行及婚戀、喪葬、生育、節典、禮儀、語言、文字、圖騰、宗教、禁忌、審美莫不結撰為豐富多彩的文化鏈。納西族的東巴文化、大理的白族文化、傣族的貝葉文化、彝族的貝瑪文化……潑水節、刀桿節、插花節、火把節莫不獨具特色,深邃而幽遠。伴隨著這些節慶、儀式的是豐富而富于特色的音樂舞蹈。因此,云南又被譽為“歌的故鄉,舞的海洋”。世世代代的人們把整個生命的意義都投入到美妙的歌聲和神秘的舞蹈當中,那里承載著他們祖祖輩輩與天斗、與地斗、與人處的生命歷史信息,是他們的歷史、生命、精神外化的結晶。
云南母語音樂文化的形式不可謂不豐富。從一方面來說,這些都為母語音樂教育提供了可滋利用的潛在文化資源,但另一方面,這些多樣化的音樂文化藝術形式在當今的主流音樂教育中,又由于其復雜多變而缺乏一種便于推廣、傳承的有效途徑。從現代教學論的角度來說,一種缺乏自身闡釋能力的教育資源是不能被有效的用于學校教學過程當中的。因而,在我們的學校音樂教育中,當面對云南豐富多樣的教育資源的時候,往往會顯得束手無策。
2、 云南母語音樂教育在西方音樂中心論影響下的困境
20世紀中國的音樂教育基本上經歷了四次大的歷史變革,這四次大的歷史變革影響到了中國各個地方的音樂教育,云南亦不例外。在這四次大的歷史變革中,強勢一方以科學、高雅、先進等符號標簽長驅直入,而弱勢一方則以心理上的頂禮膜拜,行為上的被動接受,不折不扣的全盤接收。近一個世紀以來在這種文化慣性的影響下,大多數師生形成了西方音樂文化是先進的文化,而中國的音樂則是落后的粗俗的、不科學的文化觀念,以致我國學校的音樂教育難以擺脫西方殖民文化的后殖民怪圈。
云南雖處我國西南邊陲,但同樣受此影響。如何擺脫西方音樂中心論的影響,是云南構建母語音樂教育必須首先面對的問題。
3、 漢族傳統音樂文化對云南母語音樂教育體系構建的影響
按照文化滲透理論來說,強勢文化會伴隨著經濟、政治等相關強勢媒介逐漸滲透、改變弱勢一方。而我國漢族文化以其海納百川之勢,不斷影響著少數民族的文化。學術界對中國音樂的研究也更多的是從漢族音樂的角度進行的。譬如中國音樂史、中國樂理、中國傳統音樂等教材的編寫、課程的教學更多的都側重于漢族音樂知識、理論的梳理總結。雖有各少數民族音樂志的編撰、整理工作,但并沒有有效地納入學校的課程設置中,這也不能不說是音樂文化多元傳承中的缺失。
云南由于處于祖國的邊陲地帶,經濟相對落后,且又以少數民族文化多元并存,無疑會受到漢族文化影響。這又是云南在實施母語音樂教育時所面臨的困難。
無論困難再大,從文化價值相對論的角度來說,各種文化都有其自身的價值,正是這些不同的傳統文化才使得我們的生活變得豐富多彩,而不是現代文化使然。因此,我們更應該珍惜這些萌發自不同傳統而又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
三、 云南實施母語音樂教育的理論對策
1、 以各地州音樂文化特色為背景、地州師范院校為依托,構建本民族音樂學科理論
云南母語音樂教育的實施之所以困難重重,其最根本的原因還在于這種多樣化的音樂文化形態缺乏強有力的自身闡釋能力,在當今的主流音樂教育環境下顯得難以梳理歸納,進而在其自然傳承難以有效進行的當今社會中,學校的傳承也顯得羸弱無力。
要解決此一問題,地、州師范院校音樂系科就要通力合作,充分發揮其學術高地的作用。云南共有8個地級市和8個自治州,各地市州基本都設有師范學院或師專學校,這些院校的音樂系科作為“工作母機”正可以充分依托自身區位、文化優勢,立足本土,充分調動一切可茲利用的資源(如與文化館等研究單位、本地知名藝人加強溝通,剛剛頒布的第二批非物質文化傳承人名錄中,就有文山銅鼓舞傳承人陸孝宗、黃正武的名單),深入研究本鄉本土的音樂文化資源,從一種音樂理論的研究逐步過渡到一種音樂學科理論的構建,進而反過來指導音樂理論的再研究,以形成一種良性的互動循環機制,從而為母語音樂教育的實施奠定自身堅實的基礎。
2、 從文化價值相對論的角度重新審視中西音樂文化之價值,打開西方音樂中心論的殖民枷鎖
美國民族音樂學家內特爾在1992年的國際音樂教育學會的大會發言中提出“將音樂作為文化來傳授”的觀點(管建華:《音樂民族學與世界音樂的教學中國音樂》(增刊續集),1995. 4.);20世紀70年代,德國音樂教育對音樂的理解也開始由“音樂藝術作品”轉向“文化中的音樂”(金經言:《德國音樂教育中的若干新動向》,《中國音樂》,1996第2期);澳大利亞音樂學家彼得·鄧巴·霍爾認為音樂是“文化的一種產品……不同類型的音樂,屬于、代表、事實上解說著不同的文化與亞文化群體”(桂勤編:《關于音樂教育中多元文化主義的界定》,《中國音樂》(增刊續集),1995. p67)。上述這些對音樂本體的界定反映出了一些相同的學術人文思想——音樂是一種文化,對音樂的理解必須放到具體的“情境”(Context)之中方能得出準確的闡釋。因而,文化沒有高低貴賤之分,“過去被認為是圭臬的東西其實也是人為構造出來的,過去可以不加思考不用證明的公理,現在如果自上而下地強加在豐富多樣的地方性現實之上,就難免有虛妄的嫌疑了”。(葉舒憲:《誰破譯了達芬奇密碼?》,《讀書》,2005年第1期)
從文化價值相對論的角度出發就有了多元文化并存的需求。在2004年南京師范大學召開的世界多元文化音樂教育大會上,與會專家發出了關于各級教育部門進行多元文化音樂教育的倡議書,從學科和學術方面來講世界多元文化音樂教育是音樂教育學科的轉向,是學術視野轉向全球視野的反映。有助于打破西方音樂一元中心論的影響,使我國的音樂教育真正的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管建華:《世界多元文化音樂教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陜西師大出版社,2006年12月)
云南的音樂教育應該趁此東風,迎頭趕上,以開闊的胸襟,理解、容納多元的音樂文化,以此打破西方音樂中心論的后殖民影響。
3、 正確處理少數民族母語音樂教育與漢族傳統音樂教育的關系
我國自古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大家庭,也正是各民族相互團結、求同存異才使這個大家庭綻放出五彩繽紛的花朵。從某種意義上講,經濟一體化給我們帶來的恰恰是單一的生活方式和審關疲勞,正是不同的各民族藝術物象才使得我們生活的土地變得豐富多彩,而決不是現代文化使然。因此,在當今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之下這種文化個性差異的維系就顯得尤為重要。
因此,正確處理好漢族音樂文化與云南少數民族音樂文化之間的關系,是云南母語音樂教育必須面對的另一問題。它不僅僅是一些形式上亦或課程內容上多少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云南母語音樂教育的有效實施對本民族精神生活的維系、社會和諧的構建以及文化生態的平衡都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作者單位:湘潭大學)
責任編輯: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