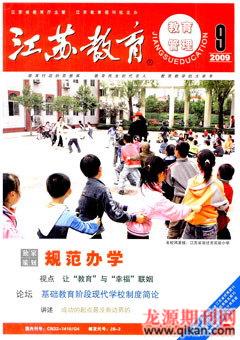課程改革進程中的建構主義思想辨正
建構主義思想自上個世紀90年代被引入中國之后,就一直在褒與貶的夾縫中艱難地生存著。特別是,當新課程改革成為建構主義思想的實踐土壤之后,很多直指新課程弊端的批判也順帶成為攻擊建構主義思想的有力辯詞。一些學者甚至指出。建構主義是一種否認客觀世界、否認人類知識的“反科學”、“反知識”思潮,是一種不可知論、唯我論或獨斷論,它對教育實踐界正產生著很多的危害,對此應當加以正視。但另一方面,諸如情境學習、認知拋錨式教學、認知彈性學習、分布式學習等國際上前沿且被實踐證明為有效的學習與教學模型,卻都將建構主義作為其后臺的支撐性理論,共享著有關建構主義的很多思想與假設。我們甚至可以看到,西方學術界自上個世紀末所發起的學習理念之革命,無一不在鞏固、加深與完善建構主義作為一種哲學思想的合理性與沖擊力,無一不在教育理論與實踐的深處尋覓建構主義思想的真正的生命張力。因此。國際上越來越多的學者都開始認識到,“不是建構主義本身是一種錯誤的認識論,而是我們在言說、在實踐建構主義思想時走了樣”,那么,辨明建構主義的思想實質、建立對建構主義的理性自覺、克服對建構主義的諸多誤讀,即是處于當前課改大潮中的人們急需補上的重要一課。
一、建構主義并非一種否認客觀世界存在的學說
幾天前,一位臺灣的課程學者楊教授來南京大學給教育系的師生做報告。從其報告的內容看(關于臺灣課程改革的興衰成敗),他對建構主義很明顯地持一種不贊同立場。在報告的一開始,他向聽眾拋出了如下一個問題以引出其對建構主義的認識,“站在你們面前的楊教授真的存在嗎?”顯然,他的意思是說,建構主義強調任何事物都是被建構出來的,包括現在正在演講的“楊教授”。現場觀眾的一片笑聲似乎表達了對楊教授幽默且看似深刻的見地的贊同。其實,如果大家都冷靜地思考一下,按照這一邏輯,世界上就沒有什么事物是客觀地存在的了,任何呈現在大家面前的事物(高山、大樓、河流等)都是人們主觀建構的一種意念,或者說,都是每個人頭腦中的一種現實幻象。很明顯,楊教授是想把“現實世界都非真實存在的”這一荒謬的認識安在建構主義的頭上。
其實,楊教授的觀點代表了很多反建構主義者的共同立場。但他們都犯了一個無限泛化建構主義觀點的根本性錯誤。對此,建構主義思想的重要奠基者馮·格拉塞斯菲爾德就曾反復申明:“經常有人指責我是在否認真實。這種看法是對建構主義的根本誤解,……,否認真實的存在是愚蠢的,這將導致唯我論,而唯我論是不可接受的”。實質上,建構主義并沒有否認真實世界的存在,而只是強調對這樣的“真實”,我們沒有一種對其加以認識的適當方式。也恰如馮·格拉塞斯菲爾德所進一步指明的,“我們能定義‘存在的意義,但是只有在我們的經驗世界的領域中,而不是在本體論意義上。當‘存在一詞運用在獨立于我們經驗的世界(即一個本體論的世界)時,它也就失去了自己的意義,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意義”。所以,建構主義思想始終不會在本體論的范圍中打轉,也不會陷入統治西方思想界近兩千年的“思維與存在何謂第一性”的本體論謎團中并使自身走向迷失,它關注的是人們對客觀實在的“認識”以及這種“認識”的限度與可能。
由此我們更可清晰地看到,科學知識是人類群體對外部客觀世界的一種“認識”,這種認識即是一種“建構”。建構的認識在一定的時空范圍中是穩定的、不變的,但在更長的時空界域中卻可能是需要修正、完善與變化的,這體現了科學知識的累積與發展的特性。由此可見,科學并非否認客觀世界的存在,而只是否認科學知識作為絕對鏡像式的存在,并主張,作為一種“人類認識”的科學知識,是在人類群體的經驗范圍中的一種“建構”,是主體世界與客觀本體世界的一種聯系,它發生在這種彼此聯系、相互交織的中途,這與建構主義的思想具有本質上的一致性!甚至可以說,上述的思想正反映出,建構主義對人類認識世界的方式做出了較為深入、準確的刻畫與敘述。由此可得到一個頗具辨證意味的推斷,即,對建構主義的所謂“反科學”特征的批判,實際上就是一種對科學本身的批判;對建構主義的所謂“反知識”特征的批判,實際上也就是一種對知識本身的批判。說白了,這種批判源自對建構主義思想的誤讀或膚淺的理解。
二、知識的適應性——建構主義思想在教育中的張力
承接上述的論述,一個有趣的問題自然地涌現出來,即,人類所建構的認識是否是任意的、無限制的、隨心所欲的?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作為建構主義思想的重要奠基者,瑞士著名的心理學家皮亞杰一再強調。“認識是一種適應性活動”。這一觀點承接了生物進化論的適應性思想,即是強調,具有適應性的動物有一套處理它們所生存環境中各類困難的行為本領,而人類的知識作為一種概念和行動綱要,本質上就是動物行為本領中的一個組成部分。由此可知,人類的認識(或知識)不是漫無目的、隨心所欲式的建構,而是在一定的經驗背景中、在認識者所賴以生存的事物與關系的網絡中產生的,或者簡而言之,在一種情境脈絡中所產生的,是主體在適應外部世界對人類的要求的過程中所自然涌現的。
根據知識或認識的適應性觀點,傳統認識論中的真理概念、傳統教育學中的“正確或錯誤”的概念,就要被一種新的觀念——“生存力”所取代。這一觀念仍然取自生物學領域,即,在生物學家看來,只要活的有機體能設法在環境中生存,它便具有生存力。由此,建構主義者認為,如果概念、模式、理論等能證明它們對于自身被創造出來的情境脈絡是適宜的,那么它們也具有生存力。“生存力”與真理完全不同,它與目標、意圖形成的情境脈絡相關聯,它在適應這種境脈的特殊性中產生,甚至可以說,它是個體生命適應力的一種真實表達。
知識的適應性以及隨之產生的“生存力”觀念,對于教育思想的轉變產生了極大的挑戰和沖擊。在孩童身上經常出現的所謂“錯誤概念”,在成人、科學家、專家等的眼中的確是錯誤的,但從每個個體的孩童角度來看,這些錯誤概念在其經驗世界中是有效的、是相融的,或者說,在孩童的相關情境脈絡中是具有“生存力”的。這些對孩童而言是合理的觀念,如果得不到教師或成人的悉心關注與耐心引導,則這種所謂“錯誤的”、但卻是“合理的”觀念,將可能長時間地這樣“錯誤”下去、“合理”下去。因此,馮·格拉塞斯菲爾德建議,“教師必須要關心學生頭腦中發生的事情,要傾聽學生,解釋學生所做的,并試圖建立起學生概念結構的‘模型。當然這是一項容易出錯的工程。但若不這樣做,任何旨在改變學生概念結構的努力都只不過是一種偶然事件,或許還會失敗”。
三、我們可以言說一種所謂的“建構式教學”嗎
臺灣學術界曾把2001年開始的臺灣新課程改革中的核心理念標榜為“建構式教學”,并將其內涵幾乎等同于作為一種教學方式的“發現式教學”。臺灣學者后來在
總結新課程改革失敗的經驗時,大都認為,建構式教學、進而所謂的建構主義是導致這輪課改失敗的罪魁禍首。實質上,臺灣學術界在課程改革的起點上就犯下了一個不可饒恕的錯誤,即,完全窄化了建構主義的思想內涵,剝離了建構主義所真正具有的哲學上的思想張力。
如上文所述,建構主義思想給教育帶來的,不僅僅是所謂教學方式上的轉變,而更是一種對學習者、對學習、對教育等認識方式上的根本性變革。傳統意義上的二元對立的教育思維方式,已經被一種更加連續的、更加關注學習者經驗的、更加富有人本意境的全新思想框架所替代。建構主義更加強調的是教育者看待教育的深層認識論的轉變,而不僅僅是所謂的外顯教學方式的彼此替代。更具體地,建構主義更強調的是個體內在的認識發生機制,而教學方式則關注外部的行為表現及其具體呈現。打一個有趣的比方。就吃飯來說,是自己動手吃,還是靠別人喂,就好比是發現學習還是接受學習,這里只存在著學習與教學方式上的不同罷了。但吃下去的飯,是否能靠自己去消化,消化得怎樣,這就進入到了“建構”的范疇中了。建構的好壞。取決于這個有機體對外部環境的適應性如何,取決于這個有機體自身的經驗的質量高低與類型差異。所以說,早在上個世紀60年代,著名心理學家奧蘇伯爾就曾用有意義學習與機械學習、發現學習與接受學習這兩個維度來描述人類學習的具體類型。很顯然,建構主義所強調的學習對應的應當是有意義學習,它主張這樣的學習必定是主體在自身經驗基礎上的主動積極地建構。而如果按照臺灣學者的看法,將建構主義安置在發現學習的范圍內。則顯然犯了歸類上的低級錯誤。發現與接受,都只表明了教學方式上的差異,而不涉及學習者個體的內在經驗上的任何變化。而奧蘇伯爾早已十分明確地闡釋道,發現學習有可能是機械的,如果這樣的學習脫離了學習者的內在經驗;接受學習也可能是有意義的,如果這樣的學習與學習者的內在經驗產生著實質性的、非人為性的關聯。
在今天的國內外教育實踐現場,大量標榜“建構式教學”的言與行普遍地存在,這其實反映了人們對建構主義所具有的思想張力仍缺乏清晰的、深刻的認識。當建構主義真正走入了一個教育者心中的時候,當建構主義真正成為一個教育者秉持的信條時,他已經不會過多地糾纏在所謂外部的、表面的教學形式是否更具“發現性”上了,他必定會更加關注學習者的內在經驗結構,更加關注學習者頭腦中正在發生著什么,并將這種深入的、細致的思考作為其設計教學的重要起點。教學的藝術性、教學的魅力,恰恰體現在教師對學習者個體經驗的釋讀上,體現在不同的教師所采取的各不相同的教學方式與手段上(無論是發現還是接受),體現在不同的教學方式背后所具有的“推動學習者經驗的發展”這一共同目標上。馮·格拉塞斯菲爾德曾說過一句頗具意味的話,筆者愿將這句話作為本文的結束語,即,“真正的教育者一定是一名建構主義者,無論其是否認識到建構主義這一標簽,他對學生經驗的關注已經在其內心深處深刻地烙上了建構主義的真實印記。”
參考文獻
[1][2][4][6]萊斯利·P·斯特弗,杰里·蓋爾主編,教育中的建構主義[M],高文等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3—20
[3]呂林海,走出建構主義思想之惑——從兩個方面正確把握建構主義理論及其教育意蘊[J]電化教育研究,2007(11)
[5]鄭太年,學習:為人的發展[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