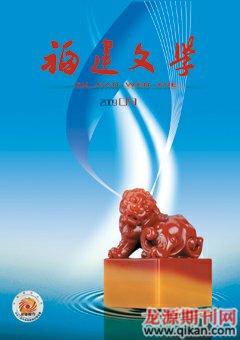鳥獸散
薛 榮
這個故事跟三個人有關。也可能和三十個人,或者是三百個人有關系。但人多了事情就說不清楚了,我只能區分一下親疏遠近,說它和三個人有關系。我這樣說并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為在這一年里,除了故事里的我之外,另外兩個男人都和我有過肉體關系。
老林是我丈夫,我們之間有那種關系是難免的。有時候在公司里,有時在賓館,但在家的次數少而又少。他不喜歡在家里的大床上做那事。他沒說環境不行,也不講自己厭了。他會有分寸地表達他不想那事,他累了,他需要休息。還輪不到他動嘴皮子,他朦朧的眼神和修長的手指都很好使。我當然是個明白人。他累了我比他累上幾倍,小孩子從寄宿學校回來,作業要看,換洗的衣服得準備,廚房里的鍋碗瓢盆等著收拾,這兒弄弄那兒搞搞之后,誰還有心思去伺候已打起呼嚕來了的丈夫呢?常常是,他的呼嚕聲像根橡皮筋不痛不癢地彈到我的額頭上,腳還沒移到床邊,我早以為自個兒也睡著了。
這會兒我也快睡著了。一代國學大師沈夢龍的故居后院,你說有多靜就有多靜。院子里月季盛開,芭蕉一半翠綠一半枯黃,看上去都像是半透明的,幾株臘梅的香氣已隱隱地傳了開來,提醒你時不時地要抽一抽鼻子,從冷空氣中撈取點心曠神怡的感受。我抽鼻子的聲音肯定會引起老林的不快。他以為我要哭什么的,這在他是無法承受的。只因為我好多年沒當著他的面哭過了,如果今天放開聲音這么一哭一嚎,事情可真就搞大了。
“你傷心什么呀?”他把架著的二郎腿放下來,身體也在椅子里坐了坐直。我睨了他一眼,打探他的心思。西下的陽光在他的眼鏡片上形成的反光模糊了我的視覺。“我知道你心情不好,哼,我怎么會不知道呢——可是你想想,”他穿了登山靴的雙腳在方磚地上跺了跺,“我把兩件事情放在一起做,也是為你好,讓你少傷心一次你總不會不明白吧。”我回頭朝門窗敞開著的室內看了看,也是方磚鋪就的地皮上撒滿了白花花的打印紙,幾臺電腦集中堆放在一個桌子上,顯示器驚險地壘成個品字形,邊上圍著一圈椅子,唯有角落里的那張辦公桌還保持著原樣,桌面上辦公用品擺放整齊,似乎主人剛才還在,現在只不過是去上個廁所罷了。
我長長地吁了口悶氣。這在老林看來可不算是對他剛才那一番話的反應。“你在聽嗎?”他問我,同時把屁股底下的椅子朝我這邊拉近了一些。我垂下眼皮躲避他的目光。那肯定是一種不懷好意又滿懷得意的目光。哪個女人受得了這個。我聞到了他嘴里的煙味,像張面膜一般地敷到我的臉上。“你想說什么你就說唄。”我回了他一句話,感覺上把他推遠一點。他嘿嘿地奸笑了幾聲,有種討好的意味。他掏出一支香煙,在右手的指甲蓋上篤了篤。“前夫畢竟是前夫,待我好一點么?”他更進一步地向我示意,這可是他的拿手好戲。過去做廣告公司,錢來錢去的,還是很傷腦筋的,現在暫時出現了空檔,他的腦袋瓜子正沒處使勁呢。接下來他會不斷地用話來刺探我,撩拔我,暗損我,否則他這一張嘴就算浪費了。其實這時我應該有些個短信的,可是手機像是沒電了一樣毫無動靜。我就開口了。我說怎么待你好,我這些年待你不好嗎?你去叫人評評看,論論看,我是怎樣一個人,你是怎樣一個人,沒有我你有今天嗎?什么叫同甘共苦?什么叫白手起家?老林你也算受過高等教育,你是真不明白還是假不明白?你……說到這兒我卡殼了。我這那是在說話,是在打沖鋒槍了,一梭子又一梭子的,說的太多等于什么也沒說。
從他的表情來看,我是等于什么也沒說。在光線的作用下,老林的臉一半陰一半陽的。他做愛時臉部表情怎么樣的,我一點兒也想不起來了。這就是所謂的前夫吧。我給自己點了支煙,又沖他揚了揚打火機,他沒接我這個茬。他仿佛沒見過我抽煙似地瞪大眼看著我,一個勁地把我往壞女人那個方向看。
煙霧追隨著臘梅花的暗香在屋檐下飄散開去。
“婚是你提出來離的,公司是我提議散的,你拿房子和兒子,我開走車子,你看這有多好,多平衡,多……”他晃了晃手里的香煙,可想不出最后一個多是什么多,“待我好一點嘛。”他站起身來,在院子里的月季花壇前走了幾步。然后立定了低頭盯著我看。我后悔沒戴個帽子什么的。這個色鬼肯定在看著我梳理整齊的發縫進而聯想到我下面去了。過去他說過這個事。他承認就是因為看多了公司里搞設計的小金的發縫而把她下面的那條縫搞開了的。
心頭火竄上了我的嗓子眼。
“待你好?做夢吧你,你是不是想要我上樓去你的辦公沙發上和你做一把,想的倒美,你死了這條心吧你。”我扔了手里的煙,抓起包要走,他倒是急了,上前攔住了我的去路。我瞪眼說你干么?他的手一攤,說我能干么呢,我老林這輩子還沒強奸過女人,我總不會強奸前妻吧?你聽聽,你聽聽,什么德性。他就是靠著這一張臭嘴和我的幫襯才開起廣告公司來的。
這個下午漫長得像韓劇,看來我只能坐在這張椅子上和他耗下去了。我已經看出來他的興致很高,就關照自己盡量少吭聲,說話能簡短就簡短,看誰能耗得過誰。我的策略立竿見影,很長一段時間,院子里除了麻雀的叫聲,就再也沒有另外的聲音。
我只顧自己想心事,老林比我難受多了。接了個電話,是約他晚上吃飯的,他沒應承下來。過一會兒,屋子里那還算整齊的桌子上的電話響了,響了很長時間,把我和老林的注意力都吸引過去了。可我們兩個誰也沒走過去接。什么業務不業務的,今天我和他一起來這兒,是要給幾個部門經理的拖欠工資發了。我們這個所謂的廣告公司名頭很大,其實業務非常單一,就是給房產商做樓盤推薦的,老林把房產商給的廣告費全部去買了房產,又拿到市場上去炒,炒到現在他自己都要去和別人合股開發樓盤,那還瞧得上家里的舊房子和舊妻子。我一個單身棄婦,接下來做什么?想到這個問題我頭就大了。我才四十歲,不老也不年輕的當口。本來我是應該說說我的長相的,發型啊,體型啊什么的,可這時老林夸起了我們租的這房子。“你看看、你看看。”老林指點著院子,有些花木熟視無睹了那么些日子,到如今他仍連名字都叫不出,可這根本不影響他的情緒和狀態。他要我看我就隨著他的指點東張西望。“多好的地方,在市中心哪兒還有這么好的古宅,托沈老先生的福才讓我們有了一個發財的地盤。嘿嘿……”老林肯定是想到當初怎么跟文物局的頭兒打關系才把這故居最后一進院子搞定的,興奮的樣子一如當初。
“租期還有大半年呢,放棄了真是可惜。”老林繞到我的背后,手放到我的肩上左右摩挲,被我甩開了。我喝斥他離我遠點他就憤憤不平地回到剛才坐的椅子上去,嘴唇抿成一線,下巴上下晃動著,一副很受啟發的沖動樣子。我等著。搞過廣告策劃的人都這樣兒,他心中有創意了你不讓他說出來真比一刀一刀剮了他還難受。“你想過沒有,”我沒反應,我才不上他的當呢,“你肯定沒想過。這些天你就知道想我的狼心狗肺,而忘了正事。”他把手里捏了好長一會的煙叼到嘴角上,示意我給他點上,我沒理他。“怎么說吧,我是不搞廣告這玩意了,這東西來錢太慢,可你可以搞啊。地方是現成的,這些辦公家具處理起來沒幾個錢可留著用還是可以用用的,還有人,我知道你恨死了設計部的那幾個小丫頭,可人家是學藝術的,人家性觀念開放你有什么辦法,你是老板了你可以不用她們,現在招幾個人還不容易,再說了有些個員工還指望著你呢。”他又架起了二郎腿,腳尖無節奏地亂抖。
“他可是巴不得有機會跟著你繼續干呢?”什么樣的好話壞話從下流的嘴里出來一律變成了下流話。我覺察到了老林是有所指的。有點緊張。
“……繼續干繼續干,你、我,誰也不會閑著的。”老林感慨地捋了捋早已謝頂了的頭發,嘖吧著嘴,像是在品味什么。“我知道我這個婚為啥離得這么順當,我知道,我打心底里謝謝他。”老林的目光如蟲子般在我臉頰上爬,我面不改色。如今婚都離了我還怕他什么呢。我清清了嗓子,說老林你要說什么就直言吧,不用這樣旁敲側擊的,浪費你的口舌。“那可不行,那不行的,我老林不是這樣的人,過去都是你說我罵我,弄得我沒法做人,我才不會像你這樣呢。”他達到了他的預期目的,這是他這個下午非要跟我在這人去樓空的地方好好聊聊的原因了。不過,照他的個性他是不會到此為止的。他還有更高的境界要上去呢?果然他接著關照我人不可貌相,知人知面難知心啊。這種話別人說說也就說說罷了,聽他這么一講我就覺得荒唐了。
可我還是泥菩薩似地坐著不開口。
因為我是在想小徐。小徐是跟我這個故事有關的第三個人。一個中文系畢業的二十四歲的小男人。他一個小時前還在這兒,站在那張收拾整齊的桌子邊上叫過我一聲俞姐。公司里另外的人也叫我俞姐,除了老林。老林叫我敏敏。那是我在家里的稱呼,老林把它叫到公司里來了。小徐一來公司就跟我走得近,俞姐俞姐地叫個不停,好在他業務上還行,很快地老林讓他當了部經理也沒人說什么閑話。很快地老林就老讓他出差,有時還叫我一起去,現在看來老林是有意設了個圈套,因為從今天他的言談中我才發覺,他對我和小徐的關系了如指掌。他一直在看好戲哪。房價在發飚,他老林也在發飚。他根本不再乎,他咽得下這口氣,并且越發覺得自個兒自由得不行,包括像離婚這樣的事也是自己想離就離。離了也就離,他還站在一個比你更高的境界上俯下身對你表示關心。
“……雖說我是得謝謝他,可你聽我一句話,他這樣的人是靠不牢的。”老林陰沉著臉,裝出心事重重的樣子。我才不會被他的假象迷惑呢。我的心順著自己的思路走。前些天公司吃散伙飯,本來這也正常,可老林非要每個員工帶上老婆或者是女朋友,沒有的還要求去借一個或租一個,搞得本來是開三桌的酒席變成了六桌。我就是在酒席上第一次看見小徐在電視臺做視頻技術的女朋友的。那天我喝醉了可就是吐不出來,今天我倒真想吐了。
心里頭惡心,我開了口。我說我、我想吐……老林急得直擺手,說:“千萬、千萬別吐露真相。給我個面子。我沒要求你什么,我沒那個意思。我是說……”他看見我皺緊眉頭,一愣,突然躥到我跟前,抓起我的手,問我是不是懷孕了?我用抓在手里的包打了他幾下,把他趕回到椅子里。老林心驚肉跳了好一會兒,才明白自己的懷孕恐懼癥又犯了。他有點不好意思,我也松了一口氣。
一架正在航拍的直升飛機,掠過沈夢龍故居的上空,不知朝哪兒飛去。沉默了一會。他在沉默中動鬼心思,我在沉默中等著。兩個人在一起長久的不說話肯定是不行的,再說了他還沒完呢?他才關心你一半他不會撒手不管的。我掏出一塊鏡子整了整臉上的妝。一個女人當著一個男人的面化妝打扮總是能緩解氣氛的。老林終于點上了那支一會在手里一會夾到嘴皮子上的香煙,深深地吸了一口,繼續清空積壓到他喉嚨口的臨別贈言。“這小子一進公司我就覺得不是等閑之輩,精明著呢。如果不是有那個事我還真有點想帶他進新公司,給他個銷售經理干干;他一開始就瞄上你了可不敢過分,等到得知這公司快要散了他才下的手,當然我也是給你們創造了機會的,這個你不要不承認,你會說我是個陰謀家,隨你怎么說吧,公司開到最后也亂了,有的貪污,有的在外邊接活單干,他倒好,沖老板娘下了手,狠狠地撈了一把,嘿嘿,佩服佩服。”老林這么說著,就像是在看自己導演的一出好戲,克制不住的得意。我還能說什么呢,早知道他站在一邊看好戲,憋死我也不會去做那樣的事情。我恨不得抽自己耳光,揪自個兒的頭發,我想我怎么這樣傻呢,當初自以為神不知鬼不覺的,暗地里又是羞又是怕,心里美滋滋的也不敢表露到臉上。我怎么沒想到他可是老手而我是個新手,他有的是經驗和手段,而我有什么,傻B一個。
剛才還在心底里蕩漾著的一些美好感覺像潮水一般地退去了。我甚至懷疑小徐是不是受老林的指使才來勾引我的。這樣的念頭一動,我的心就掉進了冰窟隆。我把發燙的臉頰埋進自已的手心里,只求天快點暗下去,老林被別人叫到酒桌上去。可他還沒完呢,他還要關心我呢?“我說這個人靠不住還是有理由的,我試驗過他,我是個騙子,他也沒啥誠信,真的,你不要不相信,我這是為你好。”你說說看他這樣講我怎么去反駁。甚至他的話進一步印證了我的猜想,小徐是受老林指使的,這小伙子只不過是老林手里的一個離婚工具罷了。我覺得今兒個公司完了,家也完了,我自個兒也快要完了。崩潰了。我想自己還是哭吧,大哭一場可能心里會好受一些。我的肩膀一開始抽動,老林卻過來搖著我的身體問我怎么了?我沒有力氣驅趕他,只是抬起頭,壓抑在胸的哭聲從嘴里出來卻是一連串咯咯咯的傻笑。
院子旁邊的木門吱呀一聲推開了。
是小徐的腳步聲。我不用抬頭也知道他站在那兒,眼神愣愣地朝我們兩個看著。我的小腿顫抖。離我不遠的榆樹下有一口枯井,史書記載沈夢龍的一個小老婆就是跳這口井死的。
“林總。”小徐叫了一聲老林才啟動腳步到我近旁,又用更低的聲音叫了聲俞姐。“我不知道你們在吵架,我……”小徐解釋道。他那略顯稚嫩的嗓音讓我鎮定了下來。我抬起頭,理了理罩住半邊臉的垂發,面無表情地瞧著這個突然出現的年輕人。我在這個故事里沒有介紹自個兒的長相,但小徐的樣子我還是要說一說的。他長了張窄臉,鼻梁又長又挺,下巴尖尖的;他穿了件愛思波雷特的短風衣,里邊灰色球衫的風帽翻在外邊,下身是一條滿是破洞的牛仔褲,腳上也是一雙登山靴,只不過老林的登山靴是進口的、高幫的,而他的是國產的低幫鞋。
我的眼光停留在這雙臟兮兮的低幫鞋上,不敢看其他。
“噢——小徐你來干什么?”老林聲音發顫,有點慌亂。“我不知道你們……”小徐又要重復剛說過的話,被老林打斷了。“你不知道的事情多了,你快說你過來到底干什么?”老林記起了他可是做過這小子老板的,一下子恢復了狀態。“俞姐。”小徐又叫了我一聲,似乎在開口說事前征求我的意見。我的心里亂極了,沒反應。“俞姐她身體不舒服。”老林很受不了小徐跟我的接近,一下子提高了嗓音。“說吧,什么事?”老林催促道。小徐的腳原地動了動。他說也沒什么大事。他的身體站得筆直,語氣也是一副不亢不卑的腔調了。
“今天發工資,我那工資條上是四千二,可信封里的錢回去一數多出了五百塊。我想是會計搞錯了吧。”一聽是這個事,我抬起頭來,小徐大大方方地沖我笑了笑。“是嗎?”一聽老林這聲氣我就知道他在裝了,“怎么會呢?”小徐偏過頭去朝屋子里望了望,沒看見會計的影子。“我知道照規距,會計弄錯了是要自己賠錢進去的,所以我來還了。”說著話小徐把裝了五百塊錢的信封交到了老林手里。老林捏了捏信封,朝我看看,突然明白他的西洋景在我面前穿梆了。“老林你瞪我干么,你看看小徐,小徐真是好樣兒的,公司都散了也不貪圖這不屬于自己的錢。”這樣夸小徐等于是在夸我自己,我一下子渾身通透,舒服的感覺抵達每個毛孔。
“你——”老林明白我的態度,急了,我不管他,拿眼睛和小徐作情感交流,而這小伙子居然不好意思地躲閃著回避。我掏出香煙來問小徐抽煙嗎,小徐搖了搖頭。“林總你給會計說一聲,你忙吧,我要走了。”小徐依舊躲閃著我的目光轉身朝門口走去,順手捋了把冬青樹葉揉捏在自個兒的手里。
“你給我回來!”
突然之間老林震怒了,那張漲紅的臉從我眼前一晃而過。
“你他媽的裝君子,那我就是小人啦——你給我站住!”小徐回轉身站在院子中央,一臉的疑惑。“你他媽的在我面前裝誠信,你裝個屁!”謝天謝地,老林沒有沖過去扭打小徐。老林在那株臘梅樹下止住了腳步。我緊跟在他的身后被他發覺了。“你想干么?這是我們兩個男人的事情,你滾一邊去。”他明白如果他和小徐打起來的話我肯定會幫小徐的,他哪受得了這個。我退到了屋檐下,叫小徐快走,小徐眨巴著大眼睛,沒聽我的。
“你他媽的小小年紀在我面前裝什么人樣,老子走過的橋比你走過的路還多,跟我玩——哼,你還吃十年飯吧!”老林氣得脖子都紅了,手指哆嗦,“你玩誠信是嗎?好啊,那我問你,你跟敏敏的事情你敢不敢跟你女朋友說?”老林的手指快點到了小徐的鼻梁骨上了。
小徐瞇細了眼睛,不回答。
“你回答我,有沒有說?”老林的唾沫星子噴到了小徐臉上。“那、那是兩回事……”小徐囁嚅著回答。老林狠狠地把信封摔到小徐的腳跟前,說:“一回事二回事都是事,都是你干的事!你給我少來這一套。”
“老林你太過分了!”
我在一邊尖叫,老林就當沒聽見,睬也不睬我。
“林總,我……”小徐想解釋,只因我在邊上,有些話實在說不出口。他別著腦袋不敢看我。
我的淚流出了眼眶。
“你不說那我說,我認得你女朋友,我去電視臺跟她說。”老林的雙手抱在胸前,腆著個啤酒肚,開始顯示威風,“再說了,你那女朋友也不是什么好貨,老子拍十萬塊錢在她面前,我就不信她不肯叉開大腿讓我狂操一通!”
“老板,我、我……”小徐結結巴巴的聲音里帶著點哭腔,我的心像是快要撕裂了一般的難受。
“哼,我再告訴你,整個下海市做廣告或不做廣告的都是我哥們,你還想在這兒混可沒那么容易,我一個電話就把你的新飯碗砸了你信不信。”
小徐低下了頭,不吭聲了。
“你揀起來——”
“你揀起這五百塊錢給我滾蛋!”老林跺著腳喊叫,小徐的手一松,那些個揉碎了的冬青樹葉灑落到他的腳邊。
“你他媽的快給我揀起來!”老林的聲音尖利的像塊玻璃,捅得我的耳朵都要流血了。他沒發覺我從他的身后走到了枯井邊上,朝井里看了看。這時小徐彎下腰去,他球衫的風帽罩到了他的頭上,遮住了他的臉頰。
我喊了聲小徐。他一聽到我的叫聲,快要碰到地上的信封的手指猛地縮了回來。他重新面對著老林站著,眼睛卻第一次直直地望著我。他濕潤的眼睛紅了。
“你要是揀起這信封我就從這兒跳下去。”
我的鞋尖踢了踢滿是青苔的石井圈。
“敏敏——”老林一聽這話就急了。他想跑過來,可我的一只腳一擱到石井圈上他就不敢動了。“敏敏你別這樣——”老林急的雙手亂擺。我說這是我和小徐的事,與你無關。
“小徐,你走吧。”小伙子還在遲疑著,可我堅決的眼神震住了他。他揚手指著老林罵了句我操你媽,然后撥腳就跑出門去。
“你走吧,我們再也不要有什么聯系……”我沖著小徐的背影喊出的那句話不知他有沒有聽清,但老林可是聽得明明白白的。他像看一個陌生人似的呆呆地看了我一會,自己過去揀起了那個信封,放在手里掂了掂,嘀咕了一句那可是下崗工人一個月的生活費啊,給你都不要,那我自己花唄。
“……你不要別人可要的,我現在就找小姐去。”他自言自語地收拾起自己的皮包和汽車鑰匙,也走了。
我一個人在沈夢龍先生故居后院的石井圈上坐到了天黑,腿軟得像棉花。小徐發短信過來,說他和他女朋友在一起,他們要晚上請我吃火鍋,我沒回。說好了是三個人的故事的,再把小徐女朋友牽扯進來的話,那就得另講一個故事了,不過那很可能仍是三個人的,而我對三個人的故事實在是有點厭了。
責任編輯 石華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