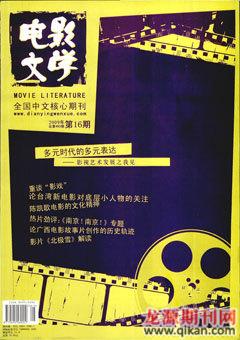評《我的團長我的團》的插曲
肖 珣
[摘要] 影視藝術從誕生之日起就是一門視聽藝術,音樂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構成元素。現代影視音樂是體現影視作品理念的一個重要手段,也是導演創造個人藝術風格的重要元素。影視插曲也具有表現歡快和悲傷情緒等一般音樂的共性特點,同樣也可表現不同地域、民族、時代等特征。本文主要圍繞《我的團長我的團》中的一些插曲運用形式進行品析。
[關鍵詞] 影視音樂;影視劇;插曲
影視音樂主要由片頭片尾音樂、主題曲、插曲、場景音樂等幾部分構成,每一部分都各自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其表現手法和形式體裁各不相同。影視音樂主要是歌曲和純音樂(無歌詞)兩種表現形式。片頭片尾、主題曲、插曲音樂既可以是歌曲也可以是純音樂。純音樂(無歌詞)部分又可分為主題音樂和場景音樂兩種,既可以是專門創作的,也可以是主題曲或者插曲發展的。但無論是哪部分,影視音樂作為影視綜合藝術的基本要素之一,仍離不開旋律、和聲、節奏和色彩的配合。只是純音樂(無歌詞)表現時在時間上一般是連貫的,而影視音樂由于受到了電影蒙太奇組接的制約,在時間上具有間斷性的特點。影視主題曲通常用以表現影視劇主題、塑造其基本形象或情緒,它的旋律可作為主題音樂加以貫穿和發展,是全劇音樂的核心。主題歌可以重復出現,也可根據劇中內容的需要,在音樂或歌詞上作相應的變化和處理。在創作和表現時,其藝術構思、結構和音樂形象要受影視的藝術總構思、總結構和畫面視覺形象的制約。影視插曲就是穿插在影視、話劇等藝術樣式中的短小樂曲。插曲內容可單獨創作也可引用別的音樂作品,但引用時要尊重版權,即獲得音樂著作權協會或詞曲作者的授權。影視插曲的作用也不僅僅是影視畫面的簡單陪襯,而是與情節和畫面搭配,融為一體。在欣賞影視劇時,觀眾是通過視覺感受而對影視中表達的世界進行審美思考,從而徹底融入影視世界中。
3月5日,《我的團長我的團》由江蘇、上海(東方)、北京、云南四家衛視同時播映,還曾引發一場搶播的惡性競爭。本劇由康洪雷導演,根據編劇蘭曉龍的同名小說拍攝而成,是繼去年熱播的《士兵突擊》之后,康洪雷采用《士兵突擊》(王寶強除外)的原班人馬,又推出的一部43集的影視力作,該劇歷時172天,耗資4千多萬元人民幣。取材于1942年到1945年抗戰期間極為悲壯的一段真實歷史。為支援英軍在緬甸(時為英屬地)抗擊日軍侵略,保衛中國西南大后方,中國遠征軍兩度入緬參戰,被視為炮灰團的一群來自五湖四海的潰兵:北平人孟煩了、軍醫郝獸醫、湖南兵鄧寶、東北佬迷龍、河北人豆餅、川兵要麻、上海人林譯、廣東人蛇屁股、康丫、張立憲……他們互相厭憎又相依為命,在團長龍文章的帶領下進行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英勇戰斗。
《我的團長我的團》作曲由獲得17屆法國漢斯國際“最佳作曲獎”的武漢籍作曲家周志勇完成,一頭一尾有曲無歌,其風格和《士兵突擊》一脈相承,簡單而又匠心獨具。片頭沉重哀戚、不失大氣,氣勢恢宏的交響樂隨著油畫般的一幅幅定格畫面緩緩響起,在雄壯聲中含著絲絲悲壯;片尾曲《夜幕》在女聲哀婉的詠嘆聲中,單色人物長卷徐徐移動,畫中人(劇中人)的悲壯、慘烈、痛苦,最終也只不過是畫中的點點墨跡,就像歷史,再波瀾壯闊也只不過是故紙堆中的文字。片中插曲《松花江上》《送別》《野草閑花逢春生》及幾首軍歌的應用更是大大提高了該劇的感染力和表現力,值得細細品評。
一、具有強烈的烘托場景氛圍的插曲
音樂能為影視劇的局部或整體營造一種特定的氣氛基調,從而深化視覺效果,增強畫面的感染力。《團劇》中的插曲,大興“拿來主義”,對場景氛圍具有強烈的烘托作用。在第二集中,禪達的收容所里,一群潰兵、傷兵為證明大家存在這個世界的能力和希望而做“豬肉燉粉條”,在這個因戰事物資極度缺乏,大量潰兵、傷兵、部隊充斥的邊城小鎮,要弄到豬肉燉粉條的所有材料很不容易,為了這頓燉菜,每個人都想盡了一切辦法,懶散、斗狠的東北兵迷龍面對家鄉菜,想到國破家亡,含著熱淚唱著“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礦,還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脫離了我的家鄉,拋棄那無盡的寶藏。流浪,流浪……”悲憤的歌聲令人斷腸、催人淚下。
第七集中,殘兵們從緬甸血戰九死一生,回到怒江西岸待渡時,東岸的中國守軍卻以借口要確定他們的身份而百般刁難,阻止他們過江。于是林譯少校帶領大家唱起了新一軍的軍歌《從軍行》:
君不見,漢終軍,弱冠系虜請長纓;君不見,班定遠,絕域輕騎催戰云!男兒應是重危行,豈讓儒冠誤此生?況乃國危若累卵,羽檄爭馳無少停!棄我昔時筆,著我戰時衿,一呼同志逾十萬,高唱戰歌齊從軍。齊從軍,凈胡塵,誓掃倭奴不顧身!忍情輕斷思家念。慷慨捧出報國心。昂然含笑赴沙場,大旗招展日無光……
騎兵軍歌《旗正飄飄》,也曾被電影《還我河山》用做插曲:
旗正飄飄,馬正蕭蕭,槍在肩刀在腰,熱血熱血似狂潮。
旗正飄飄,馬正蕭蕭,好男兒好男兒好男兒報國在今朝。
快團結莫貽散沙嘲,快團結,快團結,快團結,快團結,
團結,團結奮起,團結。……
這幾段插曲,從歌詞到曲調,不僅僅是中國軍人的身份證明,更仿佛是西岸中國軍人沖天而出的滿腔怒氣,怒氣來自民族的自豪,來自于受人欺凌的悲憤,也是中國軍人胸腔里熱烈跳動的男兒報國心。整首歌慷慨激昂,可謂氣吞山河,使人熱淚盈眶。
二、劇中對人物背景和性格進行刻畫的插曲
插曲結合影視內容和劇情,采用暗喻、渲染式的表現方法,對人物背景和性格進行闡釋和刻畫。“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劇中多次響起的這段旋律是美國作曲家約翰·奧德威的歌曲《夢見家和母親》。現在《夢見家和母親》早就無人提及,而由李叔同作詞的這首《送別》卻深深地感染著中國觀眾的情感,這段插曲第一次響起,是孟煩了和林譯看到一個滿懷夢想的學生背著行李來到這滇邊小城,襯托出孟煩了和林譯也曾經是知識青年,懷著美好的報國之心投筆從戎,而此刻卻因看不到任何希望,變得落魄甚至陰損。當這段插曲不斷響起以后,那信少年中國、信少年的朝氣能夠救中國,曾經懵懂的愛國學生“小書蟲”,已渡過怒江深入敵占區打游擊,而成為一名真正的“赤色分子”。在他犧牲時,又響起悲壯的“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壺濁灑盡余歡,今宵別夢寒”,令人潸然淚下。
劇中最具爭議的插曲是林譯被審時的背景音樂和突擊隊被困樹壘中,林譯顫聲唱著阮玲玉的《野草閑花逢春生》:
蝴蝶兒飛去。心亦不在。凄清長夜誰來,拭淚滿腮。
是貪點依賴,貪一點兒愛。舊緣該了難了,換滿心哀。
怎受得住,這頭猜、那邊怪,人言匯成愁海……
十三集中,一群凄慘壯烈的抗日英雄逃回禪達時,卻以臨陣脫逃罪受審,這段凄婉的插曲,正好配合劇中戲謔的劇情……后面緩緩而起的小提琴演奏的旋律銜接得也很
好,表現了過去大家都瞧不起的阿譯,現在卻升華為一個真實堅定的人,他說出了大家的心里話,而且也是在這個法庭上說得最到位最起作用的一個。在后面四十一集中,炮灰團需要支援時,林譯挺身而上,爆發了人性中的閃光點。他唱著這段凄厲的曲子體現著矛盾和傷心,愛著卻要葬心,其實正好和角色相匹配。阿譯的父親走在大街上被日本兵練槍射死,他因此走上從軍報父仇之路。但是由于他本人內心極其軟弱,拿著槍本來就是一種矛盾,槍和他的內心從來都不和諧。他羨慕成為團長的龍文章這樣的硬漢,這樣可以讓自己的仕途、父仇都能有所交代。這段音樂和這個上海男人一樣體現的是一種矛盾之心。
劇中雖用方言來交代幾位主人翁的籍貫,也用各種地方戲曲來突出人物來自不同地方和不同民族。二十一集中,兩軍對壘,與日軍隔岸斗嘴,為壓住小鬼子的氣焰,湘人不辣(鄧寶)連唱帶跳的湖南花鼓戲《劉海砍樵》。
“胡大姐,呃;我的妻,呵;你把我比做人才難羅嗬嗬;我把你比牛郎不差毫分,那我就比不上羅嗬嗬;劉海哥你是我的夫羅哇,胡大姐你隨著我來走羅嗬嗬;海哥哥你帶路往前行羅……”
一方面表現兩軍陣前自古湘軍多驍勇,另一方面也反應了湖南伢子的活潑、樂觀、可愛,令人忍俊不禁。三十八集決戰前夕,河南豫劇、云南民歌、壯族民歌、彝族歌曲等悉數登場,這些地方戲曲的應用,清新而具有強烈的民族氣息,充分表現來自大江南北、五湖四海的袍澤兄弟共同抗擊外敵。
三、表現戲謔和無奈的黑色幽默的插曲
東北兵迷龍撿了個媳婦上官戒慈,常扛著他那現成兒子雷寶兒,一邊扭著秧歌,嘴里哼哼唧唧的東北二人轉——情人迷:
“你要讓我來啊,誰不愿意來啊,哪個犢子才不愿意來啊……
你們家的墻又高,四處搭炮臺啊!就怕你爹用洋炮拍啊。”
用略帶粗俗的豪爽、好樂和一覽無余的戲謔,表現無家可歸的東北人渴望愛情和家庭生活與現實的矛盾心理。
再有就是迷龍和上官重逢那晚,導演用隱晦的手法來表現久別重逢的夫妻生活,當鏡頭在那群光棍兒輾轉難眠的身上緩緩掃過,配著中規中矩的二人轉音樂,這是很不協調的場景和音樂配合,讓觀眾也覺得莫名的煩躁,而這種心情恰恰就是那群睡不著的人當時的心情,看著別人洞房花燭還肆無忌憚地折騰一個晚上。通過這種表現方式,把觀眾戲謔般地帶入戲中人物的心境中去了。
最為反諷的是龍文章帶領殘部逃回禪達被審時,被迫招魂的那段背景插曲《土耳其進行曲》,表現的是諸多無奈的黑色幽默。
四、對戰爭、歷史的思考,渴求和平的插曲
《團劇》不僅在表現各種復雜的人物心理、戰爭的殘酷,同時也在表現對戰爭、對歷史、對人性的思考。戰爭是反人性的,戰爭就是由無數的炮灰用生命堆砌出來的。在十九集中,—個已經被逼迫到絕路的日本兵,自盡前在河邊絕望地唱著家鄉的民謠《故鄉》,我們能體會他的無奈和厭戰、思念故鄉、思念父母之情。也許因為他還小,還沒有被“大東亞共榮圈”這么“偉大”的理想沖昏頭腦,不理解自己在做“偉大”的“事業”(那時候的日本人一直認為自己是亞洲最文明的國家,而其他國家都是落后的,需要他們去“開化”。包括現在還有日本人在用這個可笑的理由去粉飾那場侵略戰爭)。在最后的時刻,他如同劇中中國軍隊的炮灰一樣,只有想念自己的父母、自己的朋友和遙遠的家鄉。如同旁白所說:“這也是一個迷失在異國他鄉的幽魂……”那些新兵把這幾個日本“炮灰”埋掉,也是導演對戰爭的思考,希望永遠不要有戰爭,不要把人變成冷酷的殺人機器。一個好的戰爭題材的影視劇應該是反戰的。
五、結語
一部優秀的影視劇,會因其優美的音樂而更加生動,插曲作為影視音樂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更是一部好劇的綠葉,使劇中形象更豐富、生動,更加立體化。它不僅起著烘托氣氛、表達感情、加強節奏等作用,還能構造人物的心理時空。因此,在影視劇中應充分調動音樂的各個元素,使其音樂內涵在一定程度上給觀眾傳達一種價值取向和時代觀念。
[參考文獻]
[1]李蕾.淺談電影音樂的構成[J].電影文學,2007(19)
[2]單建鑫,張躍進.中國當代電影音樂的文化特征解讀[J].電影文學,2007(16).
[3]李云階.論電影音樂[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4.
[作者簡介] 肖珣(1957—),女,四川瀘州人,副教授,西華大學藝術學院院長,四川音樂家協會、鋼琴協會會員,研究方向:鋼琴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