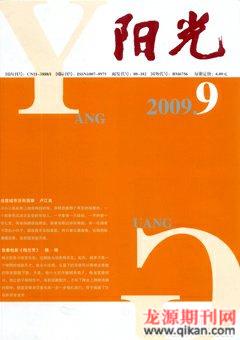重慶詞典
強 雯
夜不收
夜不收,在重慶是一個含有親昵成分的罵語。
過去是罵那些深更半夜都還不睡覺的人。讀書郎過了九點還不睡覺,就會被當媽的拿著雞毛撣子攆,嘴里罵著“夜不收”,作丈夫的熬夜看球賽被妻子磨叨“夜不收”。妻子罵丈夫,老子罵兒子,多指不務(wù)正業(yè),罵中含情帶愛。有些村民嘴刁,除了罵“夜不收”外,還帶一句“早不忙,夜心慌,半夜起來補褲襠”,借此數(shù)落那些迫不得已的夜不收。過去的人們都是安居守業(yè)的良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早睡早起是順應(yīng)自然規(guī)律。罵人者多是對的一方。
時過境遷,夜不收順應(yīng)了時代的發(fā)展,這個詞語的感情色彩更多地成了一種褒獎和羨慕。
泡吧的叫夜不收,洗腳的叫夜不收,去KTV夜總會的,都是夜不收。
現(xiàn)在的夜不收們,都是有應(yīng)酬的人。
有應(yīng)酬的人就是能人,是能混得開吃得香的人。那些下了班就去菜市場,做飯、洗衣,老老實實在家里守著老婆孩子的男人,反而被夜不收們恥笑。
有一個警察,除了睡覺,很少和家人說上兩句話,妻子說,你一天夜不收,娃兒都看不到兩面,還當不當這是個家?警察說,你莫看到我現(xiàn)在夜不收,那是還有人求,肯找我辦事,哪一天,我天天晚上在家里待著,這說明我已經(jīng)沒用了。
報紙的夜班編輯作息顛倒,凌晨兩三點下班,是夜不收;電臺的深夜主持人,踩著星光回家,是夜不收;出租車司機通宵營業(yè),也是夜不收。
名目繁多的夜生活制造夜不收。
夜不收這個詞,也越來越被現(xiàn)在的人喜愛。關(guān)于夜不收,在本地也有叫夜游神的,夜貓子的。南坪二小區(qū)有家燒烤店就叫“夜游神”,通宵營業(yè),尤其擅長烤魚,門面雖小,生意奇好。很有些江湖的味道。其實江湖中的人,都是有些夜不收的,走南闖北,跋山涉水,不以常人的作息為作息。
馬無夜草不肥,是不是說,夜不收的馬才是好馬呢?
重慶人一直以為,夜不收是本地俚語,因為我們從小就聽父母這樣數(shù)落,而父母的父母又這樣數(shù)落他們。其實,夜不收,乃是一個文言詞,只是很多人不再去追究它出自哪里,更不敢相信,它是元朝,及至明朝時期的間諜稱謂。
老臉包兒
楊家坪動物園幾年未進,也不知其中改變幾何?偶從新聞中得知,老虎誕子,孔雀遠嫁,公鴕鳥來渝定居,是之謂喜。我一同事童心大發(fā),攜小侄兒于周末抱著賞新獵奇之心,前去游玩。孰料,第二天,大家問如何,同事一臉晦氣,撂下“還是幾個老臉包兒”幾個字,再不肯多說一語。
臉包兒,望文生義,把臉都包下來了,是什么?是臉龐,可前面著一老字,知是有些年紀的人了,就是沒有多大的年紀,資歷也夠老了,混得行道深了,按照時下流行的話,叫資深臉包兒。
不過在重慶地道的方言里,上至官場,下至鄉(xiāng)野,老臉包兒一說倒是更常見。
“動物園里的老臉包兒”,準確地概括了我們小時候熟悉的動物園,是親切;無奈地透露出市動物園動物更新難的局面,是愁。這一句老臉包兒的點評,言簡意賅,形象生動,用在動物身上,卻又讓人忍俊不禁。
老臉包兒,等同于老臉,不過重慶人,總喜歡在一些聽上去歹毒的詞后,加上一個后綴,于歹毒中又有些調(diào)皮,讓人恨又不能太恨,喜又沒個理由喜,這樣的造詞法,倒顯現(xiàn)出重慶人的可愛俏皮來了。也不知是不是生物老了就遭人嫌,不然為何派生出這么多關(guān)于老的不好的名詞來?偏巧重慶人又愛給它潤潤色,添添味。
老臉包兒,在重慶也叫老板凳兒,老哥哥,老姐姐,老革革。其實革也是老的意思,想那粗革麻繩的樣子,可知皮之粗糙,質(zhì)之低賤了。在《三國志》中就有一細節(jié)是罵劉備為“老革”,可見也是有典故的,時至今日,重慶人又在老革后面加上一革字,聽上去老革革這罵腔里竟帶上了些情調(diào),試想,若是一女人半嗲半怒地罵一男人“老革革”,是什么味道?置換成重慶話,粗鄙一點,莫不是一唱三嘆的“死冤家——死冤家——我的死冤家喲!”
老臉包兒,在名利場里,更有其淋漓盡致的發(fā)揮。
每年娛樂圈都要搞一些不靠譜的獎項——諸如最佳風尚獎、最佳衣著獎,××電臺或電視臺最有人氣的男女演員等。這些所謂的獎項本身并沒有多少含金量,不過是借助明星的熟臉嘴來造勢,給自家商品或贊助企業(yè)貼金,不僅明星未必看得起,連普通老百姓都不知道這是哪里冒出來的獎項。最后,也落了個“外行看鬧熱”,老百姓看見的都是些平常見慣的明星,也沒什么新人,喧鬧了一通,圈里圈外都道“不過是老臉包兒”,如此收場。老臉包兒分獎項,叫分豬頭肉——見者有份,一人一塊。
如今各個行業(yè)都說自己圈里是青黃不接,都是些老臉包兒,從導演到演員到作協(xié),無一例外。老臉包兒在臺面上自謙地說,我們都是老臉包兒了,別人不煩,我們自己都煩,大會小會,大獎小獎,翻來覆去都是這幾張臉,老臉包兒語重心長地叫嚷著要新人,真有可畏后生者要重新洗牌,他們就擺出一副婆婆的模樣來,所以新人在老臉包兒里混是難的,是有代價的,不過這也是世間的規(guī)律,等到哪天,新人們由媳婦熬成了婆婆,歷史還得重演。
吹垮垮
吹垮垮在重慶方言里是個有極端感情色彩的雙性詞。在某些場合既可以顯得很仗義,很親昵,在另外一些場合則顯得很鄙視,很無能,頗有些外強中干的意思。
久別重逢,真情流露地吹垮垮;酒逢知己,相見恨晚地吹垮垮;談戀愛,花前月下地吹垮垮;作生意,明槍暗戰(zhàn)地吹垮垮。
喜歡吹垮垮,并且善于吹垮垮的人,古代叫說客,也有叫掮客的。總之吹垮垮的人是游走江湖的人,懂得察言觀色,投其所好,縱橫捭闔。是善捕人心者。
借吹垮垮而上位者,古有蘇秦,諸子百家,現(xiàn)有談古論今的各類電視講壇。
重慶方言的吹垮垮與北京話里的侃大山有異曲同工之妙。試看,吹與侃都是嘴皮子功夫,垮垮與大山都代表大物體,其實垮垮何嘗不是大山?不過是把山都給吹垮了,所以垮垮是山的另外一種物理形態(tài),在造詞方面,重慶人顯出了頑劣的一面。所以用垮垮來形容嘴上功夫,更勝一籌。
王朔在頗有自傳特色的小說《浮出海面》里,曾描寫一男孩死纏爛打追一女孩的情景,女孩嫌棄男孩太油滑,不踏實,一直不肯接受,有一天,男孩想了一招,又去找她說,“別人都叫我現(xiàn)代愚公。”女孩想了很久,不得其解,問:“為什么?”男孩說:“因為我在用嘴砍(侃)山。”這真是一語雙關(guān),女孩到底芳心被俘。王朔的這個笑話,和重慶方言“吹垮垮”真是不謀而合,愛吹垮垮的重慶人,何嘗不是現(xiàn)代愚公?北京有侃爺,重慶有吹哥。相得益彰,相映成趣。
只是,凡事過猶不及。
咬牙切齒、痛心疾首地說一個人吹垮垮,這個詞語,就顯得無比刺耳了。這時的吹垮垮相當于粵語里的雞婆、八卦。女孩罵男孩吹垮垮,多是男孩夸下海口,騙色又騙財,空許一樁好姻緣。上司罵下級吹垮垮,多是下級溜須拍馬,偷雞不成反蝕米。合伙人說同伴吹垮垮,是要與他恩斷義絕,江湖兩相忘。
一個吹垮垮怎么能具有這么極端的感情色彩!完全憑借說者的語氣,就可以上天堂、下地獄。
說來說去,還是這詞語背后的人。
非愛即憎,是重慶人的秉性。愛的時候,捧你,寵你,說你吹垮垮,是夸你是個貼心貼肺的可人兒。得空了,還三兩作伴,四五成群的邀請周末一起出來吹垮垮,是鞏固兄弟情,姐妹誼。
哪天翻臉了,恨你,咒你,說你吹垮垮,是要人們知道你是華而不實,胡編亂造,輕浮沒本事的浪蕩子。嘴狠的人,這時還會補上一句:“哼!吹垮垮!他的腸腸肚肚我都看得清楚!”
不懂的人,說重慶人翻臉比翻書快。
懂的人,說重慶人血性。
虧到唐家坨
菜園壩的農(nóng)貿(mào)批發(fā)市場,一個泥腿子跟另一個泥腿子殺價,突然一個人不樂意了,高聲喊:不賣了不賣了,虧到唐家坨了。
南坪八公里家具城,一個古典實木的茶幾喊價三到四千,買家一口氣殺到三百,說,你又不是紫檀木?大不了松木板板!我老家后院多得是,哄黑人沒曬過太陽嗎?賣家翻個白眼,心里估算了下利潤,手一擺:虧齊唐家坨!談都不想跟你談!
虧到唐家坨,有時也說虧齊唐家坨,都是一個意思:虧了,輸了,賠了。是否真實虧本了?不過是生意人的一個花招,就好像每天都有商鋪寫大字,跳樓價,賣血價,你要信的話,也就鉆進圈套去了,不信的話,還可以跟他磨一磨。
有不懂唐家坨典故的,反唇相譏:我還虧到李家坨了!虧齊朝天門!
說唐家坨的人也就哈哈一笑,少拿地名跟我犯渾。唐家坨就是唐家坨。
唐家坨?何方神圣。老爺子罵敗家子,一天就知道賭!你要虧到唐家坨!一代代傳下來,兒孫們只知名,不知意。
其實,犯這種典故錯誤的也多是重慶后生。
唐家坨是長江重慶段里的一個回水坨,人在長江淹死后一般流到該處就不再往下漂,凡在唐家坨以上落水的人,其家屬多在這里尋找尸體。重慶人好比喻,就用虧到唐家坨表示做生意失敗,只有投河自盡,流到唐家坨。
其實這個典故和垓下之戰(zhàn)也有不謀而合的地方。項羽敗局已定,烏江別姬,背水一戰(zhàn),孤注一擲,無顏見江東父老,雖然最后自刎而盡,但死得壯烈,就連烏江之水也要為之嗚咽,為之洪波涌起,濁浪翻騰。但到底還是一個“輸”。只是垓下現(xiàn)為安徽靈璧縣所在,不知道安徽是否有“虧到烏江”的俚語?要是此地為重慶人的地盤,恐怕就沒有后來“虧到唐家坨”的事了,“虧到烏江”估計要流傳千古了。
《歐也妮?葛朗臺》要是拍重慶方言版,應(yīng)該天天會說“燈火調(diào)這么亮,你想虧到唐家坨嗎!”布什總統(tǒng)來重慶做城市交流的話,也許會聳聳肩,學一句重慶話,國力不濟,股市崩潰,虧齊唐家坨了;福建等沿海一帶大批作出口的企業(yè),相繼倒閉,不得不說,虧齊唐家坨;喜歡把錢存在銀行的,坐收高息的人,也要一聲嘆息,說虧到唐家坨,今年緊急降息了。
穿穿兒
穿穿兒,對于一個安分守己,小富即安的地域來說,顯得尤為貶義。若干年前的重慶山重水復,山林與良田交錯,云遮霧罩,若一個人不安于耕作,不要說在祖國大地上馳騁南北,就是在這山城中,從一個村跑到另一個村,神龍見首不見尾,你就是那不務(wù)正業(yè)的人。尚未開化的重慶人便給這種異類取了個名字叫“穿穿兒”。
當穿穿兒被發(fā)明時,此地民風還很淳樸,人心大多善良,屬于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朝代。
農(nóng)民就該種地,教師就該教書,非富非貴的家庭,不老老實實地干活,東一榔頭西一棒槌,就算得到了一些便宜,也不長遠。
穿穿兒的貶義是因為這種人不走正途,走街串巷,這里收到了風聲,那里聽到了消息,看起來稀拉平常的一個人,卻明接暗合了許多社會關(guān)系,張家小兒成績不好卻要讀名校,他可以幫忙;羅家媳婦下崗想再就業(yè),他可以張羅;就是李家老爺子仙逝,他也可以跟墳場通融,占據(jù)風水寶地。穿穿兒看起來似乎無所不能,手眼通天,得過他好處的,恭恭敬敬叫他聲社會活動家,想得卻沒得到他好處的,在背后“呸”他一聲:穿穿兒!
這“呸”的一聲里,基本上濃縮了穿穿兒們的人生艱辛,人前風光的時候誰又知道穿穿兒的卑微和低賤的一面。
像針線一樣穿來穿去,堅硬銳利的是針頭,柔軟綿長的是線身,只要有一分小利,穿穿兒就要去鉆,就要去順應(yīng)。他們深諳長袖善舞之道。最開始是為著自己,但不是每次都能獲得實利,盤枝錯節(jié)的關(guān)系,他們開始穿,漸漸地穿出一張網(wǎng),當一些出其不意的關(guān)系開始呼應(yīng)時,穿穿兒便得利了。
穿穿兒,說到底了,只是一種角色,一種生存角色。這樣的角色,前有古人,后有來者,地球村沒他不行。掮客、好事者、社交名媛……是穿穿兒的雅稱,是穿穿兒的字號。眾所周知的美國成功學家卡耐基說,一個人的成功,15%取決于你的專業(yè)知識,85%則取決于你的社交能力。民間的穿穿兒雖然不懂名人名言,他們卻身體力行地實踐著左右逢源的好處。
換成重慶話說,卡耐基也曾是一個穿穿兒,他出身于農(nóng)家,做過教師、工人、推銷員、演員……工作,但這些都不是他理想的工作,他始終認為過有意義的生活比賺錢更重要,他決定白天寫書,夜間去夜校教書,以賺取生活費。于是他說服了紐約基督教青年會的會長,同意他晚間為商業(yè)界人士開設(shè)一個公開演講班。從此,他開始了一生成功教育事業(yè)。只是一個人名利雙收后,老百姓是不會再叫他們“穿穿兒”了,只會稱呼他成功人士。崇拜者們還會不計前嫌地送他一頂“英雄不問出處”的高帽。
所以,穿穿兒的社會地位還是比較低下,是屬于那些即便是有一定社會關(guān)系,卻始終在小圈子里,比如說一個管轄區(qū),魚洞、合川、萬縣等某個區(qū)縣玩的轉(zhuǎn),或某個行業(yè),醫(yī)院、健身中心吃得開的角色,而萬幸中的不幸是:他們的社會關(guān)系如此局限,又或是他們整日為蠅頭小利而困擾,他們的人生也因此很難再上一個臺階,時至今天,他們便有了更為刻薄而精細的稱呼:藥穿穿兒——給醫(yī)院推銷藥的二級代理;學穿穿兒——以各種名目為高校聚財而招生的人;房穿穿兒——謀取黑利的房屋中介。
吃豁皮
深巷里弄,豆花飯熱鬧,吃到酣處,猛聽得一聲,“你娃吃豁皮!想都莫想。”眾人一驚,停箸張望。那食客不得不掏出錢,鼠竄而逃。
公交車改為自動投幣后,乘客魚貫而入,難免逃票漏票之人,終被司機發(fā)現(xiàn)端倪,怒目側(cè)身相向,“吃豁皮的,補票!不補票不開車。”
某貪官被雙規(guī),百姓互告,“又扳倒一個吃豁皮的,該!”
吃豁皮者,不愿眾目睽睽下被指責為“吃豁皮”,大都以“忘了”“打瞌睡”“不知情”為借口,搪塞其辭,事若不敗,洋洋得意,吃豁皮一次比一次膽大,事若敗露,嘴上仍舊不服輸,要豁皮兩下。這是因為,吃豁皮比吃白食,比鐵公雞聽上去更粗野,更讓人無尊嚴。
其實吃豁皮一詞之始,并非來自于“人之初性本惡”之說,天天說別人吃豁皮的,被人罵做吃豁皮的,大概不知道,豁皮的出生倒是頗有些人道主義情懷。某干年前的村野,打家具的木工是令人驕傲的行業(yè),娶親辦喪,少不了他們的活計。只是不管木頭好歹,總得刨去原木的表面,那就是豁皮。豁皮有什么用?沒用!做不了凳子做不成床,莫說當正料,連余料都沒它份,堆在一塊還占地方。
東家的汗毛比奴腰壯。
窮人只要說行行好,就可以撿回去當柴燒,墊雞窩,甚至塞塞門縫,擋擋寒風。于是吃豁皮也就成了白撿便宜的意思了。
現(xiàn)在,吃豁皮雖說惹人厭,但看豁皮到成了樂事。街邊耍雜,夫妻斗架,乞兒行討,總有大幫人圍觀,此為笑豁皮,看豁皮,看稀奇,看熱鬧,不看白不看,不笑白不笑。
商家就喜歡大伙看豁皮,“看豁皮,看豁皮!新出的××手機,10塊錢話費送你手機。”于是看豁皮的人里三層外三層,有豁皮撿,騰點時間算什么。
驢行者也常以“某處當豁皮,發(fā)呆,神游”為由頭,招募更多的玩家,同去探險游樂。
有時間去看豁皮的,當然是閑人,所以如果談?wù)撃橙耸腔砥?往壞了說,是個耍客,蹉跎不得志,游手好閑,往好了說,那是性情中人,淡泊名利,野鶴閑云。
鄰里村人雖不懂陶潛雅興,但明白過后,他們會抬起勞作了一天的腰,對著南山,直白地說,采菊東籬下,悠然一豁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