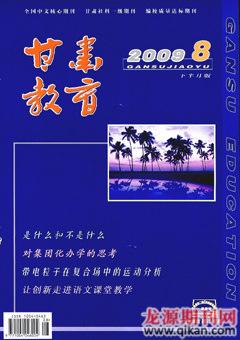是什么和不是什么
文 雨
當下社會中的許多事情讓人頗費思量,而紛紛擾擾的學術界更是進入了一個多事之赦。令人眼花繚亂。有時候你會感覺很熱鬧,到處都有頂著專家、學者甚至大師頭銜的人在談經論道,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有個什么家站在你的面前;有時候又會覺得很虛無,舉目四望,好像真正名副其實的專家學者很難我出幾個來,更不要說什么大師了。而學術腐敗的日益嚴重,學術造假的丑聞日增,更讓人懷疑,在我們的學術領域究竟還留存于多少未被污染的凈土?還有多少名人學者值得人們尊重和信賴?還有多少專家、教授仍在堅守著自己的道德底線?
季羨林和任繼愈兩位先生的相繼去世,引發了中國到底有沒有大師的新一輪爭論。其實,有沒有大師,誰是大師,不是哪個人可以說了算的,甚至也不是當代人可以說了算的,從歷史的角度看,真正的大師大多是后人封授的,而在他所處的時代,并不會得到多少追捧,有些還曾飽受非議。所以,現在討論誰是大師的問題,似乎沒有多大的實際意義,因為是不是大師,能不能成為大師,都是需要歷史檢驗的。這和當官不一樣,只要有關方面任命了。一切就成了定論,不管這個人到底稱職不稱職。
季羨林老先生在這方面真是個明白人,他知道一些人給他戴上的“大師”、“泰斗”、“國寶”等桂冠都是靠不住的,所以在他生前就一一辭謝,免得身后授人以柄,非但帶不來什么榮譽,反而為其所累,甚至自取其辱。不如推它個一干二凈,讓歷史去做最終的結論。
遺憾的是,現在像季老先生這樣的明白人不多了。在這個浮躁而又功利的社會里,很多人浮名唯恐不大,桂冠唯恐不多,炒作唯恐不火,以至于不惜采用剽竊造假等非法手段來謀取名利,或者采取娛樂明星式的另類方式來吸引眼球,可謂無所不用其極。他們就是不明白一點,人生的大廈必須要有深厚的根基來支撐,用搭積木式的急功近利的辦法是徒勞的,全得越高,垮得越快,弄不好還會身敗名裂,連普通人也做不得了。
其實我們只要認真思考一下就會懂得,在這個信息高度發達、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一個人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內搞出點成績或許相對還比較容易,倘若借助現代傳播渠道加以炒作,更有可能形成一夜成名的美麗泡沫,但要真正取得超越歷史、超越前人的成就,真正為業內、為歷史所認可,絕非易事。如果說,過去的人們可以憑借一本書,一項發明,幾幅字畫,甚至幾句短詩就可以留名千古的語,那么在信息時代的今天,如果沒有相當的建樹,要想不被淹沒,名垂青史,基本上沒有多大的可能性。多數人注定只能像流星一樣一閃而逝,最多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圍內得到認可,不要指望會獲得多么崇高的地位。所以,一定要以一顆平常心來看待自己是什么,不要生活在虛妄和幻覺之中。在我們所處的這樣一個時代,孜孜以求猶恐不得,還敢張狂自詡乎?
前不久看蒙古族歌唱家德德瑪接受電視采訪,她用很平和的話語對自己作了這樣的評價:我只不過是唱了幾首歌,沒有別的什么貢獻,根本算不了什么,不值得大家這樣對我。聽完這些話,讓人不由心生感慨:作為一個生活在名利圈中的人,居然能有這樣的清醒認識,能有這樣的人生智慧。真是難能可貴。因為我們聽過太多“成功人士”的感言,只要有機會,他們會滿懷自信地談自己的不同凡響和豐功偉業,談自己的高風亮節和無私奉獻,很少會有人說自己什么也不是。
一個人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看似一個簡單的問題,但能弄清楚的人還真不多。也正因為如此,才使得許多人在竭力追求“我是什么”中迷失了自我。我們經常會認真閱讀別人遞上來的名片,為的是了解這個人是什么,結果看了一大堆頭銜后,反而不清楚他是什么了,以至于不知道到底該怎樣稱呼才不失“尊重”。這也是季老先生之所以值得稱道的原因,因為他選擇了“不是什么”,不但把自己解脫了,也把別人解脫了,因為你不用刻意去想怎樣稱呼才算恰當,才會令對方滿意,一聲季老先生或季老師,足矣。
能夠清楚自己不是什么的人,才稱得上是活得明白的人。因為“不是什么”,是一種人生的大境界,大智慧。大覺悟,大超脫。“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后事”,何苦非要在短暫的人生旅途中苦苦追尋那些靠不住的浮名呢?
然而現實中就有這樣的人,總是沉淪于名利場中,總是不厭其煩地利用各種機會來向世人證明自己“是什么”。這里可以試舉兩側:一個是曾陷緋聞的趙忠祥,最近為推銷自己的新書又跳了出來,極力表白自己是一個“道德很高尚”的人,是全中國最優秀的主持人;一個是備受質疑的余秋雨,對“詐捐”事件極盡辯解粉飾之能事,以維護自己“文化名人”、“正人君子”、“道德化身”的形象,在很愉快地享用著粉絲們授予的“大師”桂冠的同時,居高臨下地把批評他的人統統歸入了文化小人之列……
這里引用一下曾在另一篇文章中寫過的一段話:當一個人認為自己什么也不是的時候,那他便有可能是什么了;反之,當一個人覺得自己已經是什么,而這種感覺又變得越來越強烈時,即便他原來真的是什么,那么現在也會變得不是什么了。這個觀點,在上述幾位名人身上是不是得到了很好的驗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