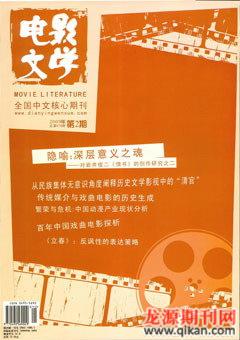2009年賀歲片中的后現代主義元素
尹 興 王柄皓
一、后現代主義電影理論
與現代主義相對的后現代主義是20世紀60年代興起于法國,并從美國等地迅速波及全球的一種文化思潮,它以解構中心的多元世界觀、用文本話語論替代世界本體論等為特征。利奧塔曾說過:“用極簡單的話來說,我將后現代定義為針對元敘事的懷疑態度。”后現代的重要特征是拼貼及由此產生的意義顛覆。20世紀60年代以后,西方社會經歷了危機和動蕩的時代,嬉皮士、反文化和性解放思潮的泛濫,反映了青年一代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憤懣、反抗和精神上的混亂。后現代主義就是這個時代的產物。
后現代主義電影理論是研究現代主義電影之后的電影美學思潮和傾向的批評理論。與現代主義電影迥然不同的另類電影為后現代主義電影批評提供了研究的對象。它們往往以反文化的立場顛覆傳統藝術電影的深度思考,以消費主義姿態拼貼五花八門的藝術技巧和手段。從蒙太奇轉向拼貼的電影語言,是后現代主義電影的標志。其作品常采用反常的情節結構、漫畫式的敘事基調、混雜的拼貼方式、電視廣告式的美學語言、黑色幽默的暴力詩學、反諷和滑稽模仿手法。“后現代電影傾向于將社會的語境散入敘事語言的迷霧中,使觀眾對堂而皇之的歷史言論,或歷史上的偉大‘推動者和偉大的主題產生懷疑,并以平凡的小人物、平凡的主題、平凡而瑣碎的故事或利用宏大敘事與平凡話語間的雜糅、拼貼和交替衍生來反襯、嘲弄元敘事的理性偏激。”
國產賀歲片通過保持大眾文化藝術性與商業性的必要張力,盡量滿足觀眾的視聽快感,強調消費性能指,稀釋人文內涵,填平美學深度,暗中契合了后現代主義文化的眾多特征。“馮小剛的‘賀歲片真正推動了后現代主義在中國電影中的發展運用。《甲方乙方》、《不見不散》、《沒完沒了》、《大腕》等幾部票房與口碑俱佳的賀歲片,從客觀上推動了大陸電影的發展。中國第六代電影導演張元、王小帥、賈樟柯、寧浩等人的作品,同樣充滿了后現代主義文化因素。無論是賈樟柯的‘三部曲,還是寧浩的《瘋狂的石頭》,都體現了后現代主義對人生存的艱難與尷尬的黑色幽默與反諷。”
二、平民意識——大眾性與世俗文化
賀歲片一以貫之的是濃濃的平民意識。在題材選擇上,常常拒絕宏大歷史場景,選取貼近觀眾日常生活的現實及在此基礎上的市民想象來架構故事。今年的賀歲片亦如此,與一般的武打片不同,電影《硬漢》貫穿始終的“平民化”的社會英雄形象,讓眾多觀眾感動不已。電影宣揚的是見義勇為的英雄情懷,塑造出來的卻是一個智障的退伍軍人英雄形象。導演通過這種夸張的戲劇表現,把“平民超人”的形象突顯出來,不斷強調做人向善,摒棄了“江湖片”中大動干戈的槍戰血腥場面,讓“紅纓槍”成為劉燁手中的武器,代表了一種無堅不摧的堅定信念和對人性的思考。影片站在平民主義的立場上,對“英雄模式”進行解構和顛覆,表現出的現代生活的變化已經徹底消解了神話中的英雄性格,這無疑是后現代文化的重要特征。
《硬漢》導演丁晟說,“完全是被電影原型人物打動,想不到我和孫紅雷、劉燁他們聊這個人物時,他們都非常的興奮,覺得這樣的人物在中國的電影幾乎沒有出現過”。劇情公布后,不少觀眾指劉燁出演的老三形象有點傻,丁晟表示,“其實這是觀眾沒有真正理解這個人物,老三可以說是很單純很有力量的人物。找到劉燁塑造老三的角色,其實是通過比王寶強‘傻根更‘傻的形象來傳達中國男人的品質,老三這個人物擔當的社會責任更理想化”。影片中的主人公不再負載沉重的主流意識形態,崇高、理性、法則、社會、人生、道德、倫理、歷史、政治等一切理想主義的東西,一切理性文明所造就的等級秩序在因歷史和現實的紐結而蘊蓄成的沖擊波面前變得淡漠。
紅纓槍年代的中國雖然經濟落后,人們的心靈莊園卻很純潔,人們都恪守著自己的道德底線。導演或許正是基于對這種純真年代的懷念和對當下社會的無奈與失望,才塑造出了老三這個靠拳頭說話、用紅纓槍懲惡的弱智英雄。從這個意義上講,電影《硬漢》是導演構建的渴望社會回歸理性、回歸大眾的一個精神家園。
三、消費主義文化主導的游戲電影文本
杰姆遜在《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中說過:“在后現代主義中,由于廣告,由于形象文化、無意識以及美學領域完全滲透了資本和資本的邏輯,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藝術、無意識等領域是無處不在的。”商品化表現在電影的制作中就是一切以市場為導向,把觀眾奉為上帝。于是,京式幽默語言、生活化的搞笑、明星聚集,還有頂梁柱葛優的生死同盟等等,成為賀歲片的標志,也因此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深刻的后現代主義烙印。在賀歲片里,充滿在喜劇氛圍中的是大眾的世俗心態和瑣碎情感,這些都與崇高、偉大、精英意識等無關,大眾化、平民化、世俗化和解構性,是賀歲片所顯現出的后現代特征。后現代文化也借此與商品化緊緊聯系在一起。消費主義的價值取向使電影成功地與贊助商聯姻。借助明星的市場號召力,賀歲片將“日常生活的意義在于其消費性和個體欲望的滿足性”的信念深深注入觀眾的心中。
賀歲片《愛情左燈右行》亦如此。十二位明星分別呈現出當代男人的極端典型,一一彰顯迥異的性格特征。他們各自代表不同的社會階層,將十二種不同的精彩匯聚而成一幅當代中國男性世界的全景圖,讓我們看一看片方經過網絡票選后的所謂型男名單吧:鄧超、黃曉明、黃磊、范偉、佟大為、聶遠、陸毅、蘇有朋、古巨基、林申、張峻寧、保阪尚希。不難理解,僅憑此演員陣容便足可以詮釋賀歲片的商業本性,換言之,是赤裸裸的商業娛樂不可能失敗的成功路子。賀歲片的喜劇模式及其喜劇因素,是迎合了當下社會和觀眾的一個審美熱點,這與后現代消解悲劇感和深度感的思潮有一定的聯系,與大眾審美的世俗化走向和消費心理有直接的關系。具體表現如下:
一是情節上的游戲性:在影片《桃花運》中,一群身份、年齡各異的都市男女里面,有想把貞操保留到世界末日的“剩女”,有絕望的主婦,也有一心只吊金龜婿的摩登女郎,有尋找靠譜伴侶的海歸,也有只想追中年婦女的……桃花運以不同的方式降臨在他們身上,這樣的情節設置本身便極富游戲性和戲劇性。
二是語言上的游戲性:影片《桃花運》中,諸多明星除了在造型上顛覆之外(葛優的長發),還充斥著大段看似平淡的情話,如被范冰冰用家鄉煙臺方言說出的“那就好好過唄”,一出口就讓人忍俊不禁。影片中還有很多令人捧腹的臺詞,影片運用調侃、反諷的語言,充分發揮語言的豐富性及其詼諧、幽默的表現力。而調侃本身就是一種消解和嘲諷,往往借助于語言和語境的不一致,能指與所指的不和諧,形式與內容的相矛盾,用游戲的手段消解它所敘述對象的恒定性和完整性,消解了價值觀念和歷史的權威意識。耿樂和梅婷塑造的形象之所以令觀眾印象深刻也和他們的臺詞有關,耿樂扮演的海歸派時不時來幾句一本正經的英文,而梅婷則是南京話貫穿始末,純正英文面對地道南京話,這種組合給影片帶來了新鮮感。喜劇性產生的重要原因,一方面是有葛優這樣的笑星出場,另一方面自然得歸功于游戲性的臺詞。
四、結語
后現代主義文化與當今社會的高度媒介化和高度商品化聯系在一起,它追求平等、民主、自由,要求文化的共享和形式的多元化,尊重每個人的選擇。“大眾化、平民化、非貴族化是中國‘后現代文藝的一個顯著特征”,2009年賀歲片無疑很好地應和了這一趨勢。這類純消費型、娛樂型的賀歲片在運用調侃、戲擬、游戲化、拼貼等后現代表現手法的過程中,消解了嚴肅、傳統,滿足了觀眾潛意識宣泄的需要,實現了后現代性的文化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