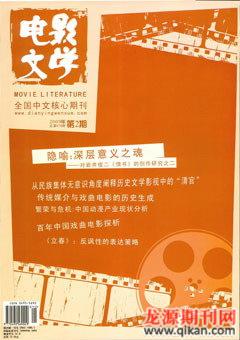脫節的時代 斷裂的時間
徐子昂
[摘要]哈姆萊特的悲劇故事中潛藏著一個通過儀式。通過儀式由分離、過渡和融合三個階段組成。父王被弒標志著王子與過去的分離。置身于過渡階段之中,他必須做出選擇:是融入一個缺乏道德依托的世俗社會,還是回歸過去的神性秩序。哈姆萊特把這個艱難的選擇轉化為“to ba or not to be”的追問。這是一個具有現代性意味的追問。現代性的降臨使得過去和未來在當下斷裂。身處其中的人們面臨著如同哈姆萊特一樣,都在經歷著一個難以完成的通過儀式。
[關鍵詞]哈姆萊特;通過儀式;現代性
人生必須經歷各種不同的階段,如誕生、成年、婚嫁、喪葬。這些階段的轉換常帶來身份的轉變與權力資源的重新分配,成為個人和社會必須面對的關鍵時刻。通過儀式便是社會應對這種轉化的手段,以實現階段之間的平穩過渡,維持社會結構的穩定。法國人類學家阿諾德·范·吉納普(Arnold van Gennep)在《通過儀式》一書中指出,通過儀式(rites de passage)由三個階段構成:分離、過渡以及聚合。分離儀式象征的是與過去狀態和舊身份的分離,如在中國的婚慶禮俗中,女兒出嫁前須向父母敬茶道別。聚合儀式象征著個人接受了社會對其身份的重新設定,以新的身份進入新狀態,比如兒媳在婚禮次日早晨向公婆敬茶,正式成為新家庭的一員。介乎二者之間的就是過渡階段,顯示出的是一種既不屬于過去,也不屬于未來的無限定狀態。如婚禮上已經告別了娘家,但又沒有被夫家正式接納的新娘。從時間順序上看,分離意味著過去的結束,融合意味著未來的開啟。而過渡階段則指向當下。
英國學者維克多·特納重點研究了過渡階段。在《儀式過程——結構與反結構》一書中,他指出,通過儀式是從結構到反結構,然后再回到結構的運動。其中,過渡階段具有明顯的“反結構”特征。結構是指平常的時候人與人之間明確的社會等級差別,但在過渡階段這些差別會被人為抹平,曾經顯赫的人物喪失了過去所擁有的地位和尊重,甚至遭到戲辱。比如在婚禮上,新郎必須忍受同輩未婚男性乃至小輩的戲弄。特納認為,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保證新成員對新秩序的尊重,有助于消除人們對新成員的疑慮。
美國學者布魯斯·林肯把注意力轉向社會上處于弱勢的女性。他對女性成年禮的研究表明,為了實現身份轉換,儀式長老要采取一些強制性手段。其中,男性長老往往以暴力脅迫女性成年者就范:“他們割傷她,強奸她,或是逼迫她奔跑、工作和熬夜。”而女性長老給予女性成年者的則是勸誘:“她們幫她穿衣打扮、為她送飯,陪她熬夜。”最終,女性成年者被塑造成真正具有自我節制能力的成員,如馴服的妻子,撫育兒女的母親。總之,女性的成年就是在社會整體秩序的脅迫和勸誘下告別童年時代,接受成人社會對其的角色定位。這種強制是迫使新成年者放棄舊身份,接納新身份的重要手段。由此,林肯指出了過渡階段的社會功能:“改變社會成員的角色、地位和身份,用新的取代舊的。”
吉納普和特納的研究表明,通過儀式保證了社會整體秩序在時間維度上的延續性。其中,過渡階段雖然令社會秩序暫時中斷,但作為兩種狀態之間的連接點(joint),過渡階段既能夠吸收過去,又能夠開創未來,從而把新與舊、過去與將來之間的對立消弭在當下之中。“在這個意義上,當下就不再是過去(was)和未來(yet-to-be)之間的斷裂,而是集歷史與可能性于一身。新成年者所立足的正是這樣的當下”。但布魯斯以女性為對象的研究則提出了一個問題:處于弱勢地位的個體該如何應對社會對其身份的強行改變?是順從地接受新身份還是捍衛童貞?一方面儀式對象必須成長,另一方面未來又缺乏足夠的道德支撐。是故,儀式對象被“卡”在兩種身份之間。于是,在個體身上,過渡階段沒有聯接起過去和未來,反而令二者在當下斷裂,使成長變為一次充滿困惑的經歷。這種困惑又廣泛存在于歷史進程之中,從而成為一個關于社會發展的原型。
當個體被置于過去與未來的斷裂之中時,他們迫切地需要解決“我是誰?”的問題:是順從地接受新身份還是通過反抗來捍衛童貞?這個問題被莎士比亞的哈姆萊特轉譯為: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對于To be or not to be的矛盾,哈姆萊特進一步解釋道:“默然忍受命運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無涯的苦難,通過斗爭把它們掃清,這兩種行為,哪一種更高貴?”這之所以會成為一個問題,是因為哈姆萊特所經歷的是一個錯綜復雜的通過儀式。但這個通過儀式并沒有讓哈姆萊特順利進入成人世界。相反,它讓哈姆萊特陷入到過去與未來的激烈沖突之中。
在年輕的哈姆萊特王子準備踏入成人社會之時,叔父克勞狄斯毒殺了父王,僭竊了王位。這是一個分離儀式,切斷了王子與他所屬的社會文化之間的聯系,使其失去了界定自身文化身份的參照物。隨后,成年禮進入了過渡階段。父王所代表的信仰和秩序被全面顛覆,社會呈現為特納所說的反結構。在意義的層面,反結構挑戰了哈姆萊特的道德底線。在秩序的層面,反結構令哈姆萊特身份突降。作為王子,哈姆萊特曾是“朝臣的眼睛、學者的辯舌、軍人的利劍、國家所矚望的一朵嬌花;時流的明鏡、人倫的雅范、舉世矚目的中心。”(三幕一場)但在反結構中,王子被剝奪了嗣位的權力,遭受到“命運的暴虐的毒箭”(三幕一場),被迫面對“人世的鞭撻和譏嘲、壓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輕蔑的愛情的慘痛、法律的遷延、官吏的橫暴和費盡辛勤所換來的小人的鄙視。”在哈姆萊特看來,這樣的反結構就是一個顛倒混亂的、“脫節了”的時代:The time is out of joint,在英文中,Joint是關節、接合點的意思。時間本是按照過去、當下和未來的線性方向發展,當下是承接過去和未來的接合點。但在哈姆萊特眼中,僭王否定了既有的社會秩序和價值觀,打斷了時間的延續性,導致了過去和未來之間的對立。于是,當下不再聯結過去和未來,而成為二者之間的斷裂點。身處斷裂點之上,哈姆萊特陷入了對未來的兩難態度之中:他必須在To be和not to be之間做出選擇:要么接受未來,要么回到過去;要么“默然忍受命運的暴虐的毒箭”,要么“挺身反抗人世的無涯的苦難,通過斗爭把它們掃清。”長期以來,學界對To be or not to be的理解進行了諸多的討論,而多元的解讀大都源于動詞be本身所具有的豐富語義。動詞be既表示生命和存在,也表示存在的方式和樣態。這樣,to be or not to be既可以指對是否存在進行選擇,也可以是指對不同的存在樣態進行選擇。如果把to be or not to be理解為生存還是死亡,那么生存對應的就是忍受,死亡對應的就是反抗。但王子隨后告訴自己,“死了;睡著了,睡著了也許還會做夢;嗯,阻礙就在這兒:因為當我們擺脫了這一具朽腐的皮囊
以后,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將要做些什么夢,那不能不使我們躊躇顧慮。”(三幕一場)。哈姆萊特用這段話道出了死亡的無意義。難道這意味著王子對反抗的主動否定?這顯然違背了王子復仇的本意。如果我們把注意力轉向動詞be的語法形態,便會發現,動詞be出現在不定式之中。而不定式在時間上指向將來。從這個意義上講,to be是對未來生存狀態的肯定,not to be則是其的拒絕,與之對應的就是was。這樣,to be or not to be所標示的就是未來和過去之間的分野。
哈姆萊特對死亡的反思讓我們看到,to be or not to be是一個兩難的選擇,中間沒有第三條道路可走。固然,用自殺來逃避選擇為宗教律令所不允。但更重要的是,即使是死亡也無法消除“我們心頭的創痛以及其他無數血肉之軀所不能避免的打擊”,(三幕一場)正是由于死亡也無從釋解王子的困境,才導致“人們才甘心久困于患難之中”。(三幕一場)在獨自中,哈姆萊特用大量的篇幅來探討死亡。他不是要用死亡來襯托出信仰的終極價值,不是要將獲得救贖的希望寄托于天國,而是要指出即使是彼岸世界也無法引導人類走出To be or not to be的兩難選擇。因此,To be or not to be不是對終極意義的宗教式追問。它所討論的是一個比生與死更為“現代”的主題。這個主題充滿了對現世的關懷,它將人置于歷史發展的維度中,在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沖突中,去考察人們究竟該如何超越自身的存在,如何在此岸世界獲得自我救贖。由此,哈姆萊特王子在成年禮上所遭遇的兩難選擇也就顯現出了濃重的現代性意味。
現代性是傳統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轉型的產物,代表著迄今為止人類社會演進中的一次最深刻的、全方位的斷裂。“由現代性而產生的生存模式,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們拋離了所有傳統形式的社會秩序的軌道。在外延和內涵兩方面,由現代性引發的變革比此前時代的絕大多數變革特性都更加深刻。”作為斷裂的結果,現代性一方面體現為宗教式思維的衰微,也就是“上帝之死”。另一方面體現為古代神性結構的崩解,即“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從人類學的角度看,斷裂和上帝之死是一次分離,而“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則暗示著一個反結構的過渡階段。因此,我們可以把現代性的降臨看作是一個過渡階段。如果我們再把人類社會的發展比作個體的成長,那么現代性就是人類社會的成年禮。這個成年禮雖然讓人類社會從農業文明過渡到了工業文明,卻將人類置于過去與未來的對立之中,深陷于新與舊、理性與信仰之間的糾葛紛爭。所以,現代性又是人類遲遲無法完成的一個成年禮。
在這個成年禮上,現代性的斷裂根本性地改變了前現代社會的時間圖式。“在傳統文化中,過去受到特別尊重,符號極具價值,因為他們包含著世世代代的經驗并使之永垂不朽。傳統……是駕馭時間與空間的手段,它可以把任何一個特殊的行為和經驗嵌入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延續之中。”但是現代社會不再以一個神圣的過去作為歷史源頭。當下不是古代光榮的延續,而是新歷史的開端。時間的歷時性被共時性所取代。這樣,時間的連續性被打斷,現在就成為過去和未來的斷裂點。
在現代性的沖突中,無論選擇過去還是將來,都具有合理性。奔向未來被視為進步,而回歸過去也具有足以說明自身的道德理由。當向前和向后都有著充分的理據時,人的悲劇性就在時間的沖突中鑄就了。這種悲劇性并非是由于個體的性格缺陷所至,而是作為一個結構性難題內嵌于社會發展的原型模式之中。自現代性降臨以來,人類一直深陷于這種悲劇之中,體味著它所帶來的困惑與無奈,并使之在情感的維度中沉淀,成為文學寫作的母題之一。To be or not to be的兩難選擇承載了這種悲劇性,哈姆萊特的困境就是現代人的困境。盡管《哈姆萊特》借用的是一個中世紀的復仇故事,但哈姆萊特卻喊出了現代人的困惑:未來還是過去,這是一個真正的問題。由此,成書于1601年的《哈姆萊特》就成為能夠代表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最典型的文化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