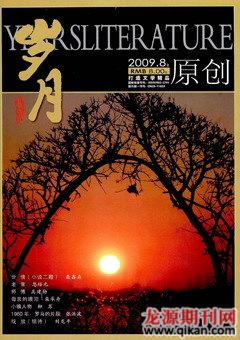蛙聲里的美麗和哀愁
王朝明
夏至剛過,所在的這個城市迎來了一場暴雨。老天爺不問人間事,節水意識不合時宜地淡薄,出手闊綽,瓢潑盆傾,大雨下了整整一天。晚上,雨才漸漸停了,半個月亮還翻上了小區旁邊的山坡。
推開窗子,風倏然吹走了屋里的溽熱,帶來撲面的清涼。隨風而來的,還有驟如急雨的蛙聲。
月色撩人,蛙聲盈耳,這對蝸居城市的人來說未免有些奢侈。而倘若不是因為這場雨,我壓根兒也不會相信,小區邊這座草木稀稀拉拉、平日里總是被浮塵弄得灰頭灰臉的山包,竟然如特洛伊的木馬一般,藏著這么多不帶半片甲卻膽敢把纛鼓擂得山響連天的肆無忌憚的兵士。
青草池塘,十里山泉,只要有蛙聲的地方,這斷然是不可或缺的——不管是在現實的自然中,還是在名士的詩畫里。而這兒,不過是城市夾縫里一座很快就會被房地產開發商的挖掘機啃食掉的荒坡,若非下雨,連個水洼都不見,更不消說池塘、山泉了。那么,它們肯定不是這里的土著,不是來自于原生的蝌蚪,而只能從遙遠的城市外圍遷徙而來。古希臘的勇士們之所以能夠潛入特洛伊,畢竟多虧了那匹虛懷若谷的木馬。而它們,該是怎樣穿越了城市密密麻麻的樓柵與縱橫交錯的街道,怎樣躲過了川流不息的車輪和摩肩接踵的人群,又如何踩著夏天的腳印準時抵達這座深陷城市重圍幾乎已被拔地而起的高樓蠶食殆盡的小山的呢?可以想見,滾滾的車輪,革履和尖屐,頑童的一個小小游戲,饕餮者大張的嘴巴,會輕而易舉地使行進遷徙中的蛙的生命以及夢想休止。柏油路是呆板且冰冷的,它還跟城市一樣健忘,它不會讓一個個曾經血肉模糊的蛙印在記憶里保存很久,碰撞,碾壓,風干,然后零落成塵,是它對待所有卑弱的進入者和不幸的仆倒者一貫的態度。沒有什么會讓盔甲堅硬力量龐大陣腳威嚴的城市有所畏懼和動情,不管是一場百年不遇的暴雨,還是月光里的一片天籟蛙聲。
苦難只是苦難者的苦難,對于旁觀者,苦難有時還會散發出美麗的芳香。就像善良的人在為希臘神話里一個個悲劇的英雄而扼腕之余,有時會驚詫于自己為何沒有了本該有的悲憫和憤怒,在心頭回蕩的,反倒是一種類似于月光下的蛙聲的美麗和憂傷。
山上的蛙聲繼續著方才的節奏。天地為舞臺,夜做帷幕,這是一支毫不在乎有沒有聽眾的鼓樂隊。這里沒有指揮,也沒有歌星,每一個鼓手都忘情投入、全神貫注、旁若無人。這些天籟之聲的制造者們當然也不會理睬我的疑問和困惑。此刻,我以近20年的鄉村生活經驗可以想象得到,無數熱忱的鼓手正散兵一樣臥在潮濕的泥地里,雨滴順著濕淋淋的樹葉滑下來,落入草叢,砸中它們的頭頂,濺開,而后者兀自巋然,絲毫不為所動;動的,只有它們的頜,還有起伏的腮鼓。
蛙聲連綿,月色朦朧,雨后的城市之夜是少有的寧靜。這樣的情境要是用來做一些令上帝常常發笑的思考,真是暴殄天物。但上帝盡管發笑,我的問題和憂慮又來了。
青草池塘,草莽之地。出于草莽的蛙是鄉野的鼓手,像田里的牛、村頭的狗還有遠方的城市一樣,在鄉野溫柔寬厚的目光里,走得再遠,蛙也是她的孩子。這些蛙們,從田間野陌,從青草池塘,從偏遠的山溪,遠道跋涉而來。忘了一路走來的流離與顛沛,忘了踟躇街頭的無助和彷徨,忘了遭人踐踏的痛楚及憤怒,一爿暫且棲身的山坡就足以讓它們隨遇而安,一陣偶然潑灑的雨霖更令它們歡欣鼓舞,一座堅硬冰冷的城市絲毫沒有影響它們以熱烈的歌聲抒發對生活的愛和憧憬。可是,夏天是個熱烈的季節,這個季節最適合表達愛情——當然,這不僅僅對人類而言,對蛙族也是。青蛙也有愛情。愛情還會結出果實。青蛙的愛情之果當然是蝌蚪。可是,問題來了——它們能夠在這座城市,在這座盡管從鄉野里誕生、成長且扶搖壯大卻似乎對哺育其的泥土有著高尚的叛逆和高傲的脾睨的城市里,為它們的蝌蚪找到哪怕一掬小小的泥洼么?
蛙聲十里出山泉,青草池塘處處蛙,稻花香里蛙聲一片。一提到蛙,一提到蛙聲,似乎總要人想到這些靈動如水的句子。對習慣了以審美的姿態來吟詠這些關于蛙聲的詩詞的人的意識里,蛙聲是暢飲稻香的豐收和安寧,是閑敲棋子的閑適和幽雅,是空谷天籟的寂寥與寧靜。可如同苦難只屬于苦難者自己一樣,美麗也只屬于那些沉浸在美麗遐想里的人們,在這個強對流天氣頻仍的季節,傾聽著天邊的滾滾悶雷,有誰能夠感知得到,放聲歌唱著的蛙,在合奏著屬于它們自己的深深的憤怒和哀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