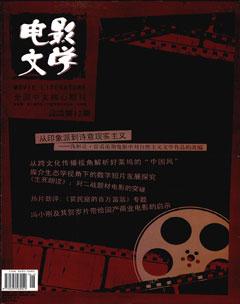從跨文化傳播視角解析好萊塢的“中國風”
蘇宏元 李 騏
摘要本文簡要回顧了美國好萊塢電影塑造中國形象的歷史,總結(jié)了中國觀眾四種不同的反應模式,并以跨文化傳播的視角,從思維方式、價值觀、定型觀念三個層面予以分析和闡釋。本文主張在全球化時代應以開放的姿態(tài)對待好萊塢的“中國風”電影,吸收好萊塢電影生產(chǎn)的有益經(jīng)驗,推動中國電影“走出去”,真正實現(xiàn)強勢的跨文化傳播。
關鍵詞跨文化傳播;好萊塢電影;“中國風”
如果從現(xiàn)存的默片《嬌花濺血》
(Broken Blossoms)(格里菲斯[D.W.Griffith]執(zhí)導,1919年)算起,美國電影塑造華人形象已有九十年的歷史。2008年,《功夫熊貓》《木乃伊3》《黃石的孩子》《功夫之王》四部中國元素電影重磅推出,好萊塢似乎又刮起了一股“中國風”。中國觀眾對此的反應卻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其實,無論是好萊塢電影的創(chuàng)作實踐,還是中國觀眾的觀影體驗,均涉及跨文化傳播的因素,這也正是本文試圖探究分析的焦點。
一、好萊塢電影的“中國風”
好萊塢“中國風”電影的創(chuàng)作并非始于今日。早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默片時代,好萊塢電影就開始刻畫華人形象,不過大多是次要的配角和陪襯。臟亂的唐人街,男人拖曳的長辮,女人長長的指甲,賭博、走私以及幫會之間的爭斗,成為中國形象的典型特征。即使以中國本土為題材的影片,也大多塑造的是一些虛實莫辨的中國軍閥,如:《上海快車》(1932)、《閻將軍的苦茶》(1933)、《將軍死于黎明》(1936)等。這一“傲慢與偏見”的視角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才有所改變。1937年,好萊塢拍攝了首部完全以中國為題材的電影《大地》。這部電影是根據(jù)美國著名作家賽珍珠獲普利策獎的小說改編而成的,故事發(fā)生的時間跨度長達40年,具體展現(xiàn)了一對中國農(nóng)村夫婦的悲劇命運,以及他們對土地的眷戀。為了凸顯“中國色彩”,整部音樂采用了純粹的中國音樂。這部影片在某種程度上“修正”了早期好萊塢電影中被嚴重扭曲的中國人形象。1949年以后,由于中美之間再次出現(xiàn)政治上的對立,好萊塢拍攝了許多反共電影片,以貶抑的立場渲染“赤色恐怖”,如:《北京快車》(1951)、《撤離地獄》(1952)、《水深火熱》(1954)等。上世紀70年代,隨著中美關系逐步正常化,李小龍挾中華傳統(tǒng)武術(shù)進軍好萊塢,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轟動和美國觀眾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熱情。這是中美電影文化交流史上一次小小的變奏。
20世紀70年代以后,由于錄像帶、國內(nèi)電視、有線電視尤其是互聯(lián)網(wǎng)的沖擊,好萊塢電影在美國國內(nèi)市場的收益不斷萎縮,每年僅10%的美國電影可以贏利。好萊塢的應對策略是從國際電影壟斷市場的贏利中進行補貼。據(jù)統(tǒng)計,1952年,美國電影業(yè)從國外市場獲得的收入占它的總收入的42%,而在20世紀70年代這一比例提升到52%至55%。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影片在歐盟電影市場中占到70%左右的份額。2003年以前,中國內(nèi)地電影市場盈利的60%也來自好萊塢大片。好萊塢電影(包括其他美國文化產(chǎn)品)呈現(xiàn)出席卷全球的態(tài)勢,也為文化帝國主義理論下了一個注腳。
電影市場的“全球化導向”促使好萊塢電影在主題、取材以及拍攝方法等電影生產(chǎn)的一系環(huán)節(jié)發(fā)生了變化。他們宣稱“永遠在尋找最好的故事,發(fā)生在哪里并不重要。”1988年,貝納爾多·貝托魯奇導演的偏西方視角但制作精良的傳記電影《末代皇帝》獲得了第60屆奧斯卡九項大獎。1993年,華裔導演王穎根據(jù)美籍華裔小說家譚恩美的暢銷小說改編的電影《喜福會》首次成功地打入好萊塢主流電影市場。以中國為題材的電影盡管不乏爭議,但在票房上頗為成功,且具開發(fā)潛力,自此以后,好萊塢的導演們開始更多更自覺地在作品中融入中國元素。1998年,改編自中國傳統(tǒng)故事的電影《花木蘭》贏得全球票房共計3,04億美元。另外,《非常人販》《上海正午》《上海騎士》《面紗》《駭客帝國》《生死格斗》《007系列》等眾多好萊塢高端概念電影中均加入中國元素,作為賣點在全球市場發(fā)行。據(jù)統(tǒng)計,電影007系列21部中的半數(shù)皆與中國有著或多或少的關聯(lián)。2008年作為中國年,好萊塢又重磅推出了《功夫熊貓》等四部中國元素電影。這些作品或者直接取材于中國傳統(tǒng)文學或民間傳說,或者以中國作為故事發(fā)生的場景,或者運用了大量中國獨有的文化符號,如麻將、二胡、毛筆等等,盡管不乏可看性,但很難說真實地反映中國社會的現(xiàn)實以及生活理想。《功夫熊貓》的制作前后耗時5年,制作成本高達1.3億美元,全球宣傳推廣成本高達1.25億至1.5億美元,席卷全球共計6.3億美元票房。
二、“中國風”電影“四論”
針對好萊塢電影刮起的“中國風”現(xiàn)象,中國各界人士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出現(xiàn)了褒貶不一的反應。概括起來,大致可分為四種論點:
1“誤讀論”
所謂文化誤讀,就是“按照自己的文化傳統(tǒng)、思維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讀另一種文化。”該觀點認為,美國電影里的中國形象是“西方文化對中國的某種摻雜著想象與知識的‘表征,是一種能主動地選擇、表現(xiàn)、生成意義的話語。”因而不可能準確客觀,存在“誤讀”和“誤解”的情況。電影中對中國文化元素的解讀與中國人的理解存在偏差,甚至是相悖的現(xiàn)象。
2“妖魔化論”
“妖魔化”是指通過文化、政治、宣傳、媒體等,在意識形態(tài)上和文化上,把自己化身為先進、正義的象征,而把對方描繪成愚昧、專制。“妖魔化中國”初始只是針對在全球背景下歪曲中國的西方策略的一個批判性研究視角,后來延展為對整個中西關系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全方位審視。持這一立場的學者們認為,好萊塢在歷史上曾以其強烈的種族主義偏見和冷戰(zhàn)政治色彩,扮演過“妖魔化”中國和中國人的急先鋒。如今這種狀況雖已發(fā)生了很大變化,但由于好萊塢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多局限于傳統(tǒng)領域,理解相對膚淺和片面,在電影中描繪的依然是落后、封閉的中國形象,沒有反映出中國社會的變遷和現(xiàn)實。
3“威脅論”
好萊塢有65%的票房收入來自美國以外的地區(qū),而中國市場在其中占據(jù)了相當?shù)姆蓊~。由于“好萊塢大片”的沖擊,中國本士電影的觀眾大量流失,票房收入長期處于低迷狀態(tài)。這種“兵臨城下”的強勢輸入,使中美電影交流形成巨大的“文化逆差”。此外,好萊塢用美國的價值觀念和文化模式來吸收和改造中國元素,把中國題材或元素處理成為好萊塢式的“類型電影”和后現(xiàn)代電影文本。電影對中國元素實行無償?shù)摹澳脕碇髁x”,而在制作成電影之后就開始大談產(chǎn)權(quán)。因此這一派觀點認為,無論從市場或文化交流的角度,這一類好萊塢電影對中國電影業(yè)和文化構(gòu)成了直接或潛在的威脅。
4“樂觀論”
該論點認為好萊塢電影對中國文化元素的創(chuàng)造性運用,不僅有利于中國文化在全球范圍內(nèi)的廣泛傳播,同時其成功的經(jīng)驗也對中國本土電影如何開采自身的文化資源提供
了啟示。李小龍的影片讓中國功夫走向世界,《功夫熊貓》使得國寶熊貓憨態(tài)可掬的可愛形象傳遍全球,而借鑒好萊塢模式拍攝的電影《英雄》《十面埋伏》《臥虎藏龍》等也都賺足了票房。
三、跨文化傳播視角的解讀
中國觀眾對好萊塢“中國風”電影做出的反應,折射出復雜的歷史和社會原因。中美兩國之間深刻的文化差異是其中的關鍵因素之一。根據(jù)跨文化傳播的觀點,在文化的生產(chǎn)、傳播或者理解、接受過程中,參與者均透過自身文化的棱鏡去審視“他者文化”,并運用自身文化所固有的方式去編碼和解碼。觀眾觀看電影的過程,即是參與電影意義建構(gòu)的過程,必然與觀眾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以及所處的文化背景息息相關。
1思維方式的差異
思維方式因人而異,因文化而異。其實,思維方式即是一個民族的文化內(nèi)核。“每個民族都有自己整體的思維偏向,從而形成自己特有的思維類型”,也因而形成了不同風貌特征的民族文化形態(tài)。
在跨文化傳播過程中,思維方式的差異直接影響傳播者與接受者對文化信息的理解和闡釋。因為由一種思維方式組織起來的文化信息或文本,接受者則以另一種思維方式去破譯或“重構(gòu)”,很難避免歧義的產(chǎn)生乃至誤讀。
中美(西方)在思維方式上的差異主要體現(xiàn)在如下三個方面:
(1)中國人偏好形象思維,美國人偏好抽象思維或邏輯思維。中國導演非常注重營造意境,重視色彩影調(diào)的運用,追求視覺畫面的完美。電影《英雄》中全身紅裝黑發(fā)的飛雪與如月決斗時,形成紅、黑、藍、黃四色交相輝映的色調(diào),完美奢華至極。而美國的科幻電影,故事可以發(fā)生在任何時代,卻非常講究情節(jié)邏輯的嚴密性。如《駭客帝國》展示了一個與人的眼睛所看到的現(xiàn)實截然不同的世界,電影情節(jié)環(huán)環(huán)相扣,讓我們不得不感慨西方導演縝密的邏輯思維。
(2)中國人擅長“整體”和“綜合”,美國人推崇“具體”和“分析”。這表現(xiàn)在中國人慣于把個人、自然和社會作為統(tǒng)一體來考察,強調(diào)事物的整體性和有機聯(lián)系,而美國人(包括其他西方民族)卻長于分門別類地比較、歸納和具體分析。
(3)中國人注重“統(tǒng)一”,美國人注重“對立”。美國式思維強調(diào)差別和對立,傾向于“一切之兩分”的切割式認識方法,清楚地區(qū)分好與壞、和平與戰(zhàn)爭、對與錯、成功與失敗等這樣一些相對的范疇,滋生出的是一種基于二元對立思維的“沖突文化”。電影007系列中正是邦德的一個個敵人成就了邦德持續(xù)四十多年的英雄形象;而追求“和諧”則體現(xiàn)了中國人的生命智慧,是中國傳統(tǒng)人文精神的精髓。電影《臥虎藏龍》不僅講述了古老中國的武俠傳奇和江湖情懷,同時也傳達出了中國人的禮義精神和道家“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此外,好萊塢電影工業(yè)追求電影的娛樂性,總是采用直觀、幽默的方式敘述故事,追求較為表面化的戲劇性效果,同時以獵奇的眼光看待異質(zhì)文化,相對忽略其復雜的內(nèi)涵;而中國文化承接著“文以載道”的傳統(tǒng),觀眾習慣于以嚴肅認真的態(tài)度去“審讀”電影,對藝術(shù)文本“本能地”具有意識形態(tài)的反應敏感性。例如,在電影《木乃伊3》中,由李連杰飾演的反面一號“秋王”完全照搬的是從一統(tǒng)天下到修筑長城直至尋求長生不老的秦始皇的故事。然而影片中此人名為“秋王”,并以怪誕的形象出現(xiàn):時而被稱為“討厭的木乃伊”,時而變成了會飛的三頭蜥蜴。中國人對秦始皇這個專制統(tǒng)治者的評價和感情是復雜的,他畢竟締造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tǒng)一的王國。因而中國觀眾很難接受電影《木乃伊3》所塑造的“秋王”形象。
2價值觀的差異
美國學者羅基切(M,Rokeach)認為,價值觀是人們關于什么是最好行為的一套持久信念,或是依重要性程度而排列的一種信念體系。不同的世界觀、人生觀對人類生存的價值和意義看法不同,形成了衡量“真、善、美”的不同價值標準。價值觀的差異是影響跨文化傳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巨大差異甚至會影響到跨文化傳播的正常進行。
好萊塢電影是以國際市場為目標的,因而力求傳達能被全世界都理解和接受的所謂共通人性和普世價值觀,并予以肯定。然而,作為精神產(chǎn)品和文化載體,好萊塢電影不免打上美國價值觀的烙印,體現(xiàn)其獨特的文化內(nèi)涵。
荷蘭心理學家霍夫斯特德(G,Hofstede)歸納出比較不同文化價值觀的四個維度,分別是個人主義一集體主義、權(quán)利距離、不確定性規(guī)避、男性化一女性化。后來,他又增加了另一個維度,即長期導向與短期導向。這些不同維度的文化價值觀可以影響到文化傳播和交流的每個環(huán)節(jié)。在電影制作過程中,好萊塢是按照美國的價值觀來對中國故事進行選擇性的改寫,強調(diào)的是美國所肯定的價值取向;而中國觀眾在電影觀看的過程中,是按照中國的價值觀進行理解。經(jīng)過選擇性改寫和選擇性理解這兩個階段,文化“原型”、文化生產(chǎn)和傳播以及文化接受之間出現(xiàn)了巨大差異。例如,美國的個人主義文化強調(diào)自我和個人的成就,在好萊塢電影中突出自我價值的實現(xiàn);而作為集體主義文化的中國更強調(diào)和諧,推崇犧牲“小我”成就“大我”。花木蘭替父從軍的故事在電影中演變成花木蘭一心追求自我成就的女英雄形象,體現(xiàn)了女權(quán)主義的精神,這就完全顛覆了中國觀眾認為其孝順父親報效國家的傳統(tǒng)理念。于是,對中國文化的“誤讀論”自然就有了立論的基礎。
與價值觀念相關的社會行為規(guī)范的差異也是影響跨文化傳播效果的重要原因。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贍養(yǎng)老人是基本的道德行為,而在美國文化中這種觀念就相對淡薄。李安早期電影《推手》表現(xiàn)的就是中國的“孝道”與美國“個人主義”之間的矛盾:朱老先生感覺被排除在家人之外。而美國媳婦瑪莎因為老人對她的影響讓她無法靜下心來寫書就一直想把老人趕出去。在美國,父與子是平等的,而中國受儒家思想影響,注重孝道,因而父子之間是一種“等級”關系。在《功夫熊貓》中,阿寶的父親居然是一只鴨子,這讓中國觀眾覺得匪夷所思,甚至認為這有辱國寶熊貓的形象。
3定型觀念
定型觀念又可譯為“刻板印象”或“刻板成見”,是由美國著名專欄作李普曼提出的,指的是人們對特定事物的固定化、簡單化的認知和判斷。這一思維方式使人們對事物的認識簡單片面,乃至引向偏見、歧視,且經(jīng)常伴隨著價值評價和好惡的感情。刻板成見對跨文化傳播具有消極影響,甚至阻礙跨文化傳播行為的發(fā)生或者產(chǎn)生歧視觀念。西方社會對中國的定型觀念(無論是歧視性的偏見或浪漫化的想象)一直是中西方跨文化傳播中的一大障礙,直至今日還不能完全消除。譬如,在好萊塢電影中,華人往往飾演反面的或“丑陋”的角色,反映的也主要是中國社會愚昧、落后或腐朽的狀況,并不是客觀真實的中國形象。這即是“妖魔化論”出現(xiàn)的緣由。
在西方,定型化的中國形象白有其源頭,早期耶穌會傳教士的片段記錄以及旅行家的游記,如利瑪竇的中國札記、馬可·波羅的游記等等,為西方人了解中國提供了最初的素材;其次,由于信息傳播的失衡,美國人對現(xiàn)當代中國的真實情形了解有限,許多涉及中國題材的小說或電影只是對中國社會的想象性描述。而早期移民去美國的華工也因?qū)γ绹?jīng)濟和就業(yè)問題帶來的沖擊以及部分移民自身的“不端”行為造成了美國社會對華人的負面評價,乃至于“蔑視”。
毫無疑問,對中國形象定型化的印象和評判或多或少決定了好萊塢電影對中國的定型化敘述。如早期的傅滿洲、陳查禮,也包括電影大師格里菲斯最后一部杰作《殘花淚》中的溫柔多情的中國男人,即可視為定型化的中國人形象的代表。而在《蜘蛛俠2》(2004年)中,蜘蛛俠以自己凡人的身體沖進著火的民房,救出一名中國籍小女孩。當他把小女孩送到她父母面前時,才發(fā)現(xiàn)這個中國家庭衣著寒酸,儼然一副現(xiàn)代版中國勞工的形象。
由于巨大的文化差異,好萊塢的“中國風”電影體現(xiàn)了美國人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以及定型觀念,但好萊塢電影在全球大眾文化市場上暢銷不衰,也說明人類文化的共通性和普適性。前者在一定程度上構(gòu)成了跨文化傳播的障礙,后者是跨文化傳播的必要條件。這是跨文化傳播活動的復雜性之所在。不過,在全球化日趨深入的今天,固守“意識形態(tài)”的視點或者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結(jié)并不利于文化事業(yè)的發(fā)展。中國電影要真正“走出去”,實現(xiàn)強勢的跨文化傳播,應在電影生產(chǎn)的“編碼”過程中,發(fā)掘既具本土性又可以為全世界所理解的那些“文化資本”;同時應以寬廣開放的心胸包容異質(zhì)文化,兼收并蓄,提升吸納其他民族文化的能力。這大概是好萊塢的“中國風”電影給予我們的重要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