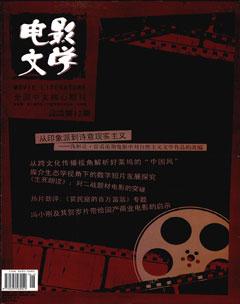影視與大眾文化
趙麗娜 董麗娟
文化的概念本身就是抽象的,經過不同的推演有時甚至是分割,而今變得繁雜而多樣。在社會領域中,文化顯示著包括知識、道德、物質、價值體系、生活方式在內的某種文明的諸方面的總和。因此,文化便處于各種觀念沖突的核心,人類長時間的探索就好像游離在幾個分割的世界中,隨著人類的進步和交流、傳遞、播送和復制等手段的驚人發展,他們才會聚到一起,彼此密切起來。
大眾文化是共享文化的一種形式,今天的文化是在各種各樣的大量會晤中,在露天的大型演出中,在電影和電視的屏幕上,供大家分享的。“大眾文化”的名稱并不確切,但不失為一個常用的、方便的用語,“大眾”就其成分來說,是一個游移不定的概念,可事實上,面向大眾的文化為了意識形態或商業的目的卻極力“操縱”大眾,討好大眾,迎合大眾的欲望。
影視是視聽藝術,視聽語言能復現對象的直觀形態,電影理論家巴拉茲曾經說過:“如果我們自己不是內行的電影鑒賞家,那么這種具有最大思想影響力的現代藝術就會像某種不可抗拒的莫名的自然力量似的任意擺布我們,我們必須細致地研究電影藝術的規律和它的可能性,否則我們就不可能去掌握和支配人類文化歷史上這一最能影響群眾的工具。”
影視作為現代大眾文化的一種“形態”,在當今社會,更突出了它的商品意識形態性和市場性。
第81屆奧斯卡頒獎典禮在美國洛杉磯落下帷幕,《貧民富翁》囊括了最佳影片、最佳改編劇本、最佳電影剪輯、最佳原創歌曲、最佳原創音樂、最佳音效合成、最佳攝影、最佳導演8個獎項。導演丹尼·保爾(Danny Boyle)設計影片時,一開始就采用了“意識流”強有力的切換技法,主人公馬里克·賈馬爾從再過一道題就能拿到巨額獎金的風光臺上,被一個耳光扇到了審訊室里,又被審訊室中的一拳打回到熱鬧非凡的競猜現場,情景頻繁地切換,被動地享有雷鳴般的祝賀掌聲和審訊室中的被動挨打,同樣表現了主人公這個弱小的個體對強勢的漠視、無奈和堅忍,這正是一種真實的生活,也是影片博來眾多“眼球”的重要緣由。
兩種情景切換的巨大反差和碰撞讓主人公產生想要逃脫這種境遇的欲望,引發了主人公對童年時代的追憶,孩子們狂野不羈的奔跑,連續變化的“幻象”,是對現實生活的抽象和再現。追憶中說唱式的音樂伴奏是一種現代氣息的體現,富于節奏變換和流動感。同時,喧嘩的人聲夾雜著車的汽笛聲,把平淡的生活烘托得具有強烈的立體感。
以往感覺印度影片表現的是一種風情,通常以富有印度民族特色的歌舞和地域風情見長,而這部《貧民富翁》更多表現的是一種意志,是一種平民化的“意識風骨崛起”,競猜現場觀眾看到的只能是人物反應的表面,并不能體會賈馬爾參加競猜活動的真正用意是尋找他“錯失”的女友拉媞卡——他生命中的最愛,體會不到他的那種“醉翁之意不在酒”,賈馬爾答題時的從容和答對題后的鎮定反應引起了人們的猜測。于是,他被警官帶到了審訊室,受到了黑暗的、不公平的甚至稱得上是狂虐的對待,審訊、拷打、電擊……
“蒙太奇”手法的運用不僅在影片開頭就調動了觀眾的思維,更是貫穿于影片的始末,將競猜題目和主人公賈馬爾的成長經歷對應起來,記憶也隨之被串聯,警察在分析、盤問他的競猜過程的同時,賈馬爾生活的點點滴滴也都呈現在面前,生活原來就是這樣的“巧合”。被問及1973年因《贊吉爾》一炮走紅的是誰,使他想起了自己為得到阿米特巴的簽名而“義無反顧”地跳進糞坑,這是一種超乎常規的舉動,難能可貴的品質——信念與執著第一次在主人公賈馬爾身上體現出來,第二道題問道“印度國徽上有三只獅子,獅子下方寫的是什么”時,他回答不出來,他選擇了求助現場觀眾,當審訊他的警官問道:“這么簡單的問題連我九歲的女兒都答得出,你卻答不出,”“你是在欲擒故縱嗎?”賈馬爾沒有針鋒相對地反擊,而是選擇了請對方回答日常生活中最簡單的問題——“喬巴迪一份水果布丁多少錢?”“上周四是誰在圣特克魯斯車站外值班?”結果是對方不知道或答錯,很自然地就將對方的鋒芒反射了回去,由于人們生活的圈子不同,對事物的留意程度不同,不知道一些他人認為是很簡單的問題的答案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不必要并且必定是無果的爭論避免了,這是弱勢者解決問題的方式,更是一種平淡生活中積累的處事哲學。
被問到“喇嘛神”因右手拿著什么而著稱時,賈馬爾的意識又被帶回到童年那苦澀的記憶中,宗教紛爭與迫害,他童年腦海中的黑色印記被重新揭開,親眼目睹一片宗教毆斗和混戰,母親倒在了突如其來的木棍之下,這是一種對人性的殘忍侵害。“每天早上醒來他都會‘想起這個答案”,這種侵害已經融入他的每根神經,時時發作,令他痛苦不已。
影片中的一號男配角——他的哥哥沙里姆,在不同的年齡段都表現出了他那個年齡少有的成熟和干練,理性的光芒和思維閃耀在他的身上,他渾身洋溢著實用主義,比如他因價錢好而賣掉了賈馬爾用不堪的“身體遭遇”換來的阿米特巴的簽名;在宗教紛爭中,他和賈馬爾一樣,失去了父母,“漏屋又遭連夜雨”,他們流離失所之時,寄居木棚,考慮到怕招來保安,他指著拉媞卡對賈馬爾說的那句“我現在是家長了,我不允許她進來”,足以看出他的家長“做派”,當賈馬爾偷偷叫拉隄卡進陋棚避雨時,沙里姆佯裝睡去,這種處事方式幫助他顯示了權威,我們透過表象看到,那實際是一種對家庭責任的擔當,一種偉大的深沉。逃離“黑幫”時他沒有拉住拉娌卡的手,當賈馬爾拼命想沖回去救拉媞卡時,他用了最理性的話攔住了弟弟:“你要回去讓他們挖你的眼睛而替他們多賺錢嗎?”最真實的現實,最樸質的話語,把他作為兄長的成熟形象勾勒了出來。同時,他又有著“監工”的嘴臉,盡管是被生活所迫,幼稚地被人利用,“無奈”是他這樣做的深層原因,但當自己弟弟的生命受到威脅時,他機智地幫助,一起擺脫被奴役的境地,他的親情觀念遠遠超出了他對物質的追求。
兄弟倆逃出“黑幫”后在火車上那暫時忘記憂傷的片刻令人仰羨,他們盡情歡樂的歌唱,猶如要在大自然的天籟中尋找清明優美的思想根源。現代社會中,這是忙碌和喧囂中的人們所崇尚的樂園,那種拋開一切瑣事和雜念的“調節”意識在這里得到了慰藉。
后來,兄弟倆以在火車上賣些小商品謀生,也趁機偷取客人的一些食物,有一次險些被抓,他們被驅趕,掉下了,火車。掉下的瞬間,兄弟倆在漫天飛舞的黃土中滾落,就像滾動在塵世中的兩粒灰塵,渺小而悲涼。透過層層塵埃,他們被眼前天堂般的景象驚呆了,他們住了下來,偶然的一次,兩位游客的主動詢問,為賈馬爾提供了一條生存之道——導游服務,他機敏聰慧,能夠將游客對他講解內容的質疑“自圓其說”;而沙里姆此時則正與街頭混混趁機偷取游客的物品,之后愈演愈烈,他們偷走游客汽車里所有能夠偷走的物品和配件。當賈馬爾遭到警察拳腳相加時,善良的游客及時解圍,并拿出錢來對他予以酬謝,我們看到,世界上并不全是暴力,更有著對弱者的憐憫與幫
助,這正是影片所展現的深層次的東西。兄弟倆并不是一開始就想做這種骯臟的勾當,他們也想以正當職業為生,可殘酷的社會現實不允許他們做到。
賈馬爾在生活的苦難中,有著他的堅實的精神支柱和富足的精神家園,那就是他愛戀的拉媞卡,他們的戀情中早已融入了親情,這使他在面對困難和挫折時表現出了堅韌,他返回孟買苦苦找尋昔日戀人,他“歡欣鼓舞”地找尋,不知疲倦,那是一種滿懷著希望憧憬美好生活的意志在激勵著他,那是一種不懈和必勝的信念。
親情一直是影片中的一條主線,當宗教暴徒襲來時,當“黑幫”在后追趕時,當看到屏幕上成為世人焦點的弟弟在憂傷等待戀人時,沙里姆都選擇了盡自己最大能力幫弟弟賈馬爾,甚至不惜失去自己的生命。這是一種別樣的“美”,是穿透世間萬物的大愛。
最后一個問題問及“三個火槍手是誰”,讓他想起了最初因逃學而錯過學習“三個火槍手”,賈馬爾心態平和。此時他像達到了那種“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他想上帝跟他開了個“不大不小”的玩笑,無奈下他選擇使用“電話求助”,他將電話打給了他的兄長,命運的天平又一次傾向了他,接電話的卻是逃出“黑幫”的拉媞卡——他苦苦尋找的戀人!這時,任何其他事物對她來說都是無足輕重的,他來參加競猜的目的達到了!
美作為人的本質力量的感性顯現,美感也是結合著目的性的實現所引起的精神滿足,大眾傳播媒介十分重視從情緒到官能感受的作用。早在18世紀,易受感動的心靈就已發出驚嘆,浪漫主義的來臨不僅使文學擺脫了從前的冷漠,也激發了人們所潛藏的一切:追求故事的興趣,消遣的需要,當然還少不了潛在的愛情,影片的結尾是賈馬爾和拉媞卡的大團圓結局,使人身心愉悅,體現的是一種性靈的升華,文化超越于享有,它是作為參與人類事務的追求,作為分享才能、知識與希望來理解的。
社會變革深入,文化格局的多元化,使舊的價值觀念凌亂成精神的碎片,新的價值選擇處于迷茫的狀態。實際上,每個時代的藝術,都是這個時代人們物化了的心靈。美感的直覺如果只停留在感性認識的范疇內而排除理智與思考的作用,那么這種美感必然是膚淺的、片面的、有限的。影片中我們看到它有冷酷如鐵的現實,也有春天般暖亮和溫柔的詩意理想。
日本著名電影導演黑澤明曾經說過,一部影片如果沒有一種叫做“電影美感的東西”,是不會感動人的,畫面構圖的形式美感、色彩的變化往往給我們最直接的視覺刺激。影片中主人公從小生活的貧民窟與瑰麗的泰姬陵、強勢群體和這群小人物的反差恰恰做到了這一點。
《貧民富翁》的現代文化精神體現的是一種西方式的實存性與東方的傳統精神的融合,德西迪里厄斯·奧班恩在《藝術的涵義》中寫到“藝術中不能被解釋或甚至不能完全描述的東西,就是作品的精神價值。”
《貧民富翁》中大型競猜欄目“你想成為百萬富翁嗎”所安排的競猜題目,反映的正是興趣、日常簡單而平靜的生活、宗教、對未來的追求,體現出的個體生命因素,如血源、種族、性別、意志權利等,在影片中得到了完美的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