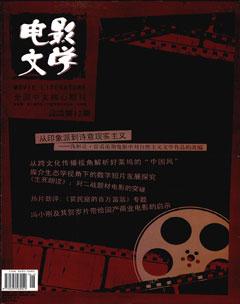《喧嘩與騷動》的人物悲劇與創作思想解讀
周文娟
[摘要]《喧嘩與騷動》中主要人物的悲劇原因無疑是由于他們缺失了對自己人生價值的判斷。福克納向往著尊重人性的理想境界,因此,他的作品展現了現代人在喪失傳統道德之后的焦慮與失落,有力地揭露與批判了美國南方社會壓迫人性的罪惡,無情地批駁了新興資本主義的極端自私的價值觀念,表現了作者的人道主義創作思想。
[關鍵詞]《喧嘩與騷動》;創作思想;人物悲劇
一、解讀《喧嘩與騷動》的人物悲劇
福克納曾說:“今天世界上的各種力量竭力以人們的恐懼來剝奪他們的個性、他們的靈魂,竭力把他們變成沒有思想的人。”些沒有了個性、沒有了靈魂、沒有了思想的人,自然不再是正常意義上的人。從這個角度我們不難理解,福克納筆下為什么刻畫了那么多人格不正常的典型人物。
1凱蒂
凱蒂是福克納筆下美國舊南方婦道觀的犧牲品,婚前失貞鑄就了凱蒂的人生悲劇,是一個最為典型的被異化的人物,具有十分明顯的象征意義。《喧嘩與騷動》中福克納首先為我們塑造了一位漂亮、熱情、富于同情心的、人性美好的化身,她對人,尤其是對弱者充滿了理解、同情、關懷與愛,與她母親康普森夫人的自私冷漠相反,凱蒂總是熱心地照顧班吉,常常不惜違抗母命堅持愛護班吉,為了哄班吉高興,她不顧母親的反對,把自己心愛的坐墊拿來讓班吉玩;甚至當杰生惡作劇剪破班吉的紙玩具時,凱蒂不顧一切地與杰生廝打了起來。最后當她要結婚離家時,她要昆丁發誓一定好好照顧班吉。小說為我們塑造了這樣一位愛與美的化身——人性美好的象征。然后又描述她的不幸失貞,進一步讓我們看到她在社會的逼迫下墮落,由此給讀者造成了極大的心理跌宕,這正是福克納的高超之處。
美國舊南方清教婦道觀從精神上奴役婦女成為被動接受男人泄欲和傳宗接代的工具。凱蒂試圖反抗而違反了“南方淑女”的規約,因此她再也無法正常地生活,注定無路可走。美麗而善良的凱蒂多次被遺棄,她的丈夫們無法忍受由于她的過錯而蒙受的社會羞辱,這就是凱蒂人性異化甘愿墮落的直接原因。凱蒂從一個古老世家的閨秀到占領軍將軍的情婦,其中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簡單生活過程,那是一種極為復雜的心理歷程;它體現的是凱蒂對于生活與人生的絕望,是對于傳統的反叛和與命運抗爭失敗之后的無可奈何。小說中,福克納使用班吉上帝般超自然力和昆丁的善良與理性來挽救凱蒂,但他們的一切努力都付諸東流、福克納以此告誡讀者,在摧殘人性的加爾文清教主義的淫威之下,無論是天上的上帝,還是人間的理性與善良,都無法為凱蒂找到一條避免墮落、得到幸福的生活道路。
福克納著意塑造了這樣一個典型人物,盡管他并沒有在小說中直接露面只存在于與其他人的關系之中,但凱蒂的故事卻成為整部作品的主線。
2班吉
班吉是被福克納蓄意安排在小說之中,用于嘲弄與諷刺基督教虛偽的說善教義。福克納借班吉這樣一個蓄意安排的白癡角色,在小說中渲染了康普森家濃烈的頹敗氣氛,如果沒有這樣一個白癡角色貫穿在小說之中,無疑將使《喧嘩與騷動》大大遜色;此外,福克納又以班吉反襯了其他人物,因為白癡是不可能給任何人回報的,因此,對白癡的態度就像一面鏡子客觀地反襯了小說中所有人物的丑美善惡,福克納也因此用班吉襯托出了杰生的丑陋與凱蒂的善良。
為了強化對基督教的嘲諷效果,小說中班吉故事的時間背景是班吉的33歲生日,而耶穌正是33歲時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這里的影射性顯而易見。這個影射著上帝的班吉竟是一個白癡,甚至不會說話,只能“毫無意義”地“喧嘩”。為此,福克納賦予了他筆下的班吉有著耶穌般的超意識力,竭力想阻止凱蒂的墮落。然而這種耶穌般的超自然力并不能拯救凱蒂于走投無路的逆境之中,凱蒂還是墮落了。這里影射的含義是十分直白的:耶穌竟像白癡一樣的無奈,只會“毫無意義”的“喧嘩”。
通過班吉對世事癡迷的意識流表述,我們不難從中體會到福克納是通過這個雜亂的癡人故事,有意識地傳達了他意欲傳達于讀者的全部感受:康普森家庭頹敗的氣氛、人物與環境。作品影射對主題的深化作用也是十分明顯的:福克納借助“耶穌”的無奈,來揭示南方舊傳統體制的沒落是無可挽回的,即使是上帝的超自然力也無能為力。如果不用影射上帝作為襯托,這一主題遠不會揭示的這樣深刻。
3昆丁
昆丁是沒落的康普森家族和南方舊時代的象征。昆丁的悲劇在與他的個性敏感卻又非常孱弱,他的意識又背負了太多的傳統而難以應對生活的現實。
昆丁眷戀自己的家人尤其是深愛著妹妹凱蒂。他之所以將凱蒂的失身歸咎于自己,并不是他真的亂倫,也根本不可能那樣做;只是由于長老會萬劫不復的天譴說教深深地糾纏著他的意識,使他以為只要人們認為他們兄妹亂倫,不用麻煩上帝,他就可以把妹妹和自己打人地獄,從而使康普森家族得到解脫。并且,在那里他就可以永遠監護著她,讓她在永恒的烈火中保持白璧無瑕。這里體現的是他對南方舊道德觀念的忠實守護,那個造就了他卻已經不復存在的舊南方傳統夢魘牢牢地控制了他,他沒有辦法走出傳統夢魘的陰影,因此,昆丁的死是一種注定的宿命。也正是這種宿命感使得昆丁世界中的一切不再具有當下的現實意義,他失去了對于現在的認知能力。昆丁的精神情感中有著太多的理性,而缺乏生命的活力,他對妹妹凱蒂的愛也是抽象與蒼白的和他的生命無關,僅僅是傳統價值觀念和家族榮譽的需要。所以,凱蒂的墮落使他感覺到自己挽救康普森家族的一切努力都是無濟于事,感到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滅頂之災。因此,他的死亡是自身價值觀念的幻滅,是一種思慮已久、從容不迫的病態期待。是凱蒂的命運使他徹底失去了最后的心理支撐,可見,他的自殺有著深刻的社會根源和心理根源,昆丁是福克納所創造的舊社會走向終結的象征。
4杰生
稍加品味,我們不難看出杰生這個《喧嘩與騷動》中的惡人,其鮮明與飽滿的程度不亞于莎翁筆下的經典惡人埃古和麥克白夫人。杰生和“斯諾普斯”三部曲中的弗萊姆·斯諾普斯一樣,是被“新南方”資本主義異化的產物。如果說通過對康普森家其他人的描寫,福克納表達了他對南方舊制度的絕望。那么,通過對杰生的漫畫式的刻畫,福克納鮮明地表示了他對資本主義“新秩序”的厭憎。福克納說過,“對我來說,杰生純粹是惡的代表。依我看,從我的想象里產生出來的形象里,他是最最邪惡的一個。””
在福克納的筆下,杰生成為一個沒有理性、不切實際,對生活現實充滿了仇恨與絕望的報復狂。福克納通過杰生這一典型人物形象揭露了人性中的丑陋罪惡,反映了現代資本主義物質屬性的殘忍與貪婪。在這個意義上,埃德蒙·沃爾普對《喧嘩與騷動》得出這樣的結論:“這一部分代表現代人,過著充滿喧囂和憤怒而又毫無意義的生活。”福克納通過小說精彩的細節描寫,表明人賴以生存的精神價值遭到瓦解的惡果,把美國舊南方社會轉型時期
人性扭曲的貪婪無恥刻畫的令人憎厭,揭示了現代南方乃至整個人類社會中異化人性的丑惡現象。
5迪爾西
迪爾西這個人物是福克納作為異化人性的對照寫進小說中的,其意無疑是出于對復活美好人性的呼喚。福克納將迪爾西與杰生相對立來體現他的積極思想:“迪爾西是我自己最喜愛的人物之一,因為她勇敢、大膽、豪爽、溫存、誠實。她比我自己勇敢得多,也豪爽得多。”同情心永不枯竭似的從她身上涌流出來;她不畏懼杰生的仇視與世俗觀念的歧視,雖然地位卑微卻勇敢地保護著弱者。迪爾西這個形象體現了福克納“人性的復活”的理想,也正是小說主題的健康性所在:福克納沒有因為人性的異化而喪失信心,說明他揭示人性的異化正是為了呼喚“人性的復活”。因此,這一章把迪爾西作為主人公安排在復活節絕非偶然。迪爾西是小說中惟一能夠理解基督之愛的人物,并且通過她在康家的行為對這種愛做出了反饋和回應。福克納以善良的迪爾西向我們宣示了人性復活的希望。
二、解讀《喧嘩與騷動》的創作思想
眷顧西方歷史不難發現,基督教思想是西方社會歷史進程中一種主導人們精神生活的文化因素,這種影響作用在美國表現得尤為突出,隨處可見宗教思想對其社會生活的滲透與體現。因此,福克納的文學創作也毫不例外地根源于基督教文化,尤其是舊南方社會的嚴酷社會現實,使他別無選擇地關注于加爾文清教的社會作用。
人性的異化,歸根到底是人生存價值的異化。《喧嘩與騷動》中主要人物的悲劇原因正是由于他們缺失了對自己人生價值的判斷。而摧毀這種對自身生存意義的認識能力的罪魁禍首,正是南方的基督教清教主義。福克納以他敏銳的目光和深刻的認識,超越了自己的情感,從而使他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南方社會的腐朽,旗幟鮮明地批判了摧殘與異化人性的加爾文清教主義,表現了他的人道主義立場。同時,他通過對南方種植園經濟制度解體的描寫,也無情地批判了新興資本主義無比貪婪的價值觀念。他的作品在更大意義上展現的是現代人在喪失傳統道德之后的焦慮與失落。
福克納生活在美國舊南方,舊南方傳統社會文化和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多角度的影響,造就了他紛繁復雜的人道主義思想基礎。盡管他的人道主義思想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響,他的作品彌漫著濃重的基督教文化色彩。但是,這并不影響他對異化人性的罪惡進行無情的揭露與批判,因為他所信奉的人道主義更多的是他對人存在價值的基本思考。福克納的偉大貢獻正是在于,他竟然從基督教人道主義的角度,無情地揭露與批判了基督教加爾文請教異化人性的罪惡行徑。毫無疑問,正是由于他的基督教人道主義立場,使他對被宗教異化的人性有著更為深刻的認識,才使得他對造成這種異化的壓迫揭露與批判顯得如此有力。
新舊交替的時代造就了杰出作家多元而深刻的思想,這不僅因為他們常常處于多角度的視野來觀察世界與生活,更重要的是這些作家往往生活在新舊事物異常激烈對立、沖突和交替的復雜社會環境之中,這種歷史變革時期的復雜環境,成就了他們藝術的成長。威廉·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正是這一時期的經典之作,福克納正是這樣一類偉大的作家。
福克納生活在美國南方時代轉折、社會轉型的時空之中。當時,舊意識形態的解體和經濟落后的現實,使依賴于傳統價值觀念生活的南方人幾乎在一夜之間失去了精神支柱,深陷于前所未有的現實與精神的雙重危機之中,對社會前途、生活意義和人身價值思慮無著的焦慮與迷茫。可以說,價值觀念的缺失使當時美國南方陷入了比南北戰爭更為嚴重的危機之中。《喧嘩與騷動》正是誕生在這樣一個充滿了新舊觀念激烈沖突的時代,這種歷史變革時期的復雜環境,成就了威廉·福克納著意創作異化人性悲劇故事的文學創作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