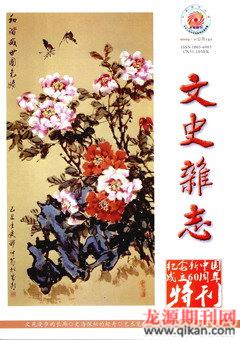新中國60年巴蜀舞臺藝術回眸
李祥林
時光荏苒,新中國成立60周年紀念的日子來臨。此時此刻,回首半個多世紀來四川舞臺藝術事業走過的歷程(1997年重慶市直轄,行政區劃上不再屬四川,本文涉及重慶方面的內容乃此時之前的),可談論的內容多多。下面,就扼要述說二三,以供讀者窺豹。
一、往事閃回舞臺擷英
話劇之于中國是舶來品。1907年,川人曾孝谷與李叔同、歐陽予倩等成立“春柳社”,拉開了中國話劇的帷幕。抗日戰爭時期,上海等地大批進步的電影、戲劇演員、導演等人川組團并演出,尤其在重慶、成都等地留下有聲有色的史跡。新中國建立,四川話劇發展迅速。歷年來,四川人民藝術劇院、成都話劇團、重慶話劇團、成都軍區戰旗話劇團等長期活躍在巴蜀舞臺上,創作和演出了大量劇目,題材涉及古今中外,如《趙錢孫李》、《月琴與小老虎》、《九龍灘》、《錢皇后的酸甜苦辣》、《孔雀膽》、《第一計》、《朋友之間》、《柜臺內外》、《魔屋》、《野妹子》、《母女風流》、《結伴同行》、《扎西娜姆廢墟》、《辛亥潮》、《哦,沙漠美人》、《空港故事》、《船過三峽》、《廣廈為秋風所破歌》、《我在天堂等你》,等等。曾被譽為“西南話老大”的重慶話劇團,半個世紀來先后上演了《四十年的愿望》、《虎穴英華》、《霧重慶》、《轉折》、《一雙繡花鞋》、《沙洲坪》、《時代先鋒》等150多個劇目。在成都,根據李劫人同名小說改編的方言話劇《死水微瀾》,1990年亮相后被譽為“四川的《茶館》”,相繼獲得中宣部首屆“五個一工程獎”、文化部“文化大獎”等,并先后赴英國、日本演出。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發生后,有及時反映抗震救災的話劇《堅守》在蓉推出并巡演各地。此外,省級重點劇目評審及打造是目前在宣傳、文化主管部門領導下正積極、有效推進的工作,全省戲劇小品比賽在有關單位主持下已舉辦十多屆。這不僅聯絡了基層各地專業和業余的作者,而且推出了一批又一批新創作品。這些作品,立足當代,來自生活,其中不乏佳作,值得肯定。
戲曲方面,巴蜀地區有川劇也有京劇。川劇是在明清以來移民潮影響下形成的地方藝術。沐浴著新社會的陽光,這地方藝術煥發出新的活力。1952年10月,首屆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大會在北京舉行,各路戲曲英才匯聚首都,亮技藝展風采。23個劇種,37個劇團,1600多人,在懷仁堂頒獎,有政務院總理到場,那氣派那規格,讓剛剛從“戲子”翻身做主的梨園藝人們無不刻骨銘心。來自長江上游的川劇藝術邁出夔門,亮相在全國同行面前,帶去了《柳蔭記》、《翠香記》以及《五臺會兄》、《評雪辨蹤》、《胡璉鬧釵》、《會緣橋》、《秋江》、《踏傘》、《議劍》等戲。出色的劇目,優秀的演員,漂亮的技藝,讓觀眾看得醉了,掌聲、喝彩如潮水般涌來。賈培之、張德成、周慕蓮、陽友鶴、陳書舫、周裕樣、曾榮華、周企何、袁玉堃、許倩云等藝人手捧獎狀,返回四川。隨著新中國成立初期的體制轉換,展開了對傳統劇目的鑒定和整理。經搜集統計的傳統劇目有近2000個,收入60年代初編印的《川劇傳統劇目目錄》中的即有1500多個。經過整理改編,在四川舞臺上陸續推出了《柳蔭記》、《玉簪記》、《焚香記》、《繡襦記》、《和親記》、《御河橋》、《白蛇傳》、《拉郎配》、《喬老爺奇遇》等大戲,兼及《思凡》、《拷紅》、《放裴》、《歸舟》、《裁衣》、《射雕》、《殺狗》、《做文章》、《迎賢店》、《柜中緣》、《八陣圖》、《別宮出征》、《酒樓曬衣》、《活捉三郎》、《打餅調叔》、《皮金滾燈》等膾炙人口的折戲。如今,四川人選國家舞臺藝術精品工程的劇目有《變臉》、《易膽大》。京劇團在成都、重慶有,鋼城攀枝花也有,歷年來著力打造和推出的劇目有《鐘離香》、《雪寶公主》、《楊八姐智取金刀》、《黨的女兒》、《四川白毛女》、《少帝福臨》、《嘉陵怒濤》、《千古一人》、《薛濤》,以及《玉堂春》、《春秋配》、《法門寺》、《群英會》、《八大錘》、《雁蕩山》、《楊家將》、《白蛇傳》、《謝瑤環》、《鬧天宮》等等。
巴蜀是歌舞之鄉,民族民間文化資源豐富多彩。成都地區具代表性的歌舞作品有彝族舞蹈《幸福光》、歌劇《長腿的雞蛋》、舞劇《卓瓦桑姆》、舞劇《鳴鳳之死》、歌曲《奮進腰鼓》等,還舉辦過數屆國際古琴藝術研討會;重慶歌舞方面,歷年來創作、移植、改編了歌劇《巫山神女》、《火把節》、《哭嫁的新娘》、《魔鬼索爾南塔》、《海島女民兵》等,演出了《白毛女》、《紅珊瑚》、《洪湖赤衛隊》、《江姐》、《貨郎與小姐》以及《費加羅的婚禮》、《塞爾維亞理發師》、《多瑙河彼岸的薩波羅斯人》等歌劇及選段。省歌舞劇院推出的作品有舞蹈《快樂的羅梭》、《康巴的春天》、《川江女人》、《阿惹妞》,舞劇《遠山的花朵》、《阿月與阿星》、《悲嗚三部曲》,歌劇《格達活佛》、《青稞王子》,聲樂《嘉陵江號子》,器樂《將軍令》,等等。2004年、2007年兩度亮相中央電視臺春節晚會的《俏花旦》(歌舞、雜技),其創意也來自蜀地藝術靈感。木偶、皮影方面,諸如神話木偶劇《孫悟空三調芭蕉扇》、《沉香救母》、《那吒》等,給觀眾留下了不錯印象。天府四川,又是多民族聚居的重要省份。這里是藏彝文明、氐羌文化大走廊,有阿壩、甘孜、涼山三個少數民族自治州,有漢、藏、彝、羌、苗、回、土家、納西、傈僳等不同民族世代棲居。他們以雙手譜寫著歷史,以智慧創造著文明。隨著文化遺產保護意識在中國覺醒,隨著非物質文化遺產節在成都連連舉辦,挖掘地方文化遺產(物質的和非物質的)進行舞臺藝術打造成為當下時尚,如容中爾甲和楊麗萍聯手打造的歌舞劇《藏謎》、得益于羌族民間音樂資源的音樂劇《太陽花》,分別取材于考古遺址三星堆和金沙文化元素的川劇《青銅魂》和雜技劇《魔幻金沙》;又如,四川少數民族戲劇有藏戲也有羌戲,而彝族歌舞、羌族羊皮鼓舞、藏羌多聲部民歌等等近年來也屢屢亮相京城及熒屏,播譽四面八方。
二、禁區突破思想解放
政治高燒的“文革”十年,給中國文藝帶來巨大災難。彼時各地舞臺上,除了主流意識和權力話語主宰下依樣葫蘆式的幾個“樣板戲”,可謂別無選擇。1978年初,鄧小平同志路過成都,下榻金牛賓館,提出要看家鄉戲。于是,周企何、陳書舫、曾榮華、劉金龍等名家相繼出場,一連三晚演出了《拷紅》、《歸舟》、《畫梅花》、《迎賢店》、《喬子口》、《柜中緣》、《花田寫扇》、《評雪辨蹤》等傳統折子戲。當然,小平同志不僅僅圖的是過戲癮。他有更深的含意,就是要借此來促進文藝界思想解放。看戲之后,他接見了演職人員,語重心長地就開放傳統劇目問題作了指示。緊接著,3月,四川省文化主管部門發文,公布首批恢復上演的《拷紅》、《攔馬》、《迎賢店》、《別洞觀景》、《點將責夫》、《水漫金山》等傳統戲;7月,川劇藝術片《川梅吐艷》經峨眉電影制片廠拍攝,向全國發行;12月,應國家文化部邀請,川劇上
北京演出……撥亂反正,中國航船駛出歷史陰霾,戲劇界在新時期春風吹拂下解了凍,民族藝術隨著思想解放、禁區打破而再獲新生。1982年,四川發出“振興川劇”號召,被稱為“空谷足音”,得到戲劇界共鳴。
剛剛過去的200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第三十個年頭。回首往事,思想禁錮打破,人文精神復歸,巴蜀舞臺藝術意氣風發,格外活躍。在傳統觀念與現代意識的激烈碰撞中,在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頻繁對話中,當代四川以無愧于時代和社會的作品,交出了敏于思考又富于激情的答卷,在當代中國戲劇史上寫下了不可忽視的篇章。你看,《易膽大》、《潘金蓮》、《巴山秀才》、《田姐與莊周》、《歲歲重陽》、《紅樓驚夢》、《四川好人》、《欲海狂潮》、《夕照祁山》、《芙蓉花仙》、《婚變案》、《變臉》、《史外英烈》、《太后改嫁》、《大佛傳奇》、《劉氏四娘》、《目連之母》、《張大干》、《攀枝花傳奇》、《中國公主杜蘭多》、《山杠爺》、《都督夫人》、《冰河血》、《峨眉山月》、《周八塊》、《桃村新歌》、《杏花二月天》、《半邊月兒明》、《白蛇后傳》、《瓊江作證》、《九美狐仙》等等,一出出,一幕幕,或古裝,或現代,刷新著舞臺面貌,娛樂著人民大眾。其中,尤其不乏銳意創新之作。可以說,是改革理念鍛鑄了80年代的“探索劇目”,是創新意識釀造了90年代的“現代戲曲”。改革,使川劇在藝術形態上從傳統向現代轉型;創新,使川劇在文化意識上從本土向世界融入。今天,藝術生產力的解放,迫切呼喚著管理體制和運作機制上的革故鼎新。時下中國,隨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方針的確立,隨著社會經濟體制從計劃向市場模式轉化,轉變政府職能、調整劇團布局、改革分配原則、激活用人制度、樹立市場觀念、強化競爭意識等等又擺在巴蜀舞臺事業面前,成為當務之急。經歷著無法回避的陣痛,接受著改革浪潮的洗禮,四川文化人在不斷地超越自我,向前邁著步子
隨新時期興起的儺文化研究,涉及藝術學、民俗學、社會學、宗教學、人類學等方方面面。過去,人們總是談“儺”色變,簡單地視之為封建迷信而唾棄之。其實,那當中有深厚的文化內容。多年來人們對中國戲劇史的撰述,主要循守的是從書本到書本的治學模式,而對積淀著大量原始戲劇因素并長期活躍在鄉野民間的儺文化現象少有顧及。儺文化研究其實以其田野成果為戲劇史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東西。巴蜀民間儺文化遺產豐富,如土地戲、儒壇戲、梓潼陽戲、酉陽陽戲、蘆山慶壇、瀘州秧苗戲、南充儺壇戲、巴縣接龍陽戲、廣元射箭提陽戲,還有嘉絨藏戲、德格藏戲、羌族釋比戲、白馬跳曹蓋、石柱土家族土戲,等等。1993年9月,在四川省儺文化研究會成立大會上,郭漢城先生說:“我和張庚主編過《中國戲曲通史》,有很多局限,當時好多資料都沒有出來,對目連戲講得很少……另外,對少數民族的戲劇,研究的也很少。儺戲在少數民族中有相當發展。我們對儺戲要廣泛地研究,思路要寬一些。這個問題一定要解決好。將來對戲曲史的修改,寫一部更完備的戲曲史,會有重要作用。”跟新時期十大文藝集成志書修纂相呼應,國內正式出版了兩部省級儺戲專志,這就是20世紀80年代的《湖南儺戲志》和新千年(2004年)的《四川儺戲志》。1999年,省文化主管部門同意編撰《四川儺戲志》的文件即稱該志為“十大集成志書《中國戲曲志·四川卷》編纂工作的延伸與繼續”。據2008年11月5日《成都晚報》報道,一臺題名《尋根》的話劇在成都推出,由自由演繹青年戲劇坊制作。該劇以民間儺戲藝人的處境為故事背景,將儺文化元素與現代戲劇相結合,探討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的位置等問題。當今四川舞臺上,《目連之母》、《劉氏四娘》以及有涉民間儺風儺俗的劇目出現,皆跟改革開放后端正了心態和觀念的本土儺文化研究直接相關。
三、東西互動海外揚名
真正優秀的藝術沒有國界限制,它是人類共有的精神財富。隨著東西方文化交流開展,巴蜀地方藝術也跨出國門,影響不斷擴大。以包括清音、揚琴、竹琴、諧劇、金錢板等的四川曲藝為例,1957年李月秋攜四川清音赴蘇聯參加第六屆世界青年聯歡節,所演唱的《小放風箏》、《青杠葉》等榮獲金質獎章;1986年,應法中友協、法國東方之友協會邀請,成都市錦江區曲藝團攜四川揚琴赴法參加第十五屆巴黎秋季藝術節,受到熱烈歡迎;1987年,程永玲等參加成都市民間藝術家小組赴南斯拉夫盧布爾雅那市和奧地利林茨市演出,亦獲好評;1992年,應法中友好協會邀請,飛刀花鼓藝人陶明成、劉陶爺孫倆隨中國民間藝術團,參加法國蒙彼利埃第六屆演員之春藝術節和阿溫尼翁國際藝術節,演出20余場……新時期以來,巴蜀民族民間歌舞以及雜技、木偶、皮影等藝術也紛紛出訪,獻藝數十個國家和地區,并在世界舞臺上屢屢獲獎。
“Beijing Opera”是老外對京劇的稱呼。同樣“以歌舞演故事”的川劇,到了洋文中也被叫作“Sichuan Opera”。當年,英國《泰晤士報》上就曾出現“四川歌劇到歐洲”的醒目標題。1959年,由陳書舫、周裕祥、袁玉墊、許倩云、司徒慧聰等組成“中國川劇團”,先后在波蘭、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民主德國進行訪問演出,歷時142天,演出69場,帶去大幕戲《芙奴傳》、《焚香記》、《譚記兒》和中、小型劇目《秋江》、《放裴》、《射雕》、《攔馬》、《金山寺》、《柜中緣》、《別洞觀景》等,讓不同膚色的洋觀眾們看得很興奮,連連贊嘆“中國戲曲這朵世界文化的鮮花仍然開得如此美麗”(波蘭《人民論壇報》)、“中國的歌劇轟動了我們的城市”(捷克斯洛伐克《新自由報》)。隨著改革開放,四川戲劇有了更多機會亮相海外。1985年,省川劇團攜《秋江》、《攔馬》、《白蛇傳》等赴歐洲參加西柏林85地平線藝術節;1987年,川劇《白蛇傳》劇組來到東鄰日本;1989年,省川劇院赴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三國15個大中城市訪演;1990年,川劇藝術家藍光臨應邀登上法國巴黎哈黑達戲劇學院講壇;1991年,樂山川劇團攜《人間好》、《水漫金山》等赴日本;1992年,川劇《芙蓉花仙》飛越鴨綠江,獻藝于朝鮮;1993年,德陽川劇團赴俄羅斯演出;1994年,成都川劇院赴德國演出《四川好人》;1996年,魏明倫的《潘金蓮》由重慶川劇院帶往新加坡演出;2000年,綿陽川劇團赴日本演出《碧波紅蓮》;2008年,遂寧川劇團赴羅馬尼亞獻藝……
1999年,一出頗具表現主義色彩又努力本土戲曲化的《馬克白夫人》出現在首屆中國川劇節上。作為西方文本的東方演繹,該劇轉換了敘述視角,以馬克白夫人替換了莎士比亞筆下馬克白的主角位置。于是,觀眾有幸隨編導重新認識和闡釋了這部文藝復興時期的杰作。2001年3月,川劇《馬克白夫人》應邀赴德國參加“不來梅莎士比業節”,使兩方觀眾也有機會品味“川劇版”的莎士比業。1999年,第八屆全同尤金·奧尼爾學術研討會召開之際,從奧尼爾《榆樹下的戀情》(又澤《榆樹下的欲望》)脫胎的川劇《欲海狂潮》獻演在與會代表面前。奧尼爾,一位充滿悲劇意識又富于人文關懷的美國現代戲劇家,能引起華土戲劇界共鳴并非偶然,如改編者所言:“我喜歡他的作品,特別欣賞他的悲劇意識,欣賞他筆下那些為了追尋理想或光明而走上悲劇道路的主人公。奧尼爾認為唯一值得寫的主題,是人的永恒悲劇。”改編不等于簡單照搬,改作不止將原作里的“美國生活中國化了”,而是盡量調動起東方戲曲手段進行再創作,將“欲望”角色化并使之成為劇中核心符號就是蜀地戲劇家的創造,《欲》劇首演于1989年,當時曾邀請美國駐成都領事館代總領事季瑞達等人在翻譯陪同下觀看此劇,觀后他說:“‘欲望的出現很有創造性。原作中沒有這個形象,這是你們的創造,也符合奧尼爾要表達的意思。”新世紀之初,該劇再度加T排演,亦得同行及觀眾好評。
四川戲劇也借助翻譯文本向海外傳播,20世紀五六十年代,外文出版社推出英譯本川劇《柳萌記》、《望江亭》等,英文版《中國文學》雜志亦刊登了《川劇節》、《拉郎配》、《評雪辨蹤》以及《川劇》等劇作和文章(1992年10月,《中國文學》又曾推出川劇《田姐與莊周》的法文譯本)。相繼刊載這方面英文著、譯的國內報刊尚有《中國建設》、《北京評論》等。前者發表過陳書肪的《川劇新生》,后者登載了介紹《巴山秀才》的文章《一個學者的悲劇》。在大洋彼岸,1978年,傳統戲《評雪辨蹤》經William Dolby翻譯后,載人其書《Eight Chinese Plays from lhPThir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1996年,Shiao-Ling編譯的《Chinese Drama after the CuhuralRevolution,1979~1989》中,亦收入川劇《潘金蓮》。川劇藝術亮相海外,還吸引來自己的“追星族”——鐘情川劇并執意要學川劇的洋戲迷,如來自大洋彼岸的蘇珊、馬可、白靈芝等人。凡此種種,同于篇幅,恕不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