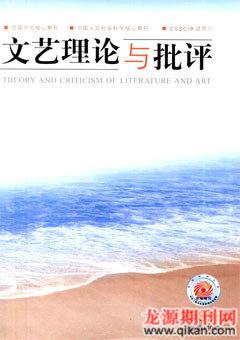回望十七年的文學理論傳統
馮憲光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60周年的時日。現在已經發表了不少文章,以紀念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的榮光。共和國走過的這60年并不是一條平坦、筆直的道路,其中有曲折,有挫折。我讀到時下一些論者的大作,較多的是把60年劃分為兩個整塊,即兩個30年。一些論者認為,前30年乏善可陳,災禍橫生,后30年鶯歌燕舞、無比輝煌。這種觀察、分析人民共和國的60年的狀況、歷史的觀點,是以改革開放截然劃分為新與舊兩個時代。人民共和國在20世紀80年代,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這30年新中國的建設事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簡單地把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攔腰截斷,忽視和否定人民共和國60年整體的基本方向和整體成就,是并不實事求是的。歷史的任何一個節點,同時都又是過去的延伸,未來的萌生。歷史是不容割斷的,更可況,改革開放本身是在人民共和國自身發展的歷史過程中進行的,它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不能抹去人民共和國改革開放前的歷史,而使改革開放以后的共和國成為改朝換代的歷史。
去年我們剛剛紀念過改革開放30周年。中國改革開放的這30年,是現代化建設高速進展的30年。可以說,一百年來中華民族的仁人志士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灑下的無數鮮血,1921年以來中國共產黨為謀求中國走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道路的英勇奮斗,60年來人民共和國對強國富民道路的不懈求索,都在這30年產生了深遠影響,結下了碩果。應該說,從歷史進程的結構性因素來看,1949年由“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作為歷史起點的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是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走上改革開放道路的主導基礎。中國在晚清就開始了部分市場經濟的改革,外資利用帝國主義的炮艦強行進入中國國土,而蔣介石政權早就實行了全面的市場經濟、大量引入外資等等,結果中國民生凋敝、國家危機重重。只有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才有可能走上民族獨立的而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現代化建設道路。
1949年是中國翻身解放之年,在中國建立了一個新的人民共和國,這是中國走向現代化建設道路的重要前提與保證。沒有民族的獨立和國家的主權,沒有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地位,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無法進行。本文在這里講這一點,意在說明,1949年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是研究中國當代歷史的一條底線。忽視和否定人民共和國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成就,割斷歷史的整體性,就不能對60年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做一個全面、準確的認識。本文是討論新中國的文學理論的,有感于此,本文著重回望建國前期十七年的文學理論,提出不能只要后30年,不要前30年,應該認真繼承和總結十七年的文學理論傳統。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的文學理論研究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指引下,表現出科學性、現代性和中國特色這三個明顯特征。所謂科學性,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指導和科學精神,堅持從科學角度研究和闡釋文學的獨特性、豐富性,進行自主性的多學科理論研究,提高與完善文藝學研究的科學水準。所謂現代性,是指文學理論研究必須具有現代學術素養和現代學術品格,即應當在21世紀全球文化現代發展水準和知識背景上,展開文學理論的研究,著重研究和回答現代社會中的文學問題。所謂中國特色,是指在全球化現代文化知識融合的背景下,注重中國文學的本土因素和文學理論民族特性的研究,提倡和形成具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當代文學理論。只有如此,在全球化的文化交流與融合中,中國當代文學理論才有實力,以本土文化的文化身份,去參與全球化的文化對話。
最近這30年中國文學理論研究所形成的科學性、現代性與中國特色的特征與趨勢,是中國當代文學理論走向成熟和繁榮的標志。改革開放30年的成就是建國60年業績的組成部分,是60年奮斗努力的結晶。可以說60年共和國的文學理論研究歷程,也就是文學理論研究走向科學性、現代性與中國特色的歷史。我們從科學性、現代性與中國特色如何形成和發展的角度來回顧60年文學理論研究的歷程,能夠更好地總結當代文學理論發展的規律,是有重要意義的。
我們回顧60年文學理論研究走過的道路時,應當看到它與中國60年來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實踐的曲折發展過程有直接關聯。60年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前17年,是社會主義事業的初創期和探索期,也是文學理論現代化建設的初創期和探索期。第二階段是“文革”十年,是現代化建設的中斷期。第三階段是30年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文革”十年,科學性的學術研究很難存在。而對于30年改革開放時期的文學理論研究成果則是有目共睹,世所公認。60年學術回顧的一個被遮蔽的部分,甚至成為重點和難題的,似乎是在對前17年學術研究的評估這點上。因為對“文革”十年的狀況都看得較為清楚,而改革開放30年的學術成就,我們已經多次總結。時常存在的問題倒是,是否建國60年的成就都集中在這30年中呢,是否前17年乏善可陳呢?
的確,前17年文藝界、學術界搞了一些“左”的政治運動,使一些有貢獻、有才華的藝術家、理論家受到不公正待遇。這使文學理論的現代化建設受到打擊和傷害,是一種重大失誤。前17年國家以行政手段強調文藝為政治服務,正如鄧小平所說,“這個口號容易成為對文藝橫加干涉的理論根據,長期的實踐證明它對文藝的發展利少弊多”(《目前的形勢和任務》)。這種狀況直接影響到文學理論研究,在前17年中文學理論研究普遍存在著圍繞政治運動風向轉動的情況,許多文學理論研究缺少自覺的現代化建設意識。有了這些問題,是不是就證明前17年的文學理論研究毫無成就可言呢?當然不是。鄧小平指出:“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們的文藝戰線基本上是正確的,文藝工作的成績是顯著的。”(《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這里對文藝工作整體的肯定,也包括對文學理論研究工作的肯定。
這一時期文學理論研究中存在的問題與取得的成就都表現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初創期和探索期的特點。存在的問題表明初創與探索的不易和不可避免的錯失。而對成績,也要從當時處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初創期和探索期這樣一個特定的歷史背景來認識。
建國前后文學理論研究的一個重大變化是,建國以后我國確立了走蘇聯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體制,因此在文學理論研究中也相應確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地位,特別是引進蘇聯模式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態勢。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夕,1949年7月2日,全國第一次文代會開幕,這次會議明確提出文藝工作要以毛澤東1942年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作為指導。這種帶有
國家意識形態的舉措,使17年的文學理論研究以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學習、宣傳、研究作為重點。而在學習、宣傳、研究上,又以學習和宣傳作為主要理論活動方式。現在看來,它存在著對于文學研究的基本對象文學事實本身研究的不足,但是它又具有與建國前文學理論研究所不具有的優勢,使得文學理論研究者普遍地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武器,取得了不能否定的成績。新中國成立以后,翻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藝論著成為新中國譯介和研究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首要任務。1951年8月,由周揚主編的《馬恩列斯論文藝》(1953年重印時改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文藝》)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這是這個1951年3月才成立的國家出版社的最早的出版物之一。這本書以1944年5月延安解放社出版的周揚編《馬克思主義與文藝》為基礎,選編了20余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文藝論著,由曹葆華等翻譯,周揚對所有譯文都做了校訂。此后又陸續出版了前蘇聯學者選編的《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和《列寧論文學與藝術》等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文藝論著。為了更為廣泛地翻譯、出版國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書籍,1958年12月,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文學研究所(后為外國文學研究所)組建編委會,與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合作,翻譯編輯出版“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叢書”、“外國文藝理論叢書”、“外國文學名著叢書”等“三套叢書”。編委有:巴金、錢鐘書、朱光潛、季羨林、李健吾、樓適夷、楊憲益等。據當時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叢書”的程代熙回憶,“上面提到的‘三套叢書,在后來出書時正式亮出叢書名義的只有兩套,即《外國文學名著叢書》和《外國文藝理論叢書》。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叢書》的旗號卻始終沒有正式打出來。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們深深感到自身經驗的不足,因為這不是編輯一套一般文藝理論叢書,而是經典文藝理論叢書。所以我們沒有急于打出叢書的旗號,何況叢書中的《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和《列寧論文學與藝術》兩本只是簡單地從外國‘拿來。還不是我們自己學者編輯的本子。為了使讀者意識到這是一套叢書,我們只是在封面、版式、規格等方面先做到大體上的一致。”(程代熙《我是在編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叢書)的工作中成長起來的》,《批評家》1986年第5期)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具有普遍解釋能力的現代理論,使新中國的文學理論研究走上了科學性、現代性的道路,同時毛澤東文藝思想極其富有中國特色。新中國17年的文學理論研究具有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強有力的指引,這是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科學性、現代性和中國特色的走向的基本因素。
1904年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被學術界視為中國文學理論現代轉型的代表作與標志。它運用叔本華的悲劇理論來闡釋《紅樓夢》的藝術價值,其根本特征是引進西方文論的思維方式、概念術語。從1904年到1949年,這近50年的中國現代文學理論研究,總體上也是依循王國維的路數,引進西方文論對中國傳統文論研究方式作體制性改變。只不過許多學者所崇奉的理論指針,所擷取的西方文論流派各有不同而已。1949年以后,文學理論研究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指導,我認為從文學理論的體制方式來看,這是對以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為代表的中國文學理論現代轉型的延伸和發展,這種追求現代性、科學性和中國特色的理論努力并沒有中斷。
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對延安和解放區當時的文藝問題進行分析,這部文藝論著就與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一樣,超越了中國傳統文論局限于對作品進行鑒賞式品評的形態模式,而具有哲學世界觀的高度。而且,毛澤東十分明確地以主客體關系范疇角度來解析文藝與生活的復雜關系,達到相當的理論高度。《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帶給建國后中國的不僅是文藝為政治服務的運作方式,而且特別在思維方式上提升了文學研究的理論色彩和科學追求。50年代中國對蘇聯文學理論大量引進,有對蘇聯文學理論簡單仿效的問題存在,有對西方文學理論一味排斥的片面性存在,同時隨同蘇聯文學理論的引進,帶來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美學思想、馬克思主義所繼承的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德國古典美學思想,也使中國文學研究的應用型、鑒賞型傳統思維方式,得到科學性、現代性的改造。由于《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中國化的著作,對這一著作的堅守與闡發,又使中國文學研究沒有完全“蘇化”,沒有失去中國自身特色。
把建國60年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就應當看到前17年不能簡單否定。這段時期有許多錯誤與不足,但是它畢竟在建國后奠定了中國文學研究科學性、現代性和中國特色這些根本因素的存在基礎。而且,文學理論研究的歷史回顧應當著重研究和闡釋各個階段文學審美意識的理論化程度,敘述文學審美意識理論形態變化的過程,展現文學審美意識理論的連續性與不連續性的歷史。如果把思考的著眼點放在這里,那么還會看到,有些深刻的理論思想,可能在前17年就開始形成,那時出現的某些思想也許至今仍然未能超越。比如胡風強調發揮作家創作的主觀戰斗精神,以這種主觀精神去關注現實,擁抱生活,從而實現文學對現實的深刻把握的思想,在力圖追求主體意向與現實可能性走向的統一方面,在我看來就比新時期劉再復的文學主體性理論要切實和深刻。學術史往往就是思想史,思想史就是某些核心思想連續與不連續的歷史。胡風的思想被封存了30年以后,中國才重新提出研究作家創作的主體性問題。胡風具有現代性的理論思想,在新時期得到了延續。
與之類似的還有藝術的人道主義問題、文學的審美特性問題、現實主義深化問題,等等。胡風的創造性文藝思想出現在建國初期(這里討論的范圍只是建國以后,不涉及建國前的材料),而前17年在文學重要問題的討論中,出現的具有科學性、現代性的思想,主要在1956年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以后和1957年大規模反右運動以前,以及1960年以后到1964年政治性學術批判以前這兩個時段。
在倡導藝術的人道主義精神方面,錢谷融1957年2月寫就,發表于1957年《文藝月報》5月號的《論“文學是人學”》,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這篇文章全面論述了文學與人的存在關系,提出人是現實存在的焦點,抓住了人,也就抓住了現實。而且,作家的美學理想和人道主義精神,應該是其世界觀中對創作起決定性作用的部分。缺乏人道主義精神,作家就無法成為現實主義者。同一時段,《新港》在1957年1月號發表巴人的《論人情》,又在7月號發表王淑明的《論人情與人性》,這些文章都呼吁文學對人情和人性的描寫。后來錢谷融、巴人、王淑明等這些倡導藝術的人道主義精神的學者和他們的思想,都受到
批判。在“文革”文化專制主義統治下,所謂《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主持的部隊文藝工作紀要》還把這種觀點扣上“資產階級人性論”的帽子,其實“四人幫”所執意要批判的“黑八論”,基本上就是前17年有科學性、現代性和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成果。“文革”的大批判,把所謂“黑八論”構筑為一個個學術禁區。新時期文學理論的開拓性發展,首先就在對“黑八論”禁區的突破。朱光潛在1979年第3期《文藝研究》上發表《關于人性、人道主義、人情味和共同美問題》,明確指出粉碎“四人幫”后,學術界“對過去形成的一些禁區仍畏首畏尾,裹足不前。這是和四個現代化的步伐不合拍的,是不可能促進文藝繁榮的。當前文藝界的最大課題就是解放思想,突破禁區。”他提出首先要突破的禁區就是“人性論”、“人道主義”禁區。錢谷融也在1980年第3期《文藝研究》上發表《(論“文學是人學”)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綱》,重申了1957年的觀點。此后學術界就開展了持續時間很長的關于人性論、人道主義的討論。文學應當表達人學的本質,文學應當具備人道主義的藝術魅力,在討論中成為理論界的共識。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的現代性思想就從這里樹立了起來。我們從中可以看到,新時期的文學理論的成就往往是在17年學術探索基礎上取得的。17年所奠定的學術基礎,不是連續性發展的基礎,而是在“文革”中斷學術發展后,在新時期開始后,人們對極左思潮蓄意扼殺的現代性科學思想的反思性承接和延續。
所謂“形象思維論”也是“黑八論”之一。前17年在對文學審美特性研究中,突出的論著有詩人艾青的《詩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中國素有作家文論傳統,艾青在本書中提出了許多具有現代性、科學性的美學思想,其中關于文學形象創造的論述尤為精彩。他指出,寫詩是一個艱苦的創造過程,詩人用感覺的鋼錘去敲剝生活對象,使自己的感情燃燒,以情感之火去熔化對象,鑄造詩句。形象是文學的開端,詩歌的特性是用形象理解世界,用形象解說世界,意象、象征、聯想、想象則是形象化的手段。這是建國后較早的對形象思維的論述。蔣孔陽的《論文學藝術的特征》(新文藝出版社1957年)提出文學的意識形態傾向性必須通過藝術形象表現出來的重要觀點,對文學形象特殊性的研究有顯著貢獻。1963年出版的以群主編的《文學的基本原理》,作為高校文科統編教材,把形象性作為文學的審美特殊性,把文學的創作特點歸納為形象思維。這些論述都是前17年的重要成果。當然,形象思維論在“文革”中被當作修正主義觀點批得體無完膚。而新時期開始的撥亂反正,又是從對形象思維的重新研究起步的。在摒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維方式以后,在克服了把文藝等同于政治的庸俗社會學以后,文學的審美特性得到了充分認識和研究。新時期從對形象思維、藝術掌握世界方式的研究,逐步深入,進而研究藝術審美本質、藝術創作與欣賞的審美心理、藝術文本的審美言說能力等等問題,真正使文學理論研究步入現代性、科學性的軌道。
“寫真實論”和“現實主義深化論”也都在“文革”中被列入“黑八論”予以批判。所謂“寫真實論”和“現實主義深化論”都是要求文學在描寫現實時,要實事求是地面對現實,如實地反映現實的真實面貌,既要展示現實中的鮮花彩帶,又要顯露現實中的陰暗痛苦。只有這樣,才能使現實主義創作不至于成為對某些現實看法公式的圖解,而取得深化的成就。這種觀點無疑具有現代意義。但是,無論是發表《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的秦兆陽,還是提出“現實主義應當深化”主張的邵荃麟,在過去都遭受不公正待遇。他們的深刻見解也只有在新時期才得到重新肯定和發展。新時期文學理論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對現實主義理論的研究。在總結長期以來的“左”的創作指導思想的失誤時,巴金反復提出并多次強調,作家要講真話。在年過90高齡以后,巴金在年邁體衰的情況下,勉力寫下的少數文章和題詞,都只有一個主題,就是作家要講真話。真話是對現實正確的言說,誠實的言說。它既直面人生,包含對客觀現實正確的認識,又直面自我,包含對待現實與自我關系的坦誠不虛的倫理態度。這事實上就是藝術的現實主義精神。巴金的這個“講真話”的話題,得到了許多作家、理論家的贊同。巴金的“講真話”這一個總思路實際上是17年的現實主義深化論的延伸。
特別值得提及的是,中國長期從事比較文學研究的著名學者錢鐘書的《管錐篇》(第1—4冊),其初版由中華書局1979年出版,其序言寫定為1972年1月,這一煌煌巨著當寫作于20世紀60、70年代,是整個新中國60年文學理論研究的傳世之作。這是一部在寫作和出版時間上剛好橫跨人們所說的前30年和后30年之間的一部理論巨著。從其寫作時間和出版時間來看,正好說明把前30年與后30年截然劃斷,是不符合基本歷史事實的。這部巨著應用了文學和文化的比較方法,但不能簡單地視為比較文學論著,而是一部理論論著。它的著述體例是以中國《周易》等傳世古籍作為評論對象,從古籍中拈出一些關鍵語句,于古今中外詩文故實里旁征博引,參證比較,闡釋中國文化與文論的精妙之論。這種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不僅表現了錢鐘書學貫中西的淵博學識,而且特別展現了他對于中國文學理論研究的示范性貢獻。錢鐘書的研究首先打破傳統文論研究的狹隘視野,并不單純就詩文作品作文學理論研究,而是在文化典籍中探索對文學的理論理解,具有廣闊的文化學視野。錢鐘書對西方古今文化與文論有精深研究,在這種全球化文化知識背景中,展開對中國《周易》等文化元典的闡釋學研究。這也就是在貫通當代中西文學理論的學理,在今天中西文學理論所達到的時代高度上,以中國文化元典作為文論資源,對中國文化文論精華進行深度發掘與闡釋。這部著作當然就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研究現代性、科學性和中國特色的代表。《管錐篇》所開拓的研究方法,所達到的學術成就,將成為新中國60年文學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的標志性的成果。
回望前17年,不是固守17年,而是強調在審視共和國60年的歷史時,應當重視17年為改革開放以后走出的寬廣道路的奠基貢獻。建國60年我國文學理論研究走過的道路,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不斷探索文學理論現代性、科學性和中國特色的道路。我們應當珍視這些成果,特別是應當繼續沿著探索文學理論現代性、科學性和中國特色的道路,勇往直前。只有從這里,我們才能走向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