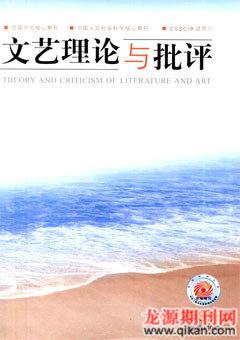聆聽故土上空飄揚的炊煙
張 春
改革開放后,從短篇小說里分離出來的小小說正日益成為當代文學的一道風景。縱觀近30年的小小說,有很大一部分是關注鄉土關注農民的。僅以《當代小小說名家珍藏》(2002)和《中國當代小小說大系》(2009)為例,有關鄉土的小小說就占了六成左右。由此可見,在小小說的蓬勃發展過程中,鄉土題材是不可回避的話題,體現著作家在物欲橫流的時代對鄉土家園的堅守,昭示著文學發展進程中某些不能移轉的關注焦點,也凸顯著當下語境中小小說難得的清醒和獨特意蘊。
現實主義是中國20世紀創作方法的主流,真實客觀地再現社會現實,這是現實主義術語最根本的意義。達米安·格蘭特曾用“應合”理論來解釋現實主義的客觀性成規,他稱“如果文學忽視或貶低外在現實,希翼僅從恣意馳騁的想象汲取營養,并僅為想象而存在,這個認真心理就要提出抗議”。文學對現實的忠誠和責任,使小小說作家們不能回避改革開放后農村的巨大變化,以及在這種變化中所揭示的價值觀沖突和在沖突中所表達出的默默溫情。
一、“風雨中前行”:鄉村改革進程之路
描述改革開放后農村的喜悅變化,是30年來鄉土文學的一個中心話題,字數在1500字左右的小小說也自然地給予了很多關注。當然這種關注絕對不是鋪天蓋地的謳歌,而大多采用一種樸素寫實的筆調進行描述。這種描述也許與謳歌有關,也許與世態有關,也許還與披露有關,體現著鄉村改革進程中曲折發展之路。
(一)凸顯新農村的巨變。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也自然改變了鄉村,生機勃勃是關鍵詞。《山鄉的五月》中的根西每次回到鄉下,面對故鄉巨大的變化都有一種觀光的心態。當被工廠裁員后,一種與生他養他的土地無法進行心靈對話的彷徨和無奈,最終使根西完成了角色的轉換,扎根農村并成為了遠近聞名的種糧大戶——根西與土地從遠到近的過程,喻示著聯產承包責任制后廣闊農村可大有作為。《麥客》則通過描述“我”在80年代初當麥客的辛苦,轉型到80年代末的麥客經紀人,再到90年代使用收割機當機麥客的過程,詮釋著農村發展之路。《男人》中的男人就是一個受傳統文化影響的男人,堅忍不拔成就了他面對困難、面對饑餓不低頭的形象。農村經濟往來是少有收據證明的,但何百源卻在《翻臉》里用阿亮對親戚阿實的訴訟,道出了現代農民的法制觀念正日益健全。面對“到底是要面子還是要肚子”的問題,《抬花轎的老師》中的老師玉林為了還債,寧愿在過年時做最被人小瞅的抬轎營生,凸顯觀念轉變。《煙棒》中的岳老黑為村民修路不怕得罪鄉長親戚,體現了作為一個老村長的高尚風格……
(二)關注農村世態紛紜。70后作家秦俑的Q村系列,都對農村發展過程中世態炎涼的鋪陳給予了觀照:《八爺的六十大壽》中的八爺要做大壽,為了爭面子要求兒子冰天雪地里三番兩次請村里最大的官村支書;《四眼》中的四眼為了獨吞水井里的一塊無中生有的寶石,深更半夜下水尋找而丟了性命。《兩瓶貴州醇》中的村主任,是一個熱情的人,但他的這種熱情往往顯得有些多余,在認真說服寶鎖打消離婚念頭后,才接受本無事可求的寶鎖送的酒。《村長》中的村長卻是一個被冤枉的村長,為了不想再做盡得罪人的工作,他想方設法地要求鄉長辭了他,但在征求鄉長同意抬了二狗家的糧食后,恰遇市里三令五申不得強搶,他被鄉長以素質不高的罪名尷尬地辭掉了,故事將農村基層干部事難做、人難為的現象表現得入木三分。另外,沈祖連的《五婆的鳥巢》、孫學文的《泥塘》、曹德全的《煙棒》、趙新的《高興》等作品也都關注著農村中的世態紛紜。
(三)表現改革之路的艱辛。農村是個大社會,改革進程之路猶濕艱難。王奎山在《割韭菜》里就對某些村干部的胡作非為進行了批判:劉三家的韭菜被村主任老婆割了,他罵街不成還被村主任羞辱了一頓,老婆水芹也在村主任的“特殊關照”下成了婦女主任,但這卻是以劉三的恥辱為代價的。趙文輝的《好事》則披露了以鎮政府白秘書為代表的一群官僚:村支書文玉為了評選好人好事,本來就是好事的事情還要上下找人活動,花費了本不該花費的財物不說,還欠了白秘書一個人情。同樣讓人氣憤的是在梁海潮的《選票》里一些希望當村長的候選人,四處花錢請人填票不僅顯得可悲,讓人感覺到農村基層組織中的某些不正常。而且這種不正常往往又與上一級有關,如《池塘無魚》中的鄉長為了讓縣長們周末能在池塘里釣到魚,命令村長在無魚的池塘里放魚,充滿了諷刺意味。而《劉老爹的酒文化》中的劉老爹就對這種無奈感到了心痛:已經是市長的兒子寶根每次回家都會提越來越貴的酒,但這卻讓劉老爹找不到從前爺兒倆一起喝燒酒的滋味了。在凌可新的《偷樹》里,曾經是護林員的木看不慣別人偷樹,多次反映無效,萬般無奈之下偷了棵樹到派出所自首,所長說一棵樹夠不著拘留……
二、“沖突中拷問”:家園建設中的價值選擇
伴隨著農村改革進程的加快,人們曾經根深蒂固的價值觀念得到些許轉變,看待同一件事情,已經不再是同一種聲音,而是已漸漸學會用思想的眼光來觀照,體現了社會的一種進步。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農村建設中還存在這樣那樣的欠缺與不合理的現象,而大多人只是立足于自身角度為出發點思考問題,因此推動農村現代化建設將任重而道遠……
(一)凸顯悲憫情懷。悲憫其實并非一個貶義詞,而是作品中透露出的一種無奈,常讓人沉重。《扶貧經歷》中的“我”代表縣里給農民郭改名送去扶貧款,但最后是“你前腳剛走,后腳村里就收走了,說是抵了去年的提留款”,從而折射出某些基層組織的腐敗。《稻草人》中的“他”,在村長們的“關心”下,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稻草人。《太學生》里的村支書兒子最終選擇臥軌自殺,質疑著望子成龍與支書特權的價值困惑。《彎道》中的李發順靠公路彎道發車禍財,最終他自己失去了一條腿。《娥》中的國哥的思想也要轉變,因為他的所謂“正義感”,讓啞女娥和自己都成了犧牲品。還有石鳴的《三月花開》里的桂花、包利民的《山上山下》里的小王、張新平的《欠條》中的二桂、楊崇德的《官訓》中的“我”、劉殿學的《有關部門》的“有關部門中的人”、喊雷的《鴨趣》中的朱科長們以及肖有亮的《老汗》中的老汪,都折射出農村世態中所表露的悲憫。
(二)體現價值尊崇。農村人的觀念是很難改變的,但某些“根深蒂固”的思想卻又那樣地讓人尊重。蘆芙葒在《三叔》里刻畫的三叔,一直希望戰勝家旺,但當家旺家真的因為車禍衰落時,他卻給家旺提供支持,“希望家旺能重新振作起來,像以前那樣和他斗一斗,那樣活著才有意思”。趙新的《高興》中的生兒當上村長后才在與“爹”的對話中明白,作為村長更應當扎根土地,應當將“耕讀傳家”作為一種文化予以堅持。在喊雷的《生死抉
擇》中,拄著拐杖的劉大爺目睹風雨中橋被沖垮,為了避免司機從斷橋上被水沖走,他“視死如歸地又一次站在了公路中間”。何曉在《觀鹿山的戲樓》中刻畫了變質蛻化的兒子對應著的一身清廉的曹先生,“看不見姑且聽之,何須四處鉆營,極力排開前面者;站得高弗能久也,莫仗一時得意,挺身遮住后來人”。深意無限,哲理明顯。《天浴》則傳達出愛好洗浴的葉子的價值選擇是正確的,雖然離開洗浴城回到家鄉的她“提著桶在院子里轉來轉去,卻怎么也找不到一個可以洗澡的地方”,但卻回應了作為一個年輕人對夢想的追問。
(三)凸顯和諧價值。金錢與環境、物欲與時間等問題常常困擾著改革開放中的農村和這片鄉土的人們。在賈平凹的《獵手》中,獵手在殺盡山林中的狼后一直想方設法尋找狼,當他死后發現與自己一起掉下去的其實是一個披著狼皮狩獵的獵人,而在掉落過程中他發現狼是殺不盡的,此時他才恍然大悟,應當追求一種自然的和諧。在李浩的《被買走的時間》中,陳痞們為了獲得暫時利益而不惜污染土地、最后遠走他鄉后的醒悟告訴讀者,犧牲的不僅是土地還有永遠不可能回來的時間。趙文輝的《賣牛》則刻畫了老實憨厚的小順和老漢的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何曉在《那是留給雀子過冬的》為讀者鋪陳了一副和諧的美景:張家小院里樹上的柿子從來不摘,僅僅是希望那些過冬的雀子能夠留下來,表達了人與動物的美好相處。申平在《頭羊》里折射出人的自私與動物的偉大,希冀著更多的人來尊重動物。侯德云的《冬天的葬禮》里,在饑餓的冬天,一座小村祭奠的是一群老鼠,因為它們曾用創來的糧食拯救過饑餓的人們……
三、“花開的聲音”:鄉村大地上的主旋律
30年來的鄉土小小說中,優秀作品猶如雨后春筍,塑造出很多優秀的人物形象,這些形象中透露出的默默溫情,自始至終都能讓讀者獲得感動,猶如千姿百態的花朵在馨香中使人感到春暖花開的美好意境。
(一)彰顯“文化之美”的氛圍。曾經獲得過莊重文學獎的短篇小說大家聶鑫森,在小小說領域里也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塑造的人物形象總是那樣生動,他營造的作品氛圍總是那樣地富有文化之美。如《逍遙游》中古籍校勘與論證專家賀先生,是一個經歷過大風大浪卻又毅然堅守著精神家園的老教授,他對年輕小伙子陶淘的言傳身教,使陶淘走上了人生正軌。賀先生辭世時很安詳,因為“我現在把該做的事做完了,寫完了書,還有了你這個傳人,此生無憾”。還有《大師》里的著名山水畫家黃云山,這是一個知名的畫家,但當他面對一個已故農村畫家的作品時,他說,“我愿以我平生的一幅得意之作,交換你父親的任何一幅小品”,小說塑造了兩位真正的大師。劉建超在《老街漢子》里先抑后揚地塑造了一個耿直的牛五,表現出一個真正的軍人的文化性格。
(二)透露“詩意之美”的溫情。具有詩人氣質的于德北,在《秋葉》里塑造了充滿夢想又詩意般死亡的詩人佳衛,將敢于擔當的人民子弟兵高大偉岸的形象凸顯出來。王奎山在《紅繡鞋》里“渲染的是在這災難的打擊下麥苗的那種感人肺腑的愛心和大方得體的孝心”。尹全生在《七夕放河燈》里通過翠子、河生和大順的三角戀,體現了大順的偉大,突出著一種暖意。在曹德全的《大山的情緒》中,男人在獵人朋友去世后,依然把獵到的野兔勻一半放在朋友家門口,然后唱著山歌離開。表現了鄉村獨有的詩意。陸穎墨的《鐘樓》里塑造了流浪漢紅根在老流浪漢阿勇去世后的傷心,因為“除了他,還有誰可以讓我來可憐呢……”還有李永康的《十二歲出門遠行》、《路》、《將軍樹》、《五奶奶》、《楊子榮》、《娟娟》、《絕招》、《愛我的人已經飛走了》等,都真實地傳達著一份難得的溫情,這在普遍以故事或者情節為技巧的小小說敘述中,是極有創見的。
(三)展示“樸素之美”的意境。文化人李文秋和寡婦小月(劉國芳《鄉村軼事》)的交往,樸實中透露出平淡是真的愛情和傳統的扶持精神。在劉建超的《遭遇男子漢》中,葉子在逃離城市后遇見了救助她的男人,她發現山村的愛情是那樣地令人迷醉。在郭昕的《玉子》中,被愛情迷醉的玉子,在丈夫的移情別戀中勇敢地走出,體現了她追求真正生活的主見性。在王瓊華的《心事》中,老單身漢二德牯暗戀著寡婦桂花卻不敢表白,最后被同樣喜歡他的桂花罵走,原來讀懂心事是那樣的重要。在宗利華的《綠豆》中,綠豆很有主見,自由戀愛后馴服著丈夫,完成了期冀她招婿的父母心愿。在湯紅玲的《哭嫁》中,秀秀在家人勸哭而未哭出時,獲悉母親“暈倒”時,她頓時大哭起來,大伙喜笑顏開,道出秀秀是個好女孩。伍中正用農民作家身份傳達出農村的一切,《翻越那座山》里的媒婆注重心靈之美的考察,將自己的女兒許給了請她作介紹的霍。周仁聰在《籬笆墻》、《艷陽天》、《哥哥》、《日子》等中,讓人久久沉浸在作者營造的氛圍里。同樣讓人感動的是陳毓的《雉誘》里有負罪心的雉誘和孫學文的《馬棚》里有情有義的棗紅馬,以及中村的《吃瓜》里外相嚇人的表弟所營造的獨特樸素意蘊。
①劉海濤《微型小說學研究——群體與個性:世界華文微型小說家研究》第98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