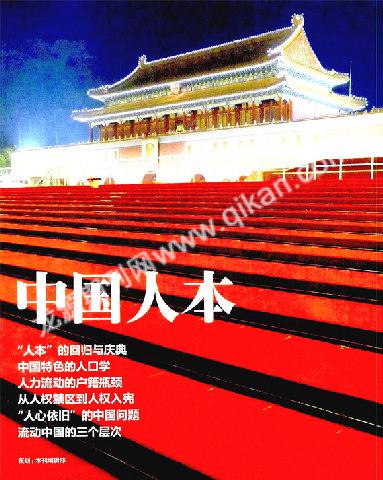“人本”的回歸與慶典
劉 陽
人本主義需要新的回歸,在更高的意義上實現它自身。而這,絕不僅是一個政治命題,人在完整生命意義上所應獲得的解放不可能通過政治行動來實現。
正逢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周年將至,國家諸多建設成果在國內媒體上得到了集中展現。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口號》,匯集了對國家重要領域事務的綱領性表述以及公民應該持有的態度。逐條閱讀,其中,第12條就是——“堅持以人為本,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立國之本在人,一切事業的落腳點在人,回顧與總結60年來新中國在人的領域所走過的道路、取得的進步和積累的經驗,為大寫的“人的未來探索方向,將是國家慶典中最富于意義的篇章。
深入歷史的“人本”
現代政治離不開理念的凝聚和傳播,一種執政理念只有生動凝結為簡潔有力的口號,才能在最大范圍的人群中激起共鳴與相從。通過口號的營銷,滿足與撫慰人群共性的心理需求,不斷喚起水靈靈的新希望,取代枝頭原來那幾片葉子。
2003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上,“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被正式提出,“以人為本”在那個秋天進入了當代中國的政治詞典。
《求是》雜志曾發表文章指出,“我們黨提出的以人為本,不是任何其他理論體系中的命題,而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的命題。”一個政黨的活力就表現在它能不斷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吸收人類社會的一切優秀的文明成果并提出新的時代命題。而命題的有效性不表現在它為某一政黨所特有,而表現在它能最大限度地凝聚人們的普遍共識和正當利益。正因為“以人為本”是一個具有相當普遍意義的命題,超越了狹隘的利益集團訴求,所以獲得了廣泛的認同。
盡管春秋時期管仲早就說過“夫霸王之所以始也,以人為本”;孔子在馬棚失火后問傷人了嗎而不問馬,因為人比馬重要;古希臘的普羅泰戈拉提出了“人是萬物的尺度”,但是,“以人為本”真正具有現代哲學意義、具有社會實踐的可能,要等到近代人本主義的出現。
通常的教科書版本是這樣的:以人文主義思潮興起為標志的歐洲文藝復興,把人對神的崇尚,轉向對人自身的崇尚。這種人文主義思潮所倡導的以人為本位的人本主義,與中世紀的“神本主義”相對應,高揚人的意義和價值。
如上所述,人文主義思潮應是人本主義的母親。但專業研究卻表明,“人文主義”是19世紀杜撰出來的用語,文藝復興時期的人們從未使用過該詞。嚴肅的歷史學家甚至建議刪去冠在許多人頭上的“人文主義者”的稱號,因為他們并沒有一致的哲學主張和政治思想。有限的共識僅僅在于,他們都曾主張越過中世紀,直接閱讀古代經典;而在信仰方面,竟然都相當敬虔。顯然,歷史被人們從當代的興趣出發重構了。
西方哲學史上最重要的人本主義思想闡述者,是費爾巴哈,“人”是費爾巴哈哲學的中心和最高對象,他是馬克思主義人本思想的重要理論來源。然而,19世紀初普遍彌漫的樂觀主義情緒無疑也洗禮了費爾巴哈杰出的頭腦,正是在他以及他的后繼者那里,人為自己加冕,成為自己的主宰,上帝不過是人頭腦創造出來的產物,人自己就是自己的救世主。
“人本”,究竟是以人的理性為本,還是以人的本能為本?^何來的自信,認為自身的理性部分必然戰勝本能沖動?對人自身的頂禮膜拜帶來了對自然對同類的膽大妄為,于是20世紀成為人類歷史上空前黯然的時代。神圣事物被拉下馬后空出來的位置,被一干領袖或野心家覬覦,他們把自己塑造成一尊新神,由這些偉大人物發出的“神圣”號召,開啟了無數噩夢,反思這一切,令人恐懼的不是人的能力不足,而是人的能力沒有了邊界。
清醒的聲音最易被喧囂的時代所忽略。當人們不甘心烏托邦僅僅作為空想和對現實的批判對照存在,不惜代價要把其拉入現實世界的時候,馬克思的同齡人布克哈特卻在1872年預言現代工業與軍事政權的交匯、極權主義對人的控制,終其一生,布克哈特向往的是文化自由自在地蓬勃發展,而從不贊嘆大國專制或是廟堂森嚴。蒲魯東則在1860年預見到了集體大屠殺的出現,只是,有幾個人肯信他?
另一方面,“人本主義”對“神本主義”的驅除并沒有贏得人的全面解放,反而陷入了拜物教的新奴役,也就是說,被人本主義勝利攻占的陣地幾乎一夜之間吊詭地升了“物本主義”的旗號,并開始了空前放肆的狂歡:貨幣成為新宗教,被無數人虔誠地信奉著。消費主義成為比人本主義更誠實的對世界的描述。
新技術是好幫手嗎?
公開承認拜金,因為過于粗鄙而被有教養的人們否認。一個更理性更文明的選擇,是信奉科學的力量。西美爾早就指出,貨幣成了現代社會的宗教。它是承載一切千差萬別事物的等價物,自身卻空無一物。由貨幣激發而壯大的現代精神力量只有一種:理性。科學研究最需要理性、客觀,科學對人類生活的改變力量有目共睹,于是,科學成為一種新信仰,而且是每個人樂于公開標榜談論的信仰。
然而,正如理性本身只是精神手段,要想使這些手段起作用,首先要確定一個目的,而目的唯有意志才能創造。科學同樣如此,它需要目的的引領,更何況,科學無法改變人性。物質的完美永遠無法取代人的完善。
早在19世紀初,正是對科學的迷信,讓法國的孔德天真地預見,現代工業必然要導致消滅戰爭。德國的洛維特在一個多世紀后以遲到的尖銳坦率地指出:“他沒有看到,人在統治自然方面的任何進步,都造成了屈辱的新形式和新程度,所有進步的手段也同樣是倒退的手段。”
對于那些把希望寄托在科學的發展和新技術的出現,以為政治問題可以由技術來解決的人們來說,要接受洛維特的坦率,即使在今天仍然需要一點勇氣。他們最不該忽視的是,在博弈中占據上風的利益集團比弱勢者更有條件和機會掌握新技術、利用新技術,為無人性的技術附加一個意志,設定一個服務對象。技術決定論高估了某一具體的技術手段超越特定歷史與社會語境的可能。
互聯網就是一個近在眼前的例子。人們對它寄予了不切實的厚望,認為它將帶來民主化,這種模式化的思維過于簡單機械了。最典型的言論是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在2000年發表的,他把中國的網絡監管比作“把果凍釘上墻”的徒勞努力;而6年后,連微軟、雅虎、谷歌都不顧國際組織的抗議開始配合政府的網絡審查;9年后的今天,果凍在哪?——在墻上。中國的網絡以防火墻的技術實力傲然于世,在一波波“掃黃”的網絡治理整頓中,人們付出的代價是信息來源多樣性的損失,或許還有現實世界里“小姐”的泛濫。
德魯克說過,效率是把事情做對、做好,而效果是做真正該做的事。科學和技術只負
責解決效率問題,不過問效果。
事實證明,新技術對生活本質的影響被一廂情愿地夸大了。在網絡時代里,沒有網絡,新疆人民一樣生活著,還可能因禍得福:那些讓父母頭痛的網癮少年全都不治而愈。庫爾班大叔究竟是騎毛驢上北京還是坐飛機上北京,只是技術問題,根本不重要。他去北京的目的無非是在精神層面上看望毛主席,在政治層面上反映基層的成績和問題,在經濟層面上希望不要把工程全都包給一小撮人。如果在家門口就能投票表決地方父母官的政績,為什么還要去北京?
技術作為手段,無法救助人本主義的貧困,因為這種貧困是目的論意義上的貧困。
人的空間和前景
在中國,“人本”面臨著疊加因素的多重考驗。在人口、人力、人權、人心幾個層面上,隨著人從生物性的存在、被固定在土地上的低級附屬物,成為具有一定技能、能夠自由流動的經濟意義上的生產要素,到成為擁有完整而立體的權利的政治人、社會人,不再是單向度的經濟動物,最終憑借精神領域的超越追求、作為一只會思想的蘆葦而確立人的尊嚴,不同的人因為迥異的人生際遇而停在不同的階段,每個環節都有痛苦的個體在午夜徘徊不眠。而當個體的自我實現需求與體制性的障礙產生沖突,這種痛苦將成為無所不在的壓抑的來源。
基本的物質匱乏使任何一種理念都顯得虛偽飄渺,個體權利被尊重的程度如果處于一種穩定可預期的狀態中,將大大提高人們心理上的安全感。數億人被一個部門負責按照一個模式教育,不可避免地要以損失文化的創造力為代價,網絡民族主義的泛濫則可被視為這種教育的一個成果。在精神領域,已故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生前一直呼吁——讓宗教團體成為在黨及政府的領導下,在憲法、法律和政策的范圍內,按照自身特點獨立自主地開展工作,享有自身的人事、財務、業務自主權的宗教徒的民間性團體。
“國家”、“國”與“家”之間,以社會化生存為特點的人類,當他/她的社會空間僅僅作為一個消費娛樂場存在著,其權利拓展的可能就被大大削弱了。所謂開放社會,就是要把“人本”的空間嵌入“國”與“家”之間。自2001年戶口制度改革試點以來,幾乎每年核心媒體都會發布有關該領域的全局或地方性改革措施的消息,但回頭看,表面化已經成為戶口制度改革的顯著特色。改革的艱巨性證明,戶口政策絕不僅僅承擔著社會控制的功能,它同時也是資源分配、支撐中國經濟奇跡的基本制度安排,它不只是水閘,同時是一臺水泵。戶口制度是判斷“人本”前景的晴雨表,如果戶口制度最終實現了理想化的目標,那么我們甚至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增長方式,取得了重大進展和根本扭轉。
中國政府1998年就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全國人大常委會迄今尚未批準其生效。公約的簽署,表明了中國政府對國際社會普遍原則的認可和一種積極自信的態度,這是根本性的、原則性的,而公約的批準與實行,不妨被視為是技術性的,需要結合中國國情,權衡實際效果,把握時機,而不淪為表面文章。2003年以來,“以人為本”理念的提出、確立、改善與實踐,無疑為公民權利落地進一步夯實了基礎,營造了氛圍。
中國所面臨的挑戰并不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遭遇類似的問題。天下為公的胸襟、學習的能力與自由的試錯機制,既不狂妄、僭越,又不妄自菲薄,將有助于縮短摸索解決之道的時間。
今天,人本主義被認為具有成為中國各族群共享的核心價值的可能。每一個曾經鮮活具體的概念,都是在諸多限制條件如灰塵般的層層覆蓋之下,在時間的無情流逝中被風干。而根本性的難點還在于終極意義上人本主義面臨的悖論,這是全體人類最終無從逃避的考驗。
正如流行歌曲里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人們通常只有指著更高的事物才有可能起誓立約。“以人為本”就像是一個約定,歷史地看,人類從未實現過,因為這個約定從出現開始就失去了締約的另一方。人人心中都有個魔鬼,如果一切行為都是人自己的選擇、都以人的自身好惡為歸依,人類失去自身之外超越視角的審視,就將最終失去判斷的標準,相對主義的陷阱將使人們不再有能力和信心斷定,哪種做法是不“以人為本”的,從歷史本身無法引申出批判歷史的原則。
人本主義需要新的回歸,在更高的意義上實現它自身。而這,絕不僅是一個政治命題,人在完整生命意義上所應獲得的解放不可能通過政治行動來實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一個國家只有為“人本”核心價值的各種可能釋放最充分的空間,它才能在歷史的夜空中閃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