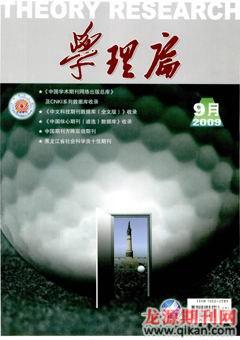論新寫實小說中的后現代主義因素
朱孟剛
摘 要:新寫實小說與現實主義傳統及現代主義文學意識藝術技巧盡管有著這樣那樣的相似之處,但它更多的是呈現主體消解、平面化、多元性、不確定性等傾向,體現出一種后現代主義價值立場和審美趣味。
關鍵詞:新寫實小說;后現代主義;消解;原生態;零度敘事
中圖分類號:I054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2-2589(2009)23-0096-02
后現代主義是二戰之后發源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一種社會文化思潮。它是對現代主義的一種反動,也對現代主義的一種繼承和超越。后現代主義作為一種有影響的思潮,對文學領域也有著重大的影響,它否定作品的整體性、確定性、規范性和目的性,主張無限制的開放性、多樣性和相對性,反對任何規范、模式、中心等等對文學創作的制約,甚至試圖對小說、詩歌、戲劇等傳統形式乃至“敘述”本身進行解構。具體來說,它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具有極強烈的世俗文學傾向。第二,反叛傳統,消解中心。第三,重視個體的生命體驗,它注重展示主體生存狀況,認為世界是荒謬無序的,存在是不可認識的。
在20世紀八十年代前后,后現代主義很快成為熱點,達到了鼎盛時期,并迅速波及到全世界。當然,后現代主義也波及了我國的思想文化界,尤其是我國的文藝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后現代主義在西方漸趨沉寂的時候卻在我國形成了蔚為壯觀的景象,并對文學領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我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來的新寫實小說,就是較有代表性的中國后現代主義文學文本。
新寫實小說發端于1987年的《煩惱人生》和《風景》。隨后,《單位》、《一地雞毛》、《伏曦伏曦》等作品相繼涌現。這些風格相近的小說的面世,使得新寫實小說在文壇上占據了比較顯眼的位置。而池莉、方方、劉震云、劉恒等青年作家也就成為新寫實小說的中堅力量。這些作家雖然沒有象尋根小說家們那樣提出明確而響亮的理論主張,但他們的作品卻具有共同的審美特性,如對人們生存狀態生存本相的高度關注;對細節真實的重視以及零度情感的敘事方式等。這些文本特征使得新寫實小說具有了后現代主義烙印。
盡管新寫實小說與現實主義傳統及現代主義文學意識藝術技巧有著這樣那樣的相似之處,但它又不同于以往的現實主義文學,既沒有批判現實主義的犀利解剖,也沒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澎湃激情,它更多的是呈現主體消解、平面化、多元性、不確定性等傾向,在很大程度上表現了與“后現代主義”思潮相通的美學趣味和價值立場。下面我們就從審視對象、敘事方式、藝術色彩等方面來分析一下新寫實小說中后現代主義因素。
一、人物主體意識的消解
在對人本體認識的問題上,歷代文學都把人當作世界的中心、歷史的主體。而到了后現代主義那里,“個人不再有反抗異化和逃避痛苦的承諾,現實異化和精神分裂成為人的本然處境,個人既不需要反抗異化的能力,也沒有抵御痛苦的必要。”新寫實小說正是如此,作品中的“英雄人物”讓位于平凡的小人物。著力描寫在艱難困苦中的聲聲不息的平民百姓,表現他們的人生際遇和心理歷程。無論是《煩惱人生》中的印家厚,《一地雞毛》中的小林夫婦,還是《艷歌》中的遲欽亭、沐嵐,他們都是下層社會或市井中的平凡一員,他們所惟一執著專注、費盡心力去應對的,是瑣碎而世俗的生活。
人物主體意識的消解導致了人物形態的類象化。傳統現實主義文學注重塑造典型人物,側重于強調人物鮮明獨特的個性,然而新寫實小說中的人物卻皆是一種類型化的人物。印家厚、小林、遲欽亭等人物幾乎可對換生存位置而不影響作品意義和故事框架,他們的生活方式、生活欲求乃至處世原則都是雷同的。最為典型的是劉震云小說中的一系列“官人”形象:老張、老孫、老袁、老方、老趙、老劉……正如其稱呼的無個性、無特色一樣,他們的性格特征、思維方式毫無二致,全是“官場”這個大模具所復制出來的同一類“官人”,只因為官位的不同而有著不同的官腔,說著不同的官話。小說展示了具有同一種情致的群像,卻因為人物缺乏特殊個性標識而無法彼此區別開來。這里呈現出弗里德里克·杰姆遜所說的后現代“類象文化”的特征。在以消費主義為意識核心的機器復制時代,都市精神生活呈現出嚴重的商品化傾向,人們的情感、氣質都像商品一樣可以批量上市,規格、功能具有同一性。
二、描摹原生態的生活,注重細節的高度真實
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一直被傳統的現實主義視為圭臬,而新寫實小說家們卻拋棄了這一創作原則,不再信奉“文學來源于現實生活而又比現實生活更高、更美、更理想”這一信條,致力于表現日常生活的庸常和瑣細。在對待“真實性”這一問題上,現實主義強調經過典型化處理的“真實”,現代主義則側重主觀的、心理的“真實”,而新寫實主義作家力戒粉飾、加工、變形和夸張,他們相信原生態的生活景觀,是最“真實”的生活場景。他們的創作指向不是對生活進行典型的充分的開掘與描寫,而是盡力再現一個又一個生活過程和生存狀態,不加修飾的原汁原味的還原凡人俗事,從現實主義的理性開掘與深化轉向生活的原生態與刻骨的真實,從而達到消解文學與生活二元對立的目的。
曹文軒說:“新寫實主義者試圖以其作品證實:現實主義(傳統現實主義——筆者注)目光短淺將輕重顛倒了,事實上是‘雞毛(劉震云《一地雞毛》——筆者注)最重——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人們絕大部分時間,沒有機會接受什么重大事件或參加什么重大活動。……人生之難之痛苦,是在綿綿的日常生活中得到體現的。生活所具有的重量。”的確,社會生活中絕大多數的人都不是生活中力挽狂瀾的英雄,而是普通的小人物,是小人物就要面對庸俗瑣碎的日常生活,就要面對生活的煩惱,然而這日常的煩惱又是何等的沉重!“人生三部曲”寫了戀愛、結婚生子和婚后育子等幾乎是一個人一生的煩惱、無奈和沉悶。人生煩惱的根源又在哪里?從池莉的小說中我們看到的答案,一是現實中國社會物質貧困的現狀,二是人們難以滿足的欲望,二者的對立是不可調和的,這種不可調和性構成了人的尤其是小人物的生存困境,給人的心靈蒙上了一種無法言說的凄楚和疲憊不堪的無奈,這就是生活的“原生態”,生活其中的人對其艱難性有切膚之痛。這實質上是池莉對“原生態”生活深切體驗的藝術呈現,也是后現代主義在新寫實小說中的藝術體現。
另外,在對小說細節的處理問題上,也體現了后現代主義的特征。傳統現實小說對細節的選擇加工往往刪除、抹掉一系列不需要的細節,從而塑造典型環境下的典型人物。這種選擇加工是作家主體根據自己的審美態度和作品所要表現的特定意蘊來進行“去粗取精”的,生活本身固存的、然而對作家主旨無關的所謂“枝蔓細節”都被毫不猶豫地砍掉了。新寫實小說家卻并不回避對瑣碎生活細節的描寫,把傳統現實主義作家不屑表現的“一地雞毛”般的小事——買豆腐、趕早班、捅爐子、接送孩子、迎送客人等等一一不加選擇、不加修飾地搬進小說。這樣就使得“文學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這種二元對立關系消解,文學幾乎等于生活本身。作家主體意志也在文學與生活一元化的轉折中悄然隱退。
三、運用零度敘事法展開敘述,完全淡化價值立場
“零度敘事”就是作家在創作時將自己主觀情感控制在零度,冷漠而不動聲色地呈現生活的原生態。他們從不主宰人物的命運,從不顯現自己的感情色彩,他們不再試圖以高昂的熱情改變現實,也不想以激憤的語言抨擊丑惡,只是對正在發生的生活進行冷眼旁觀,默默地抒寫著普通人的苦難生活,表現著生活的難以撼動。文學不再是生活的教科書,它與世俗同呼吸、共命運。
所以,無論是劉震云的《一地雞毛》,還是池莉的“煩惱三部曲”,或是方方的《風景》,高揚主體精神的價值立場已經消失了,小林的價值觀、印家厚的“生活如網”、七哥的冷酷玩世的人生哲學,作家們都不加以評判。或者稱之為“中止判斷”。正如評論家王干在《近期小說的后現實主義傾向》一文中所指出的“取消對生活的種種主觀臆想和理念構造,純粹客觀地對生活本態進行還原,在還原過程中,作家要逃避自己的意識判斷、理性侵犯。”而這種零度情感的敘事,在《風景》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不僅僅是敘述視角的獨特能反映出作家情感的控制,就從新寫實小說題目我們也能感受到這種風格來。池莉的《不談愛情》《熱也好冷也好活著就好》、諶容的《懶得離婚》等這些題目本身在那些滿懷豪情地進行著宏大敘事的作家們看來是不可想象的。
當然,這種零度敘事不是作家們的率性所為,它的出現有著深層次的緣由。新寫實小說誕生于八十年代末,隨著經濟改革體制的縱深推進和商品意識的日漸抬頭,整個社會走向世俗化,人們從理想與浪漫的云端跌回到凡俗的現實中。同樣,作家身上的啟蒙熱情也就難以被調動起來。過去在作品中所體現的“我們改變世界”的狂想被現在的“世界改變我和你”的現實所替代。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新寫實小說家們的零度敘事態度是對文學啟蒙原則的質疑。同時也表現了作家們對當下生活的失望情緒。
從根本上說,新寫實小說秉承了后現代主義的懷疑論,對人主體精神價值、作家權威意志采取徹底否定態度,不再從作家中心觀念體系出發來建構充滿烏托邦沖動的精神世界,而是直面無體系、無中心、碎片化的現實生活,以不加選擇的、零散化的敘事方式展示無序的平面化的“生活原生態”,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更能把握人類生存的真實狀況,表現在理想、理性光輝掩蓋下“小寫的人”的原色人生。
同時,由于所指一元化消解,能指呈現多元化傾向,文本同生活本身一樣具有了多種解讀的可能性,讀者對文本解讀的能動性得到極大張揚,這樣一來,“讀者和文本間激起了無止境的對話”(斯潘諾斯語),文學更能適應大眾不同層次的精神需求。但從另一方面來看,新寫實小說對于主體性的消解使它本身消減了價值深度,不能承擔起建構人類精神家園的文學功用,讀者難以從中獲得更為高尚脫俗的精神啟示,它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的衰落終是不可避免的。
參考文獻:
[1]王岳川.后現代主義文化美學景觀[J].北京大學學報,1992,(5).
[2][3]曹文軒.中國二十世紀末文學現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3).
(責任編輯/石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