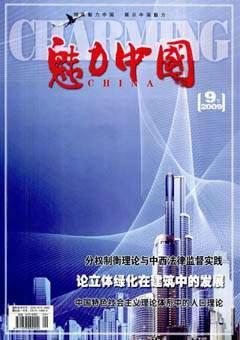論選擇性罪名的罪名確定
謝祎青
筆者在工作中遇到這樣一則案件,簡要案情是:公安機關從被告人趙某某的住處查獲1支以火藥為動力發射彈丸的槍支及1發子彈,趙某某自供該槍支和子彈系從他人處購得,用于防身。本院以非法持有槍支罪對被告人趙某某提起公訴,后法院認定了本院指控的事實,但以非法持有槍支、彈藥罪定罪。
本院的指控和法院的判決中對于事實的認定是一致的,但在定性上卻存在分歧,本院認為被告人趙某某的行為構成非法持有槍支罪,理由是根據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構成非法持有彈藥罪需“非法持有軍用子彈20發以上、氣槍鉛彈1000發以上或者其他非軍用子彈200發以上”,而本案中,被告人趙某某非法持有的子彈未達到數量要求,因此不構成非法持有彈藥罪。法院的判決中認定被告人趙某某的行為構成非法持有槍支、彈藥罪,其理由應該是非法持有槍支、彈藥罪是選擇性罪名,選擇性罪名是不需要數罪并罰的,因此行為人若實施了選擇性罪名中的數個危害行為,雖僅有一個危害行為構成犯罪,但在確定罪名時應以行為人實施的全部危害行為為準。
將上述的分歧抽象出來就是,選擇性罪名中,不同的危害行為是否必須達到各自的定罪標準才能予以認定。從量刑角度看,這種分歧一般不會影響對被告人的量刑,但筆者認為消除該分歧對于司法實踐有重要意義。因為,該分歧造成的問題不在于是否會給被告人的量刑帶來不利影響,而是會導致定罪不準確,造成司法的不統一。定罪是指司法機關依據事實和法律認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以及構成何種犯罪的活動。定罪的作用不僅是為量刑奠定基礎,其核心作用是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處罰,實現刑法的保障機能。而定罪作用的充分發揮,最為關鍵的是正確定罪,特別是司法機關要統一認識,對相同的行為作出相同的認定,否則刑法的保障機能無從談起。
針對上述分歧,筆者同意第一種觀點,具體分析如下:
首先,從選擇性罪名可以分解為數個獨立罪名的特征分析。所謂選擇性罪名是指一個法律條文規定有兩個以上有密切聯系的犯罪行為或犯罪對象,司法人員在具體定罪時,既可連用,又可分解使用,而不實行數罪并罰的罪名。1選擇性罪名具體說來有以下幾種情形:第一,行為對象相同,行為方式不同,不同行為方式可以分解拆開作為不同的罪名。第二,行為方式相同,但行為對象不同,根據不同對象,可以定為不同罪名。第三,行為方式和行為對象均可以選擇,這也叫雙重選擇。
據上所述,一個選擇性罪名可以分解為數個獨立的罪名,行為人只實施其中的一個危害行為,則僅以該危害行為定罪處罰。此時,行為人實施的該危害行為必須達到刑法或相關司法解釋規定的定罪標準,否則不構成犯罪,這是毫無疑問的。對本案稍作改動,若公安機關僅查獲被告人趙某某僅非法持有1顆子彈,趙某某的行為則不構成非法持有彈藥罪。再回到本案,也就是說趙某某同時持有1支槍支和1顆子彈,因趙某某非法持有槍支的行為已符合定罪標準,構成非法持有槍支罪,那持有的1顆子彈也由此而構成犯罪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因為,非法持有槍支和非法持有彈藥其實是兩個獨立的危害行為,評價一危害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只能是該危害行為本身是否符合刑法的規定,而再無其他標準。若認為本案中趙某某的非法持有1顆子彈的行為構成非法持有彈藥罪,就會導致對同一危害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有不同結論,這顯然違背了定罪的平等原則。平等原則的基本內涵是“同樣情況同樣對待”,這一原則適用于定罪活動,即是要求對同一危害行為是否構成犯罪以及構成何種犯罪的結論要求一致,不能受其他無關因素的影響。
概言之,將選擇性罪名分解為獨立罪名時,不同的危害行為只有達到定罪標準才能構成犯罪,基于這個前提,行為人同時實施多個危害行為,合并以一個選擇性罪名定罪處罰時,各個危害行為同樣需要達到定罪標準。
其次,從選擇性罪名不實行數罪并罰的特征分析。刑法理論的通說認為,選擇性罪名作為特殊的一罪,不實行數罪并罰,即行為人實施某一選擇性罪名包含的全部犯罪行為,不按照各個犯罪行為單獨定罪,而是合并認定為該選擇性罪名,且作為一罪處理,不數罪并罰。選擇性罪名不實行數罪并罰是產生第二種觀點的理論前提,換言之,若需數罪并罰,就會導致加重被告人的刑罰,此時認定被告人的行為構成犯罪需充足的理由。以本案為例,若認定被告人趙某某的行為構成非法持有槍支、彈藥罪,且以并罰處理,則會加重趙某某的刑罰,若趙某某抗辯其持有1顆子彈并未達定罪標準而不構成非法持有彈藥罪,此時,司法機關無法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相反,僅因為對選擇性罪名不實行數罪并罰,即使認定趙某某的行為構成非法持有槍支、彈藥罪,并不會由此加重趙某某的刑罰,這就使得該種做法貌似正確。
為此,需要對選擇性罪名不實行數罪并罰的理由作深入分析,使人們對其理論依據有正確的認識。我國刑法學界普遍公認,犯罪構成是區分一罪與數罪的標準,犯罪事實具備一個犯罪構成的為一罪,具備兩個以上犯罪構成的為數罪,具體地說,行為人以一個或概括的犯罪故意(或者過失),實施一個或數個行為,符合一個犯罪構成的為一罪,以數個犯罪故意(或者過失)實施數個行為,符合數個犯罪構成的為數罪。2犯罪是刑罰的基礎,刑罰是犯罪的后果,一人犯一罪,以一罪論處,是毋庸置疑的,而一人犯數罪,通常需數罪并罰,這也是數罪的應有之義,但也有依一罪處理的例外,比如牽連犯、想象競合犯等。選擇性罪名可以分解為數個獨立罪名使用,行為人分別僅實施其中一個犯罪行為,可以分別構成不同的犯罪,而行為人同時實施該罪名所包含的所有犯罪行為,也僅構成一罪。從形式上說,這其實是有違犯罪構成理論的,但刑法既然作出如此規定,我們必須探究該規定背后的實質性理由。筆者認為,回答這一問題,需要深入到選擇性罪名所包含的各個危害行為之間的特殊關系這一層面。對此,筆者作出如下分析3:其一,對于行為方式選擇的選擇性罪名而言,其數個行為方式經常并發出現,數個危害行為之間有手段和目的的關系,比如走私、販賣、運輸毒品行為,行為人從境外走私毒品入境,一般需要運輸毒品,而后將毒品賣給他人;其二,對于對象選擇的選擇性罪名而言,數個犯罪對象之間經常連帶出現,有時此犯罪對象是彼犯罪對象存在的前提。比如,非法持有槍支、彈藥罪,行為人非法持有子彈一般是為了配合槍支進行使用。正是因為選擇性罪名中的數個危害行為之間具有特殊的關系,行為人同時實施全部危害行為也只構成一罪具有了實質合理性。這也體現了我國刑法所倡導的謙抑性原則。
刑法的謙抑性,有學者認為,是指立法者應當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或者不用刑罰,獲取最大的社會效益——有效地預防和控制犯罪。4根據謙抑性原則,對于那些具有并發性或連帶性的危害行為,應盡量少地設置罪名,否則行為人若同時實施多個該種危害行為,會造成罪名繁多且刑罰過重。試想,行為人同時實施了偽造國家機關公文、偽造國家機關證件和偽造國家機關印章三種行為,若不將該三種犯罪行為設置為一個選擇性罪名,則被告人的行為就構成了三個罪名,應該三罪并罰,這就加重了被告人的刑罰。因為,被告人雖然同時實施了該三種犯罪行為,但它們是統一于一個犯罪目的之下的,而且是經常連帶性出現的:偽造公文,自然需要偽造印章,而使用偽造的公文時,也需要偽造相應的證件。為此,立法者設置選擇性罪名來解決這類問題,即可將選擇性罪名依據行為人實施的行為分解使用,也可合并為一罪使用,這不僅能做到嚴密法網,有效懲罰犯罪,還能做到不過分加重行為人的刑罰。
概言之,選擇性罪名名為一罪,實為數罪,不實行數罪并罰只是刑法為嚴密法網,又體現刑法的謙抑性而作出的特殊規定,行為人實施數個危害行為而以選擇性罪名定罪處罰時,各個危害行為均需達到定罪標準。
最后,筆者進一步作了思考,認為有必要在刑法總則中明確規定對實施選擇性罪名中多行為的犯罪人從重處罰。一般而言,數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明顯大于同種一行為的社會危害性,例如,行為人僅持有槍支的行為與同時持有槍支和子彈的行為相比,后者的社會危害性肯定大于前者。根據罪刑相適應原則的要求,應對實施選擇性罪名中數個犯罪行為的行為人判處比實施其中之一行為的行為人更重的刑罰。但是,一個選擇性罪名只有一個與之相對應的法定刑,無論是行為人實施選擇性罪名中的一個行為還是數個行為,司法機關都只能適用該法定刑,這就會出現行為人實施數個行為與實施一個行為可能處以同樣刑罰的結果。為了使處罰結果更加符合罪刑相適應的原則,在不實行數罪并罰的前提下,適用以一罪從重處罰的方法來處理就顯得比較恰當。而要實現這一要求,就有必要在刑法總則中明確規定對實施選擇性罪名中多行為的被告人從重處罰。
1 李永升:“我國刑法中的選擇性罪名”,載《云南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
2 參見馬克昌著:《犯罪通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617頁。
3 筆者對選擇性罪名中各個危害行為之間關系的分析,是以典型的選擇性罪名為基礎的,對于司法解釋確定的其他非典型選擇性罪名是否具有這種關系,不在本文評析范圍之內,比如,盜竊、搶奪槍支、彈藥、爆炸物罪中,盜竊、搶奪系兩種獨立的危害行為,并不具有如本文所說的并發關系,司法解釋將該罪名確定為選擇性罪名是值得商榷的。
4 參見陳興良著:《刑法的價值構造》,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53頁。
(作者單位:下城區人民檢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