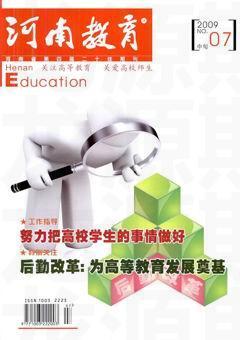從安全與發展的視角看新中國建設道路
王傳利
在近現代世界歷史上,人類經歷的三次科技革命為人類社會發展帶來了契機,但并不是任何一個國家都能全力以赴地投入到這些科技大發展中。被壓迫民族和被侵略國家實現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僅僅意味著它們獲得了社會政治經濟建設的起點,并不意味著它們獲得了國家建設的安全保證。處于資本主義國家軍事包圍、封鎖、脅迫中的社會主義國家無法正常地發展,無法自由地吸收世界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成果,也不可能自由地與外界進行互通有無、取長補短的交往與合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很想立即一心一意地領導人民從事大規模社會經濟建設。毛澤東在寫《論聯合政府》《新民主主義論》時,已經有一個建設國家的構想。1949年9月21日,毛澤東在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的開幕詞中說:“全國規模的經濟建設工作業已擺在我們的面前。”同年9月30日,毛澤東為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起草的會議宣言中說,人民政府“將領導全國人民克服一切困難,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掃除舊中國留下來的貧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但是,新中國不得不面對這樣的國際格局:“二戰”后形成的美蘇兩大陣營對峙,中國正處于雙方在亞洲對立的最前沿,國家建設受到美蘇關系變動的影響,不可能完全擺脫大國紛爭狀態的干擾。當時,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面臨著雙重任務:一方面要積極進行國家建設;另一方面要英勇抗爭危害國家安全的帝國主義、霸權主義,謹慎地為國家的社會經濟建設尋求安全的國際環境。所以,當時的國家建設一波多折,舉步維艱。
一
新中國建立之初,百廢待興。毛澤東用兩個多月的時間訪問蘇聯,就是為即將開展的大規模的國家建設尋求安全環境和經濟技術支援。在中國與西方國家對立狀態難以改變的情況下,毛澤東采取了“一邊倒”的政策,在社會主義陣營里尋找朋友,使得當時的中國獲得了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的援助:一批大型建設項目奠定了新中國工業化的基礎;獲得了對于中國人民來說極為寶貴的建設經驗;中國獲得了北方數千公里的安全邊界。一個人口最多的國家和一個面積最大的國家聯起手來推動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
1950年開始的抗美援朝戰爭,是美國侵略者強加給中國人民的。中國人民正在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之際,美國武裝侵略朝鮮,侵入我國臺灣,派飛機轟炸我國邊境城市丹東、寬甸、輯安等,矛頭直指鴨綠江邊。我國是在國家安全受到嚴重威脅的情況下被迫出兵的。從1950年10月19日始,抗美援朝歷時兩年半。中國人民為了打贏這場戰爭,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戰爭開支是62億元,相當于1950年工農業總產值的1/9。幾乎在抗美援朝的同時,中國不得不抗法援越。中國在國內經濟條件十分困難的條件下,采取節衣縮食的辦法,從1950年4月起在全國范圍內籌集了大量的武器裝備和各種軍需物質,源源不斷地運往越南,支援胡志明領導的越南革命。
由此可以想象,一個剛剛獲得全國政權、有了建設國家藍圖、急需國際援助的國家不得不卷入戰爭,意味著什么?用來改善人民生活和用來投資文化設施及經濟建設項目的資金本來就十分短缺,捉襟見肘,反而被抽出相當大的一部分作為戰爭費用,我國的社會經濟建設受到了很大影響。但是,如果沒有民族獨立和國家安全,國家建設就是一句空話。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同仇敵愾,勝利地完成了這些重大歷史任務。到1953年初,在國民經濟完成恢復的基礎上,我國進入了經濟建設和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改造的新階段。
二
經過抗美援朝和抗法援越,中國迎來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比較愜意的時期。1955年的萬隆會議上,中國的和平外交政策獲得了極大成功。隨后,中美兩國開始對話,盡管是在低層次上。我國周邊關系得以迅速改善,出現了有利于中國發展的國際形勢。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敏銳地抓住有利于中國發展的時機,及時調整國內政策,加快實施國家工業化的發展目標和國際發展戰略,對工業布局、發展速度提出新的看法。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論十大關系》,其中的一段話說:“過去朝鮮還在打仗,國際局勢還很緊張,不能不影響我們對沿海工業的看法。現在,新的侵華戰爭和新的世界大戰,估計短時期內打不起來,可能有10年或者更長一點的和平時期。這樣,如果還不充分利用沿海工業的設備能力和技術力量,那就不對了。不說10年,就算5年,我們也應當在沿海好好地辦4年的工業,等第五年打起來再搬家。”這篇文章中,毛澤東還講到調整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的比例,把軍政費用降低到一個適當的比例以省出更多的資金用于經濟建設等。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知識分子工作會議,周恩來傳達和闡述了毛澤東關于“向科學進軍”的指示,提出制定1956年到1967年我國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的任務。周恩來指示規劃委員會的負責同志,要盡量瞄準當代世界的新興科學和技術,采用世界的先進技術,不失時機地迎頭趕上。按照“重點發展,迎頭趕上”的方針,圍繞今后10年左右經濟建設各方面的需要,我國提出了57項重要的科技研究任務、600多個研究課題,確定了包括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超高頻技術、電子計算機、噴氣技術、自動化和精密儀器技術、新冶金技術、主要疾病的防治和治療、資源勘探、新型動力機械和大型機械等項目。1963年,國家對規劃項目的執行情況進行了全面檢查,結果顯示絕大多數科研項目都已完成,并且已經應用到生產建設中。我國整體科學技術的發展大大縮小了同世界先進科學技術的差距。科研規劃任務的完成也解決了第二和第三個“五年計劃”中國家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迫切需要解決的一些科技問題,填補了我國科學研究領域一些技術項目的空白,加強了某些重要基礎學科的研究實力,發展了一批新興科學技術。比較突出的是我國實現了石油自給,在原子能、火箭技術上的重大突破也使我國有了原子彈、氫彈的成功爆炸以及導彈、人造地球衛星的成功發射。
天有不測風云。世界局勢沒有留給社會主義新中國進一步安心從事建設的時間,陰云重新籠罩了中國。在20世紀60年代,我國安全問題方面發生了三個重要事件:一是1964年美國借口“北部灣事件”轟炸北越;二是蘇聯大肆反華;三是1962年中印邊境發生大規模軍事沖突。關于這段歷史,鄧小平1989年對來華的蘇聯領導人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不久,中國的革命戰爭取得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不侵略別人,對任何國家都不構成威脅,卻受到外國的威脅。”復雜的國際環境,險峻的周邊環境,影響了我國的經濟布局、積累與消費比例的安排,使得中國人民無法按照經濟規律發展。在安排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我國將“吃穿用計劃”調整為“戰備計劃”,暫時中止進一步調整重工業超前增長發展戰略的既定部署,重新優先考慮國家安全。1964年5月的中央工作會議鄭重提出制訂經濟計劃要考慮戰爭因素,要進行一、二、三線戰略布局。其實,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里已經有了“省下軍政費用、增加經濟建設費用”的主張。第二個五年計劃里,軍政費用占到總開支計劃的17.7%。但20世紀60年代國際局勢緊張后,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軍政開支提高到27.2%,其中,1964年達到32.5%。軍政費用的增加主要是國防費用的增加,這就必然擠掉一部分對經濟建設的投資。
當時,援外也是我國國家防務的特殊部分。中國人民不能分享人類文明發展的成果,從外部獲得豐富的物質支援,反而要拿出稀缺的資金和并不富裕的物質資源支援世界被壓迫人民的革命斗爭。如1967~1972年援外數額是1950~1966年的3倍多。那時,我國經濟發展還很落后,如1965年和1972年的人均國民收入分別是194元和248元,所以人民生活受到了很大影響。在如此艱難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充分利用世界大變局的形勢,在國際社會中積極尋找發展社會主義中國的出路和機會。
三
20世紀70年代,世界醞釀著新的變局,國際政治經濟的各種力量呈現重新組合的態勢,為中國的發展提供了難得的契機。西方國家在經歷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有恢復性質的高速經濟擴張以后經濟發展緩慢下來。1971~1972年,西方國家出現了程度不同的經濟衰退,以至于出現了1973年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美蘇爭霸的態勢朝著有利于蘇聯的方面發展。美國在世界布兵設防力不從心,尤其是在越南戰爭中元氣大傷。國內經濟陷入嚴重的“滯漲”、急于從亞洲脫身的美國,迫切需要中國這一戰略力量來抵制蘇聯對美國霸權地位的挑戰。1968年9月,在獲得總統提名以后,尼克松接受雜志專訪時明確地說:“我們必須不忘中國。”高瞻遠矚的毛澤東立即意識到尼克松上臺后中美關系的變化。1972年尼克松訪華,中國和美國兩個國家由對抗重新走在一起,掃除了中國與西方經濟技術交流活動中的一個重大障礙。
20世紀70年代,中國共產黨抓住有利時機,為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拓展外交空間。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多數票通過了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由于恢復中國在聯合國里的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合法席位,中國在法律上成為少數幾個為世界安全負有責任的大國之一,極大地提高了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發言權。在法理意義上,中國可以在聯合國與國際上的大國一起平起平坐地討論國際問題了。這是中國人民在國際舞臺上站起來的標志。
開啟中國與西方國家經濟技術合作的大門并非自20世紀70年代始。早在1964年1月,中國就與法國建交,這對于中國加強同西歐的關系是一個重大的突破,對美國孤立中國的政策是一個沉重打擊,開辟了中國同西歐開展貿易往來和經濟技術交流的一條道路。1963~1966年中國先后與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瑞典等簽訂了總價值為2.8億美元的80多項工程與項目。1973年的石油危機宣告了戰后西方“黃金時代”的結束,誘發了世界性通貨膨脹,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體系從此瓦解。這種世界變局為中國發展提供了機會。中國抓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急于尋找出口市場以擺脫經濟危機、貿易條件比較有利的機會進口國內迫切需要的設備,擴大經濟交流。1973年1月,毛澤東批準了進口約43億美元的設備、技術的方案。不久,又陸續追加一些項目,總額為51.4億美元。這是繼20世紀50年代大規模進口蘇聯技術設備以后的又一次大規模引進技術設備,反映了國家加強農業和輕工業以滿足人民吃、穿、住、用需要的政策走向。
有學者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意義已經超出中國的地域。社會主義中國打破了雅爾塔會議上的“世界三大戰爭巨頭”分割世界的政治版圖,鼓舞了第三世界被壓迫民族的崛起,從而使世界走向三極化。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成就激勵下,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人民以武裝斗爭和政治斗爭摧毀了16世紀地理大發現以來已經發展數百年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接管的是一個經歷了多年戰亂、危機、極其落后貧窮的中國。新中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頂住了國際壓力,奮發圖強,在險峻的國際環境中摸索實現國家工業化的道路,并且終于初步實現了社會主義工業化,成就輝煌。他們的努力為把我國建設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作者系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
責編:思 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