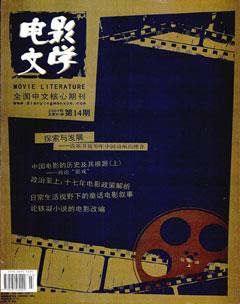論鐵凝小說的電影改編
胡景敏
[摘要]鐵凝的小說情節單純,境界淡遠、空靈;同時又意蘊豐富,不乏思想的穿透力。改編者一方面用電影語言準確傳遞原作的神韻,創造出電影的詩意美;另一方面把經文字含蓄表達的思想轉化為可以直觀的影像;凸顯并豐富了原作的意旨。
[關鍵詞]
鐵凝;小說;電影改編
一
盡管鐵凝對把自己的作品搬上銀幕并不積極,但她還是有著“無法逃避的好運”。其小說創作以獨有的魅力受到電影人的由衷喜愛,多次被改編:中篇小說《沒有紐扣的紅襯衫》改編成電影《紅衣少女》(1984);中篇小說《村路帶我回家》改編成同名電影(1988),鐵凝自任編劇;短篇小說《哦,香雪》改編為同名電影(1989),鐵凝擔綱編劇;短篇小說《安德烈的晚上》改編為同名電視電影(2001)。
其實,把鐵凝的小說改編成電影是有難度的,存在一定的藝術風險。大凡讀過她作品(尤其是短篇小說)的人都會產生這樣的感覺:她的小說情節單純,意蘊豐富,境界淡遠、空靈,透出一種自然、樸素的美;很多作品與其說是小說,還不如說是帶有濃濃詩意的散文。當然,這也正合于她本人對小說的理解,她說,短篇小說展開的是景象:中篇小說講述的是故事;長篇小說追問的是命運。鐵凝的創作深得“荷花淀派”的神韻,她的小說表現出散文化詩化的特點。她在創作中不屑于經營一個緊張曲折、沖突尖銳的故事,而是堅持有耐心地寫出“思想的表情”,發掘出人的精神深度。因此故事在小說中往往被處理成淡淡的一條線索,簡約、含蓄、瑣細。在飄忽的故事主線周圍,作者卻不惜筆墨通過一個個場景的描繪寫出人的生存狀態,寫出人與外界的關系。如果說在中篇小說創作中,作者還抑制著自己的詩情,努力講出一個故事,那么在短篇小說中,她確實僅僅描繪了一個景象、一種狀態,故事只是停留在似有似無之間。因為不具備一般電影所要求的矛盾沖突和鮮明突出的人物性格,所以改編鐵凝的中短篇小說對創作者而言無疑是一種嚴峻的考驗。《紅衣少女》導演陸小雅在事后總結時說:“這是一篇多么不容易改編的作品啊!我怎么會那么執著地把它搬上銀幕呢?我有些后怕了,這是件冒險的事情啊,當時我的自信是從哪來的呢?”《哦,香雪》的導演王好為在“導演隨筆”中也表達了創作前的擔心:“我向往了很久的人物和生活,一下子又覺得平凡、樸素得說不清、抓不住了。”可見,這是改編者的同感。但是小說的藝術魅力還是誘惑她們去勇敢嘗試,在克服困難中獲得藝術創造的愉悅。
顯然,她們需要共同面對三個問題:第一,如何充實小說內容,使原本單薄的情節豐富起來,但又不破壞作品的整體格調;第二,如何用電影語言準確傳遞原作的精神內涵,把經文字含蓄表達的思想轉化為可以直觀的影像:第三,如何在電影散文美的追求中避免生活細節的碎片化,做到“散而有骨”。應該說,她們獲得了成功。
二
《沒有紐扣的紅襯衫》出現在思想活躍的1980年代中期,通過中學生安然對自我的追求,既表現了一個少女的成長,也對青年追求自我的舉動做了多側面的反思。
《紅衣少女》的創作者正是看重了小說這一點,在改編中努力突出安然自我追求的社會思潮意義。在原作中,姐姐安靜既是小說中的人物,又作為第一人稱敘述人對故事發展加以評判,她猶豫徘徊在追求自我和遷就社會之間,她的價值世界和日常生活世界是分離的、矛盾的,她為此感到痛苦,這些引發她不斷的自問和思索。安靜的自問和思索正是小說思想魅力的源泉,但是改編者為了追求電影自我尋找主題的明朗性,放棄了第一人稱視角(即安靜的視角),而改用全知視角,原作中帶有安靜色彩的限知敘述轉化為客觀敘述。電影劇本按照時間順序,再現了主人公安然評“三好”的1l天生活。以及由她輻射出的周圍的人和事。電影中的安然是個16歲的女中學生,姐姐給她買了一件沒有紐扣的紅襯衫,她非常高興。但她也有煩惱,最怕學期末的評“三好”。安然最終評上了“三好”,但當她得知這是姐姐和韋婉交易的結果,她毅然退掉了“三好”。她感到迷惘、孤獨、困惑。這是一個少女的成長,但成長的方向在哪呢?是堅持走自己的路,努力地尋找真正的自我,結果或許會像爸爸那樣一輩子苦苦追求,畫出那么多不被人賞識的畫?還是向環境臣服,把自我掩藏,做一個俗氣市儈的韋婉,或者做一個被環境熏染過于早熟、虛偽的祝文娟?是像媽媽那樣經過挫折再去領教命運的厲害,總結出自己的處世哲學?還是像姐姐那樣生活在價值世界和日常生活世界的分裂中?這是安然的問題。很顯然也是我們的問題。
《紅農少女》保留了小說的基本故事框架,但是也做了很多的改動、豐富和補充。比如小說中姐姐雖然做了努力,但安然還是沒有評上“三好”。在電影中改動為安然評上了“三好”但最終放棄了。而且電影增加了對評“三好”過程的詳細描繪。這一改動有力地說明了安然不向異己的環境臣服的姿態。電影還增加了較多由小說邏輯延伸出的情節。例如,童年安然在農村大道上奔跑,安然和因家庭貧困輟學的米曉玲在學校告別:安然在白楊樹路上看“眼睛”;姐妹間因評“三好”事件導致的隔閡等。為了適應電影以影像蘊涵思想的需要,改編者增補最多的是有意味的細節。如爸爸媽媽看照片。白洋淀上孩子們關于蘆葦的對話,賣冰棍的大爺,教室里的午休,等等。豐富的細節起到了增加真實性,強化思想表達的作用。總之,小說和電影都充分利用了各自的藝術優長,積極回應了呼喚理解、信任、真誠的時代命題。作家和電影人分別以他們出色的工作推動了社會思潮的進步。
同樣以思想深度取勝的是《安德烈的晚上》這部作品,但與《沒有紐扣的襯衫》不同,短篇小說《安德烈的晚上》因其包含著豐富的信息量,為電影改編提供了厚實的基礎。小說敘事始于1950年代,終于1990年代,時間跨度近半個世紀。小說以安德烈從幼年到中年的經歷相貫穿。以安德烈的婚姻和他與姚秀芬的交往為主干情節,旁及周圍的諸多人事。情節的日常性似乎排斥了戲劇性,但是這些對追求寫實風格的電影改編不構成障礙:相反小說的情節密度卻是改編的優勢。電影把重心放在了安德烈的婚姻和沒有開始旋告結束的婚外情上,并以此剪裁小說中的多余情節,同時增加細節、對白,把交代性敘述擴充調整為連貫的場景,用畫面的直觀代替文字的講述。安德烈是罐頭廠的壓蓋工人,他是個平凡的小人物,甚至在小人物中他也是個弱者、不幸者。安德烈從小到大一直處于“被選擇…‘被籌劃”的境遇,從名字、興趣到工作、婚姻。可憐的安德烈和情人姚秀芬中途流產的“出軌”讓人無限感傷。他已經“不會”出軌了。如果說畸形的文化可以消滅人,那么安德烈就是其中的一個。電影敏銳抓住了日常生活的悲劇性,一種被習以為常的表象掩蓋的悲劇內涵,用細節和畫面的力量抗拒人們對一段婚外情感的窺視欲。創造出平實低沉的審美風格,引導觀眾向更深處思考。
三
《村路帶我回家》對原作的故事構架沒有做大的改動。與安德烈相仿,女主人公喬葉葉如小草般柔弱,在那樣一
個時代,對于個人的前途、愛情,甚至命運,她既沒有選擇的自由和權利,也沒有選擇的能力。因此她只能被生活的漩渦裹脅,實際上她好像也愿意被裹脅。在東高莊,她要面對三個青年:金召、宋侃和盼雨,他們都喜歡她,但小說并沒有描寫錯綜復雜的愛情糾葛,而是寫到了喬葉葉在不同情況下對他們的選擇。喬葉葉的生活平淡似水,能稱得上戲劇沖突的也許只有她的愛情生活了,但這僅僅是一種舒緩的摒棄了緊張氛圍的人與人的遭遇,而不是沖突。盼雨拿著斧子找到金召,影片的畫面是充滿生機的農家小院,屋里傳來的吵鬧聲音顯得那么滑稽多余,人物再次出現時,戰爭結束但金召的鍋漏了,一個輕松幽默的收場。工于心計的尤端陽也被處理為非對抗性存在,她似乎只曾經與喬葉葉擦肩而過,電影淡化了她對葉葉命運的影響。“合謀”葉葉扎根農村的大隊支書、公社書記、縣委書記等反面形象也都是以寫意的形式表現在銀幕上,從而保證了影像的連貫與和諧。這諸多因素合成了影片平實素雅的格調,充分展示出生活的質感。電影在平實之外又融合了很多優美抒情的因素,這是原作所不具備的,從而使改編后的作品具有中國山水畫的寫意味道,給人一種雋永的審美享受。
短篇小說《哦,香雪》更像一首絕句、一首清新的小詩,寫的是生活在大山褶皺里的山村少女們的故事。這個小山村叫臺兒溝,千百年來掩藏在大山深處。有一天鐵路修到了臺兒溝腳下,再有一天在臺兒溝設立了小站,火車停靠一分鐘。這短暫的一分鐘給臺兒溝的姑娘們帶來了新奇、憧憬和無盡的遐想。小說的主干情節缺少電影要求的戲劇性,它描繪的是常態的生活和情感,希望通過戲劇性的瞬間表現生存的厚度和豐富底蘊是不可能的。因此,改編者的任務不是增加原作的情節沖突,而是在情節主干周圍增加細節的密度,回到以平常生活表現人的生存狀態的思路。
小說通過姑娘們的眼睛含蓄表現出現代工業文明對農耕文明的撞擊以及二者的融合,同時也表現出自然的美和少女們素樸的美。為了適應這樣的主題,改編者對原作的擴充主要集中在兩方面:(1)展示姑娘們的日常生活,其實也就是山民們的生存狀態,以此發掘民族性格中蘊蓄的“積極的美德”;(2)描寫她們通過車站(火車)形成的與外界的關系,以此揭示兩種文明的沖撞與融合。勞動構成了山民主要的生命活動,很多小說未曾涉及的內容在電影中得到了極具真實感的展示,香雪看榜回家,給羊捎回青草,給羊喂鹽,這些細節不但充滿山區生活的情趣,而且表現出少女與小羊兩個小生命的和諧。鳳嬌和父親曬花椒、搟氈更是典型的山村勞動景象。姑娘們打柿子一場,火紅的柿子和姑娘們青春的笑臉相輝映,讓我們看出人與自然相互依存的和諧關系。釘蓋簾這一微小的細節也極富生活情趣,由此可見改編者的匠心。在勞動場景中,尤以香雪婦女河灘開地和香雪娘推碾子熬油最具藝術震撼力,兩個場景交互穿插,靜默中透出凝重,山民們如此這般地世代艱苦勞作,既值得我們獻上敬意,又讓我們感到心酸。除了勞動場景外,影片還增加了一些能夠表現山民樸素深摯情感的細節。香雪考上了中學,父親叮囑母親用油提子給她要帶的辣椒白菜上多滴兩滴油:香雪吃的白薯面黑窩頭受到同學的故意盤問,母親心疼她給她烙白面餅,父親又提醒說再多放點油,這微不足道的兩滴油把親情表現得那么真切感人,而又令人酸楚欲哭。香雪開學前,爹給她做木鉛筆盒,娘給她繡花書包一場戲是根據小說中的一句話生發出來的,由此可見寡言少語的爹娘心中埋藏著農民式的愛、智慧、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香雪上學在小說中沒有展開,作者只是把它處理成香雪急切想得到一個鉛筆盒的原因,概述了同學們對她不無嘲弄地反復盤問,借此表現出她的善良、純潔,以及因貧窮感到的羞恥。但是,在電影中,香雪上學成了重要的章節。不僅小說中提及的內容給以正面展示,而且增加了吃自薯面黑窩頭的情節,一是娘拿出家底為香雪烙白面餅,想到帶上它就可以平等地和同學吃午飯,她為之高興;但是想到父母的艱辛,她還是把白面餅放了回去,拿起了黑窩頭。二是她拿出黑窩頭在同學面前毫無顧忌地吃。當同桌拿過飯盒讓她就點菜時,她舉起咸蘿卜說:“我有!”顯然,香雪的性格特點在電影中更為豐富、立體,除了善良、純潔、羞恥心之外,又增加了自尊、從容、坦蕩等性格元素。如果說同學們的盤問表現了物質優越導致的某種市儈心理,那么香雪的言行則體現了來自草根階層,代表了民族品性的真、善、美。對于姑娘們到車站看火車,小說僅選取了一個有代表性的場景給以詳細描繪。另外就是一段概述性文字交代姑娘們和車上的旅客和和氣氣地做買賣。電影則描寫了姑娘們前后四次到車站看火車。四次到車站看火車,做買賣,姑娘們由緊張新奇變得老練成熟,火車的一分鐘停靠給山村帶來了現代文明的信息,豐富著她們的生活,也改變著她們的生活。某種意義上。鳳嬌的“北京話”,香雪的鉛筆盒,都成了現代文明的象征符號。電影還增加了姑娘們雨天到候車室巧遇下鄉寫生畫家的一場戲,這些都是現代文明和傳統農耕文明精神交流的象征。
電影通過造型、聲音、蒙太奇等手法創造出了一種散文詩式的生活氛圍,在詩化的日常生活中讓人感受時代的變遷,領悟生活中的美。《哦,香雪》將散文美與詩意美熔于一爐,是當代中國電影史上不可多得的散文電影精品。
鐵凝小說以其獨特的審美特質吸引著改編者。改編者則以新的藝術創造將原作的神韻轉化成電影的詩意之美,將小說的思想意蘊凸顯為可視的影像。文學借助電影擴大了影響,電影倚重文學創造了人文底蘊豐厚、藝術格調清新的佳作。
[參考文獻]
[1]鐵凝,“關系”一詞在小說中——在蘇州大學“小說家講壇”上的講演[J],當代作家評論,2003(06),
[2]陸小雅,《紅表少女》創作后所思所想[J],當代電影,1985(04),
[3]王好為,在大山的皺褶里采擷——《哦,香雪》導演隨筆[J],當代電影,199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