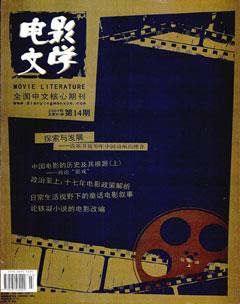《小婦人》實現女性主義的“變異”策略
龍 云
[摘要]奧爾科特寫《小婦人》的時代處于美國內戰剛結束、新舊交替的社會轉型期,奧爾科特贊成女性主義所倡導的女性自立、自強、自主,并鼓勵女性爭取符合個體意志的自由。在《小婦人》中奧爾科特采用一些“變異”手法解構了男性的話語權和男性中心主義,間接地為女性存在和女性生活模式的變通提供了參考。
[關鍵詞]“變異”策略;權力話語;美德;自主
《小婦人》是美國女作家路易莎·梅·奧爾科特的傳世之作,自問世以來吸引了無數讀者。《小婦人》故事情節簡單真實,卻感人至深,問世一百多年以來,多次被搬上銀幕。并被譯成各種文字,成為世界文學寶庫中的經典名作。南導演吉莉安·阿姆斯特朗執導的《小婦人》更是奪得了1994年奧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影片。在這本小說化的家庭日記中,奧爾科特講述了孩子們從天真走向成熟,從自我走向他人的成長故事。奧爾科特在創作過程中運用了一些打破常規性的變通手段,以間接的方式表述了作者的女性主義主張并引發了社會對女性存在以及女性地位進行重新思考。
一、權力易位
法國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化史家米歇爾·福柯(1926~1984)提出的權力話語理論認為話語就是權力,權力存在于一切話語之中。它對一切社會中的話語生產進行控制、選擇和配置,對潛在的威脅、暴力、危險和煽動性的話語進行壓制和排斥。可以說誰掌握了話語權力,誰就可以主導話語。在漫長的父權社會中,被剝奪了平等權的女性從古至今一直在為爭取自己的基本權力而斗爭;在文學領域,女性則為爭取大眾聽到自己的聲音而進行斗爭。在《小婦人》中女兒間的對話以及女兒與母親的對話體現了對男性話語權力的解構,這種女性主義對話干預(intervention)策略是為了增強女性的自我身份。
1父親的“缺場”
《小婦人》最顯著的特點就是缺少男主角,文章開篇女兒們在討論圣誕禮物時,就交代了父親的缺場,這也為全文的整體敘述鋪墊了基礎。“喬幽幽地說道:‘我們現在沒有爸爸。很長時間也不會有。”父親的“缺場”并沒有影響家庭的歡樂氛圍,馬奇太太和她的四個女兒在沒有丈夫和父親的支持下,仍然頑強地通過自己的勞動愉快地生活著,圣誕夜馬奇的家里依然成了童心不泯的歡樂場。小說中絕大篇幅是女性間的對話,這是對父權話語的顛覆。可以說,女性主義的本質具有解構性,父親的“缺場”為推倒父權主義的話語霸權找到了有效的途徑。這一寫作策略的意義在于動搖了以男權為中心的性別定型論和話語權威,同時也為女性承擔起生活和社會中的各種責任提供了機會,為女性把持話語空間提供了可能。
2母親的主導作用
在法國女性主義作家西蘇看來,好母親是“全能的、博愛的、寬宏大量的女性”。父親的“缺場”使得母親馬奇太太成為家庭的精神支柱,她依靠自己的力量締造了快樂的家庭傳統:“她們從打很小,剛能咿咿呀呀念出‘小星星,亮晶晶時,就開始了每晚的歌唱,這已經成了家庭傳統,因為媽媽天生的好歌喉。清晨她的聲音最先響起,她一邊走來走去料理家務,一邊哼唱,像百靈鳴囀。晚上最后聽到的,仍然是她甜美的聲音,小女兒們永遠聽不夠她的搖籃曲。”媽媽在家庭中的決定性作用體現在媽媽角色的任何變化,媽媽為了讓女兒們懂得各盡其能,“一向忙忙碌碌的媽媽一大早就捧一本書,懶散地躺在搖椅上晃來晃去,確實是自然界一大奇觀,喬覺得,哪怕日蝕、地震、火山爆發,都不會比這更讓她震驚了……哪兒哪兒好像都亂了套”,女兒們發出感慨:沒有母親就不是家了。可見,母親角色的轉換馬上讓家里亂了套,這一情節的設計突顯并強化了母親地位的重要性。
二、意象變形
蘇珊·巴斯奈特認為女性主義者可以通過“無窮盡的再閱讀和改寫的快樂,把自己對操縱文本的標記昭示天下”。(許寶強,袁偉2001:323)意象的改寫有助于女性對于文本的駕馭,同時也顯現出女性的視界,從而突顯女性的意識和身份。在《小婦人》中艾美學校的老師戴維斯被學生畫像,呈現出一幅大鼻子、駝背的丑態,這其實是奧爾科特把繪畫過程變為生產話語權力的過程,也是對男權話語的權威性的一種蔑視,在女性視野中戴維斯先生“神經得像個巫婆,暴躁得像頭熊”。其實,意象變形關涉到文化和意識形態問題,這種意象變形的寫作策略關涉到女性自身權力的取得方式,改變了長期以來男性的威嚴主導意象,表現了女性的偏離和叛逆。
女性常態意象的間歇性改變昭示了女性同樣可以掌握話語權,這樣男性中心主義在不同程度上被解構和顛覆了。作為家中的長女,梅格一直是眾姐妹的榜樣,她的形象和舉止可謂是當時女性的典型范例,因為傳統的維多利亞時代的安靜、祥和、優雅嫻靜、多才多藝的傳統淑女才是當時社會所推崇的。不過梅格也有間歇式的“張狂”:梅格在莫法特家的小舞會之夜盡顯風頭,涂脂抹粉、跳急驟旋轉的日耳曼舞、與奈德和他的朋友費希爾喝香檳、撒瘋逗趣、差點用長裙絆倒舞伴的“張狂”模樣都讓隨行的好朋友勞瑞大為驚駭。希瑞勸誡梅格不要喝太多酒,梅格一反常態地回答“今晚我不是梅格,我是個‘玩偶,想怎么瘋就怎么瘋。明天我再不‘矯揉造作了”。梅格用“玩偶”,“矯揉造作”來評價自己的表現,這暗示著她對當時女性日復一日枯燥無味、喪失個性的生活的反感。舞會上的“矯揉造作”更是其本性的最好流露。
不過,正如Derrida所言:“意義不能被‘復制或‘恢復,而總是被創造或再創、刷新。”(Flotow,2004:83)可見變形的的程度越大,獲得的話語權力就越大。女性的話語權力和身份就是在不斷“創造…‘再創造”和“刷新”的過程中形成的,是女性主體性的產物,并非自動生成,徹底的而非間歇的變形才能協助女性走人自由的天地。
三、“靈魂革命”的維度
奧爾科特非常善于用她的小說來提出一些道德觀念,為婦女的權力和地位進行闡釋。《小婦人》中的母親鼓勵四個女兒“靈魂深處爆發革命”,但并不采取強制手段。而是任由她們去經歷生活中的酸甜苦辣,讓孩子們有機會去真實地體驗生命。馬奇太太認為孩子們現在的成長經歷如同她們小時候排演的《天路歷程》。
1美德的培養
信仰天父的仁愛。喬一直以來因為艾美撕了她的書稿而心存芥蒂,母親勸導喬說:“孩子,在你的生活中,煩惱和誘惑剛剛開始,但如果你能像對世間的父親那樣,感受到天父的力量和慈愛,你必能抵御它們,超越它們。你把愛和信給了天父,你就離他越近,越能擁有人間的力與智謀。他的愛與呵護永遠都不會消歇和改變,也無人能夠從你這里奪去,他會給你一生帶來安寧、幸福和力量。用你的心去信任,去他那里訴說你那些小小的憂慮、希望、罪過和悲傷,就像你自由自在地來到母親身邊。”聽到母親一番話,喬感覺到無私與自律的美好,在母親的引領下,她走向這位朋友,他向她敞開愛的懷抱。
2正確婚姻觀的樹立
在當時19世紀美國傳統的婚姻觀念中,財產是至關重
要的準則之一。馬奇太太反對以金錢為導向的婚姻。她對女兒的擇偶提出了建議:“不想見你們匆匆忙忙闖入世界隨便嫁給什么人,只為他有錢,或者有一所豪宅,但它不是一個家,因為那里沒有愛情。錢是個有用的和稀罕的東西,用得恰當,也是個高貴的東西。但我決不希望你們認為,它才是最當緊的或惟一值得追求的東西。我寧愿看到你們做窮人家的妻子,只要你們幸福、滿足、相親相愛,也不愿見你們做個女王,卻失去了自尊與安寧。”馬奇太太認為金錢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人間至美至純的愛情才是幸福的源泉,她這一觀點是對傳統婚姻觀的顛覆。當時的美國社會推崇“真正女人”的傳統信條是把女人禁錮于家庭生活中,扮演社會為女人所規定的賢妻良母角色,并以這種無形的枷鎖阻礙婦女的個性發展。這種社會壓迫促使奧爾科特立志為女性爭取一條獨立的道路。以便她們能夠按照自己理想的模式安排自己的生活。奧爾科特在《小婦人》中塑造了追求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要求在家庭中與男人有平等地位的新女性形象。
奧爾科特對于婚姻的態度可以概括為:再多的金錢也買不回曾經擁有過的寶貴的一切:愛、安定、寧靜和健康,而這些才是生活中真正的幸福,更值得人們留戀和珍惜。
四、結語
以往的文學作品多是以女性的缺場、沉默和男性的出場發言為前提的,女性沒有話語權,任憑男性話語的操縱。女性主義目的就是要消解“菲勒斯中心主義”,反對男權話語對女性的歧視,女性主義的目標是瓦解男性的話語結構,從根本上顛覆父權主義的中心論。《小婦人》中馬奇家四姐妹對自立權力的追求及她們對家庭的忠誠眷顧的描寫。使故事熠熠生輝。小說利用一系列“變異”策略解構了男權社會的主流話語,徹底顛覆了男性的話語權力,體現了一種革命性的力量。在《小婦人》中,奧爾科特突破傳統的女性形象的描寫,倡導女性自強自立。奧爾科特作品的意義在于:首先以女性意識和女性視角統領全文;其次對傳統女性形象、女性觀念有所顛覆。可以說是繼承中兼有創新;再次是對女性獨特的生存體驗和生命體驗有著自覺表露。可以說,奧爾科特的小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的心理意識,是女性在文學世界中建構自我表現的一次革新性嘗試。
注釋:
①②③④⑥⑦(美)路易莎·梅·奧爾科特,小婦人[M],賈輝豐,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1,12,113,67,82,98,
⑤英國清教徒牧師約翰·班揚(1628~1688)所著宗教寓言體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