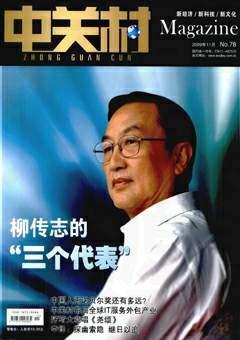抒寫大章唱《堯頌》
喬忠延
盡管作為大型音樂舞蹈史劇《堯頌》的一名歷史文化顧問,盡管親歷了從編劇到樂創(chuàng)、排練、舞美……但是大幕開啟,光縷噴射,看著帝堯帶著先民沖破洪水圍困,獲得新的生機(jī),我還是受到了強(qiáng)烈的震撼!
我為歷史震撼,帝堯的業(yè)績震撼著我!
我為大地震撼,滋生輝煌業(yè)績的臨汾大地震撼著我!
我為劇本震撼,孫巖筆下黃鐘般的文字震撼著我!
我為導(dǎo)演、音樂震撼,他們的藝術(shù)光芒震撼著我!
我更為策劃、創(chuàng)意、組織、排練者震撼,總策劃、作家、山西省臨汾市人大主任、堯文化研究開發(fā)委員會(huì)主任劉合心的睿智果決,市人大教科文委主任盧金城的從容剛毅震撼著我!
我的身心、我的靈魂在震撼中受到了一次新的陶冶,一次新的洗禮。當(dāng)震撼人心的大幕徐徐落下,我不由道出了由《堯頌》引出的幾個(gè)升華:
臨汾的演藝品位升華了!

臨汾的戲劇文化升華了!
臨汾的文化藝術(shù)升華了!
而且,在這升華中,更升華了中華民族的舞臺(tái)演藝水平!
此后,我不止一次回味《堯頌》,也不止一次叩問自己,《堯頌》震撼自己的魅力在哪里?升華中華民族的舞臺(tái)演藝水平的關(guān)鍵在哪里?最終凝定在我腦際的是三個(gè)字:新、深、美。
新——?jiǎng)?chuàng)意新。創(chuàng)新是民族的靈魂,創(chuàng)新是發(fā)展的動(dòng)力,創(chuàng)新是文化藝術(shù)的命脈。回溯一部人類史,漫長的歲月印滿了創(chuàng)新者的步履。創(chuàng)新使人類始有農(nóng)耕文明,創(chuàng)新又推進(jìn)了農(nóng)耕文明,更將告別傳統(tǒng)農(nóng)耕文明。對(duì)于文化藝術(shù)來說,創(chuàng)新就是生機(jī),而循舊必然僵死。《堯頌》最大的感人魅力就在于創(chuàng)新。
眾所周知,堯文化的研究并不一帆風(fēng)順,直到近年臨汾市堯文化研究開發(fā)委員會(huì)成立,標(biāo)志著一個(gè)新的里程成行了。2007年12月舉辦的中國·臨汾堯文化高層論壇更是標(biāo)志著研究工作躍向了一個(gè)新的平臺(tái)。堯文化研究的成果逼枝壓葉:堯都平陽,已成定論;帝堯?yàn)槊駧煹鄯?文明始祖,無可非議;更為讓人欣喜的是將帝堯視為國祖,也沒有絲毫的微辭。這就無可辯駁地告訴我們:臨汾是中國的搖籃!臨汾文化是中國的源頭文化!
就在堯文化的宣傳普及以微小的步子艱難前進(jìn)時(shí),《堯頌》初創(chuàng)了,排練了,面世了!帝堯走出了典籍,走出了考古遺址,走出了研究者的憂慮,亮相在了舞臺(tái),形象、生動(dòng)、鮮活,把一個(gè)業(yè)已枯萎的身軀復(fù)活了,把一段被人遺忘的世事再現(xiàn)了!舞臺(tái)的生機(jī)為帝堯平添了生機(jī),舞臺(tái)的活力為帝堯平添了活力。我不得不為《堯頌》叫好,以《堯頌》傳播堯文化簡直就是神來之筆。回溯往事,舞臺(tái)就是中國歷史的傳播園地,多少中國人了解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不都是在舞臺(tái)上嘛!通過舞臺(tái),帝堯直面觀眾,貼近人民,這確實(shí)是宣傳堯文化的創(chuàng)新之舉。
深——立意深。如前所述,舞臺(tái)使堯文化煥發(fā)了新的生趣。但是,舞臺(tái)藝術(shù)同一切流行藝術(shù)一樣,都是一把雙刃劍。它在成就一種物事的同時(shí),又可能限制物事,這種限制都是因?yàn)槟w淺而俗化了深邃。因之,當(dāng)堯文化即將走上舞臺(tái)的時(shí)侯,我多少為之捏了一把汗。怕這種藝術(shù)方式承載不起厚重的歷史,或者為了迎合觀眾的口味而使歷史流向媚俗。這便可能事與愿違,使本來可以成為大章(大章,堯時(shí)期的歌舞)那樣壯美的題材滑落成幾個(gè)燕雀的嘰嘰之聲。然而,我多慮了!在觀看《堯頌》時(shí),我隨之穿越歷史隧道,直奔上古,去直面帝堯,領(lǐng)悟帝堯。我從帝堯的身上讀出了什么是仁愛,我從帝堯的行跡上看到了什么是天下為公,我從帝堯的業(yè)績上悟得了什么是和諧。仁愛—天下為公—和諧,這些堯文化的精髓都在舞臺(tái)上生動(dòng)地展現(xiàn)了出來。
沒水時(shí)的焦慮,打井時(shí)的艱辛,包容了仁愛;觀天的敬業(yè),禪讓的義舉,展現(xiàn)了天下為公;那一場在《擊壤歌》聲中的爭議,以及樹立起那尊誹謗木的往事無不在呼喚著和諧。這些生成于數(shù)千年前的文化,誰能說過時(shí)了?不僅沒有過時(shí),而且還有著現(xiàn)實(shí)意義。任誰也不得不贊賞堯文化是先進(jìn)文化、優(yōu)秀文化。當(dāng)時(shí)代的步伐以和諧為節(jié)奏闊步向前的時(shí)候,觀看《堯頌》我們不得不為那深入的開掘、淺出的表現(xiàn)而贊美,而叫絕!
美—形式美。立意是靈魂,形式是肢體。靈魂要在肢體中展現(xiàn)。從這個(gè)意義上看,在創(chuàng)意、立意之后,形式即上升為成功與否的關(guān)鍵。即便在創(chuàng)意之初已經(jīng)確定了舞臺(tái)表現(xiàn)的方略,但在舞臺(tái)表現(xiàn)上也有多種類別,是歌曲聯(lián)唱,是舞蹈表演,還是傳統(tǒng)戲劇,這在選擇上尚有很大空間。空間大,可供選擇的自由度就大,這似乎是好事,但自由度大往往讓人左右徘徊,猶豫不前。最大的可怕還不在于此,在于隨波逐波,輕易運(yùn)用某種形式,甚而因輕車熟路而削足適履。這種舊瓶裝新酒的套路,不知扼殺了多少創(chuàng)新的藝術(shù)胚胎。當(dāng)我坐在劇場,陶醉于《堯頌》時(shí),是已經(jīng)為其完美的形式折服了。可以說,在《堯頌》中,肢體足以承載靈魂,靈魂又能在肢體中盡展風(fēng)流,形式和內(nèi)容的有機(jī)結(jié)合使《堯頌》美輪美奐,光彩照人。
大型音樂舞蹈史劇,一聽這形式就是創(chuàng)新,一看果真不假。上世紀(jì)六十年代,有一部風(fēng)靡全國的電影—《東方紅》。其形式為:大型音樂舞蹈史詩。無庸置疑,《堯頌》與之切近,但切近不等于相似。很明顯,《堯頌》和《東方紅》的形式也就是一字之差。《東方紅》是史詩,《堯頌》是史劇。但也正是這一字之差賦予了《堯頌》藝術(shù)的新生。可貴之處在于,帝堯雖然是全民族的,但畢竟成長在臨汾這塊土地上;堯文化雖然是全民族的,甚至是全人類的,但畢竟形成于黃土地上。倘若用一種常用的民族文化符號(hào)詮釋也無可非議,不過總讓人覺得少了文化特質(zhì),淪為一定時(shí)期的全國糧票。這便背謬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這個(gè)創(chuàng)新規(guī)律。好在,《堯頌》沒有沿襲史詩,而是蛻變?yōu)槭穭 R粋€(gè)劇字就有了新意,更何況其運(yùn)用的戲劇是在臨汾這座中國戲劇搖籃里生成的蒲劇呢!
蒲劇同堯文化一樣都是臨汾土地上結(jié)出的果實(shí)。堯文化是源,蒲劇是流。當(dāng)古老的人們投擲擊壤,歌之舞之,戲劇之流便在源頭鼓蕩出發(fā)了。到了元代以后,終于定格為蒲劇。臨汾的蒲劇在中國戲劇界享有很高聲望。在上個(gè)世紀(jì)八十年代中國首屆梅花獎(jiǎng)評(píng)選中,臨汾市蒲劇院的任跟心和郭澤民名列第三和第七名梅花大獎(jiǎng),震動(dòng)全國。以后又連獲20多個(gè)梅花獎(jiǎng),被中國戲劇界命名為全國唯一一個(gè)“梅花之鄉(xiāng)”。用蒲劇去塑造帝堯,去活畫帝堯,可以說是諸種舞臺(tái)選擇中最明智的一舉。這一舉對(duì)于《堯頌》的藝術(shù)成就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或許是我孤陋寡聞,至今還沒有看到,也沒有聽到,在藝術(shù)的苑地里有大型音樂舞蹈史劇,倘若真是如此,那《堯頌》就不僅是臨汾文化界的一枝紅杏,而且在全國也獨(dú)領(lǐng)風(fēng)騷了!
這便是《堯頌》震撼我的原因。
如今,時(shí)光雖然已經(jīng)過去幾個(gè)月了,但那種藝術(shù)的震撼仍在,在我的血脈中,在我的神魂里!
(作者系中國作協(xié)會(huì)員,山西省臨汾市作協(xié)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