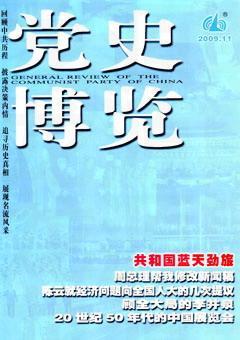一個場景,兩個轉折,兩種心境
王香平
武漢,作為與毛澤東家鄉湖南長沙毗鄰而居的九省通衢,注定要在毛澤東的生命軌跡中占有特殊的位置。這里,是青年毛澤東離開長沙后涉足的又一個大城市;這里,是走上職業革命家道路的毛澤東早期革命活動的中心城市之一。作為政治家,毛澤東與武漢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作為詩人,武漢特有的地理人文景觀成為他不可多得的素材源泉。一個產量不多的詩人,卻有兩首佳作誕生于此,不知是毛澤東的慷慨,還是江城的幸運。也許是機緣巧合。正是這兩首相距近30年于同一場景創作的不同詞作,形象逼真地傳達出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轉折時期那種特有的心理軌跡。
一
1927年,對于20世紀的中國革命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旋渦和拐點。而對丹心救國的革命家毛澤東來說,更是經歷了求索道路上前所未有的苦悶與掙扎。一首《菩薩蠻·黃鶴樓》以寥寥40余字便淋漓盡致地道足了其中三味。
“茫茫九派流中國,沉沉一線穿南北。”浩浩蕩蕩的長江橫亙東西,相會于漢口的粵漢線和京漢線縱貫南北。儼然一座天然的地理坐標。當年佇立黃鶴樓上的毛澤東,正處在這東西南北的交會點上。原本一個客觀的地理形貌,卻被詩人冠以“茫茫”、“沉沉”等頗具感情色彩的疊詞,不管是形容時空之邈遠廣闊,還是狀寫物象之厚重凝滯,都說明在毛澤東胸中,交會的不僅僅是東西南北。更是風云變幻的革命,是波譎云詭的政治,是“心潮起伏的蒼涼心境”。
盡管大革命還沒有宣告失敗。但在1927年的春天,轟轟烈烈的革命洪流中卻涌動著一股不可遏制的反革命逆流。作為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居然向上海的共產黨人舉起了屠刀。中共的主要創始人李大釗也慘遭北方軍閥殺害。風云驟變的革命形勢,毫不留情地將一貫善思慎度的毛澤東推到了十字路口——一個決定中國革命前途的歷史關口。國民革命的命運何去何從?中國共產黨人的奮斗道路何去何從?
“煙雨莽蒼蒼,龜蛇鎖大江。”又一個疊詞“蒼蒼”,外加一個“莽”字和一個“鎖”字,顯然,毛澤東的憂慮、痛楚和迷惘已然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看不到希望的曙光,摸不準前進的道路,一種前所未有的蒼涼與悲愴幾乎要將詩人整個吞噬。
是客觀的革命形勢確實已到了如此嚴酷的地步,還是作為詩人、政治家的毛澤東敏感多慮的神經使然?革命實踐的發展很快便證實了這一切。進入1927年4月,革命形勢陡轉直下,從蔣介石發動的“四一二”政變到汪精衛的“七一五”叛變,大革命以失敗而告終的現實粉碎了所有愛國志士的革命理想。
中國的出路在哪里?民族的希望在何方?誰能夠擔當挽中國革命于倒懸的大任?一首于大革命失敗前夕吟哦的《菩薩蠻·黃鶴樓》傳達出毛澤東未雨綢繆的問詢與思索。這是一個政治家深刻而敏銳的洞察力所在,更體現出一個革命者、愛國者為尋求中華民族的解放道路而發出的深長悲嘆和陷入的無限苦悶。
“黃鶴知何去?剩有游人處。”以革命為己任的毛澤東,自然不可能把希望寄托于富有美麗傳說的駕鶴仙人。“剩有游人處”的自我定位,不僅表現了詩人作為清醒的現實主義者的痛楚,也暗含了毛澤東還將立足現實進行不懈奮斗的決心。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便成為詩人主體決心和追求的進一步表白,同時也為全詞蒼涼凝重的基調增添了一股激昂向上的力量。盡管看不清來路的方向。但探索和拼搏的勁頭不會因此而減弱。相反,與狂風惡浪搏擊,逆反革命潮流而動,這本身就是毛澤東一貫的秉性和風格。
面對形勢的瞬息萬變和革命的險惡危機,毛澤東的心情沉重而壓抑,思想上有如千斤重擔。說明他對中國革命的艱難、復雜和曲折是有充分估計和清醒認識的。在革命力量的重新分化組合中,一些反動勢力赤裸裸地暴露出其冷酷與血腥的面孔。
1927年5月21日,一個叫許克祥的小軍閥,只用一個團的兵力,就把湖南看似強大的農民運動徹底擊垮,把中國共產黨在湖南的力量全部打人地下,這就是歷史上的“馬日事變”。這一事變,從反面印證了毛澤東于兩個月前也就是1927年3月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對中國革命所作的描述:“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這一事變,也加速了中國共產黨對革命道路探索的步伐。于是。“七一五”叛變發生后不到一個月,中共中央在漢口緊急召開“八七”會議,確定了以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和開展土地革命為新內容的路線方針。在這次會上,毛澤東一語驚天下地提出“政權是由槍桿子取得的”著名論斷。隨后,在湖南農民運動的基礎上,毛澤東親自領導農民暴動,舉行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秋收起義。然后又率部向井岡山進軍,從此中國革命找到了正確的道路。
多年以后,毛澤東曾對《菩薩蠻·黃鶴樓》自注道:“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前夕,心情蒼涼,一時不知如何是好。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號,黨的緊急會議。決定武裝反抗,從此找到了出路。”
從“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到“找到了出路”,前后不過4個來月,大革命失敗的陰霾還沒有完全散盡,中國共產黨就找到了自己前進的道路。這一轉折完成的速度如此之快,跨越的時間如此之短,固然有緊迫的斗爭形勢使然,但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本質揭示、對客觀情勢的深刻洞察、對革命出路始終抱持的高度審慎與思考,則成為至關重要的主觀因素。
因此,奔騰不息的浩渺江水和凝然佇立的千年樓臺,這一動靜相宜的天然場景,無疑成為大革命失敗前夕雖不是黨的最高領袖卻堪稱革命先行者的毛澤東憂患沉思與崇高情懷最直觀而生動的歷史見證。
二
近30年后,依然是黃鶴樓,依然是長江,這一似乎與毛澤東精神相通的地理景觀,當它又一次擔當起作為詩人毛澤東情感表達的客觀物象時,記錄下來的卻是毛澤東完全不同的精神風貌。
30年時間,歷史跨越了兩個時代。當毛澤東徜徉在“九派引滄流”的長江中盡情舒展自己的筋骨、領略長江的風采時,他已然是一位建立了人民政權的共和國領袖。親歷新中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毛澤東禁不住唱出了心中的贊歌,一曲《水調歌頭·游泳》充分展露出詩人對新中國建設的憧憬與豪情。這是1956年6月。
1956年,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史上具有標志性意義的一年。這一年,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提前實現。社會主義建設即將翻開新的一頁。
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著名的《論十大關系》的報告,報告后來被稱做是中國共產黨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開篇之作。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新目標、新綱領、新思路,似乎在向人們昭示著觸手可及的美好前景與未來。
5月3日,毛澤東離京南下。在武漢,63歲的他第一次橫渡長江。“今日得寬馀”的詩人身心是愉悅的、輕松
的、舒展的。因此,《水調歌頭·游泳》的基調悠閑明快、樂觀豪邁且充滿希望。
同樣是長江,30年前是“煙雨莽蒼蒼”,30年后是“極目楚天舒”;同樣是龜蛇二山,30年前是“龜蛇鎖大江”,30年后是“龜蛇靜,起宏圖”;同樣借用神話。30年前是“黃鶴知何去?剩有游人處”,30年后是“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世事變遷,風物依舊,而人的心境卻殊然迥異。
然而,歷史的詭譎便在于,當人們確認已是“山置水復疑無路”時,“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前景往往并不遙遠;而當人們篤信目標近在咫尺、成功指日可待時,通向成功的道路可能還很漫長甚至會布滿荊棘。充滿曲折。
1956年,確實是容易激發人們豪情壯志的一年。從1921年建黨開始,歷經35年奮戰的中國共產黨終于可以帶領中國人民開啟社會主義建設的嶄新航程。毛澤東擊水新唱《水調歌頭·游泳》,抒寫的是詩人的宏圖夢想,也是抒寫中國人民的凌云壯志。尤其是“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云雨,高峽出平湖”諸句。不僅暢想了20世紀中國人的三峽情懷與建國理想,更成為激勵幾代中國人矢志奮斗的經典名句。
今天,當三峽大壩巍然屹立在長江西段時,似乎唯有“高峽出平湖”才能表達人們的無限驚嘆與由衷贊美。然而,不經意間,整整半個世紀的光景過去了。掐指一算,中國共產黨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從1927年到1949年走了22年,而“更立西江石壁”的實現卻是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幾十年以后。
看來,社會主義的建設道路似乎并不比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道路好走易行,社會主義建設也并非像毛澤東所描述的那樣“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由此可以看出,1956年的毛澤東心態確實是超乎尋常的自信和放松了。
“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表面上寫當時正在修建的武漢長江大橋,實際上也泛指整個社會主義建設o 1957年5月21日,毛澤東對身邊秘書林克說:“《水調歌頭·游泳》這首詞是反映社會主義建設的。一橋飛架南北,只有我們今天才做到了。”在古今對比中,一種超越前人的高度自信油然而生。“天塹變通途”。所謂“通途”,在毛澤東心中,意指通向未來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恐怕也在情理之中。在毛澤東看來,中國共產黨能夠帶領中國人民贏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也必然會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走出一條寬闊的“天塹變通途”的康莊大道來。
“風檣動,龜蛇靜,起宏圖”,在表現詩人豪邁和暢想的同時,也給人一種節奏的緊迫感、緊張感。因此。當詩人借用孔子“逝者如斯夫”感嘆時光易逝而傳達出只爭朝夕、奮發進取的強烈愿望和廣泛號召時,我們分明能感受到詩人主體內心一種力爭上游的急迫與熱切——那就是希望社會主義建設能夠一日千里,一往無前。
事實上,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從1955年夏季以后,在農業合作化和對手工業、個體商業的改造方面已經出現了“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的問題。1956年初的經濟工作中也出現了急躁冒進的情況。
當然,作為人民共和國的領袖,毛澤東自然是希望積貧積弱的中國人民能夠早日體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優越,早日享受到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的成果,但歷史的發展畢竟有著它不可抗拒的客觀規律。何況,在古老的東方大國建設社會主義,作為一項前所未有的全新事業。也絕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事。
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究竟怎樣走,要以怎樣的心理和精神狀態去走?作為歷史性地改變了20世紀中華民族命運的中國共產黨,是不是領導社會主義建設就必定一帆風順?顯然,處在1956年轉折關頭的毛澤東,有的是夢想,是激情,是豪邁,但似乎又缺少了什么。也許是一種憂患意識的缺失,那就是對未來道路上可能會面臨的種種困難和問題缺乏思想上的預設:也許是冷靜的分析和認識不夠,那就是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深入探索和思考不夠。
暢游長江3個月后,1956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大,提出了國內主要矛盾的新結論,即國內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并據此作出了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必須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的重大戰略決策。
盡管這一符合客觀發展要求的實事求是的政治路線的提出,標志著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轉向全面建設的重大歷史轉折,但路線的制定與具體實施畢竟是兩回事。當1956年過去后不久,中國這艘社會主義的東方之舟便開始了20多年的曲折航程。
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會議上講話時說:“過去20多年,工作重心一直沒有認真轉到經濟建設方面來,經濟工作積累的問題很多。”
半個世紀后的今天,當我們回望來路時。實現社會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全面建設的真正轉折,居然走了如此漫長曲折的一段道路,讓人痛惜而又啟人深思。而作為共和國的領袖和主要決策者,毛澤東通過《水調歌頭·游泳》一詞所表現的他在1956年的思想與心境,不能說與這一轉折實現的艱難漫長毫無關系。
三
江澤民說:“英雄造時勢,時勢也造英雄。在人民創造歷史的同時,不可否認,對歷史事件的成功或失敗,某些個人起關鍵作用。”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進程中,毛澤東在1927年和1956年兩個轉折關頭通過《菩薩蠻-黃鶴樓》和《水調歌頭·游泳》這兩首詞作從一個側面表現出的不同心境和思想軌跡及其與后來歷史發展的重要關聯,也許對我們對后來者永遠都不無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