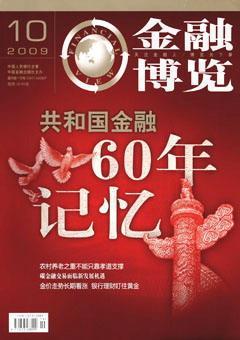西方霸權(quán)與金融崛起(六)
陳雨露
1716年,路易十四去世后的法國王室比較煩,因為他們沒錢花。法國王室的年收入約是7千萬里弗爾(1795年前法國的一種貨幣單位),可支出是2.3億里弗爾,大部分錢用來替“太陽王”擦屁股了。
路易十五年僅5歲,攝政王奧萊昂公爵則純粹是個飯桶,他提出的方法無非是追查失職的財政官、廢除一些行政職務(wù),王室危在旦夕。
這個時刻一個傳奇人物約翰·勞(1671~1729年,John Law)橫空出世,在世界歷史經(jīng)濟學說史、金融史上,約翰·勞絕對都是值得一提的人物。
按照約翰·勞對人類的貢獻,可以這樣定義他的人生:經(jīng)濟學家,法國財政大臣、通用銀行創(chuàng)始人,法蘭西銀行創(chuàng)始人,殺人犯、越獄犯和金融詐騙犯。
約翰·勞出身于英國愛丁堡一個兼營黃金首飾的銀行世家,青年時代接受過良好的政治經(jīng)濟學教育。據(jù)說他曾經(jīng)想去學習銀行和股票交易,但關(guān)于他的記錄卻說他年輕時通常是在賭桌上賺生活費的。雖然最后他曾貴為法國財政大臣,學術(shù)思想獨樹一幟,但他絕對不是年輕人的楷模,因為1694年約翰·勞為了搶女朋友殺掉了情敵,最后被判終身監(jiān)禁。
約翰·勞絕對是個天才,他很有辦法,具體什么辦法不太清楚,反正最后他成功越獄,到了歐洲大陸。在前往歐洲大陸的旅途中(或者說逃亡中)約翰·勞提出了自己的金融理論,1705年出版專著《貨幣與貿(mào)易通論》。
之后200多年,不斷有人復述他的學術(shù)思想,其中有寫了一本書名叫《就業(yè),利息與貨幣通論》的人,這個人叫做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此《通論》非彼《通論》,但彼《通論》源自此《通論》。
約翰·勞的主要觀點如下:經(jīng)濟蕭條的情況下,增加貨幣供給不會提高物價,反而會增加產(chǎn)出,如果沒有金銀,也好辦,用紙幣代替就行;政府應(yīng)當設(shè)立擁有貨幣發(fā)行權(quán)的銀行,這家銀行應(yīng)當提供足夠的信貸和通貨來保證經(jīng)濟繁榮。
1919年,熊彼特在看到《貨幣與貿(mào)易通論》之后掩卷長嘆,“約翰·勞的金融理論足以使他在任何時候都躋身于一流貨幣經(jīng)濟學家之列”。
很不幸,約翰·勞生活在十八世紀,更不幸的是他把當時的法國當作了自己經(jīng)濟理論的試驗品。
可能是法國王室聽說了約翰-勞的理論,可以自己動手印票子,還能帶來更多稅收,很好。不就是成立一家銀行嗎,只要能夠搞到錢,10家也不成問題。不過,此時攝政會議還不敢讓約翰·勞放手去干,1716年法國政府只特許約翰。勞在巴黎建立了一家私人銀行,就是通用銀行(Bangue Genarale),并授予通用銀行特許貨幣發(fā)行權(quán),貨幣可以兌換硬幣和付稅。1718年12月4日,通用銀行被國有化,更名為皇家銀行(Banque Royale),任命約翰·勞為行長。1719年皇家銀行開始發(fā)行國家法定紙幣,同年約翰·勞組建印度公司(Compagnie des Indes),壟斷了法國所有歐洲以外的海外貿(mào)易。
1719年約翰·勞以5000萬里弗爾的價格買下了法國皇家造幣廠,同時發(fā)行印度公司5萬股股票,每股面值1000里弗爾,用以募集資金。印度公司股票的升值給約翰·勞以信心,他跟著以5300萬里弗爾/年的價格接管了法國稅收,他對整個法國征稅,多不退,少補,約翰-勞的方法是裁撤稅官、擴大稅基,取消皇室貴族免稅待遇。
公平地說,約翰·勞在最初的幾年里確實為法國帶來了好處,皇家銀行經(jīng)營良好,緩解了王室財政困境,還捎帶打擊了貴族。
不過接下來的事情,就有點不靠譜了。
約翰·勞希望通過印度公司募股償還30億里弗爾國債,印度公司為此在1719年9~12月份增發(fā)30萬股,每股面值5000里弗爾。
可以這樣猜測,約翰·勞的真實想法是通過皇家銀行發(fā)行紙幣解決財政危機,再通過賣出印度公司股票回購市場上流通的貨幣,這樣實際上流通的貨幣不會增多。
他的思路跟現(xiàn)代中央銀行也沒啥區(qū)別,當代各國中央銀行經(jīng)常賣出國庫券對沖流通中的貨幣,比如中國人民銀行購買不良貸款的專項票據(jù),就直接賣給銀行回收人民幣。國庫券和印度公司股票的實質(zhì)也很類似,都不進入實體經(jīng)濟。
問題是,印度公司股票被炒作得實在太高了,到了這個時候已經(jīng)是完全的投機。如果泡沫破滅,皇家銀行將無法通過發(fā)行印度公司股票回購貨幣,而且印度公司股票好像不能完全對沖流通中的貨幣,按股票發(fā)行價計算約翰·勞最多對沖掉一半貨幣,
關(guān)鍵是,印度公司的股票根本沒有約翰·勞吹噓的收益,雖然當代中央銀行許諾的國庫券收益也沒什么實體經(jīng)濟支撐,但中央銀行和實體經(jīng)濟可以承受這個利率。所以,在那個時代,以股票支撐貨幣回購實在不是一個好主意,遺憾的是當時約翰·勞確實就這么干了,王室的信譽就此亂成一團糟。
股票本身就是投機性金融產(chǎn)品,交易市場上的人多為資本利得而非紅利,當股票價格不能維持收益時,泡沫會破滅,屆時將失去回購貨幣手段,而流通中的貨幣足以擊垮皇家銀行。
約翰·勞注定是這場游戲的輸家。
1720年,約翰·勞的事業(yè)達到了巔峰,王室宣布由他出任法國財政大臣,據(jù)說當時一名貴婦人曾為見她一面故意制造馬車交通事故。傳奇沒有延續(xù)多久,僅到1720年5月印度公司股價就開始下跌,雖然跌幅遠沒有傳說中的離譜,1721年9月也不過跌回1719年5月的水平,約翰·勞設(shè)計的這個體系還是有可能支撐下去的,如果沒有銀行擠兌的話。
如果按照資本充足率計算的話,即使按最低估的數(shù)字,皇家銀行的資本充足率也是16%,比巴塞爾協(xié)議規(guī)定的現(xiàn)代銀行整整高一倍。率先跑到皇家銀行擠兌的竟然是王室成員,任何銀行都經(jīng)不起擠兌,當時的英格蘭銀行也不行,或者說從古至今沒有任何一家銀行能抗住。
每當看到這段歷史,人們都驚訝于約翰·勞的金融天才,計劃本來天衣無縫,根本無懈可擊。但在關(guān)鍵時刻王室背叛了他,并把罪責推托到他身上,約翰·勞的金融帝國轟然倒塌,他只得拿出老本行,再次出逃。
由于印度公司吹噓的是密西西比挖掘黃金的收益,因而這場鬧劇經(jīng)常被稱為密西西比泡沫。密西西比泡沫與郁金香危機,南海危機本質(zhì)截然不同,或者說本就不是一個重量級的體系。
約翰·勞體系本身并沒有過多的錯誤,現(xiàn)代中央銀行就是這個貨幣運作思路,如果說有錯,他確實不應(yīng)該選擇股票作為回購手段,更不應(yīng)該把回購價格定的這么高。
能指責約翰·勞嗎?相信讀者自有公論。此后,大概80年內(nèi)法國都沒敢再重建銀行體系,始終使用鑄幣。可惜,歷史永遠是一艘不能返程的航船。
對于約翰·勞,我們只能說他不應(yīng)該改行當財政大臣,好好當你的逃犯,好好研究你的經(jīng)濟學,或許當代經(jīng)濟學之父就是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