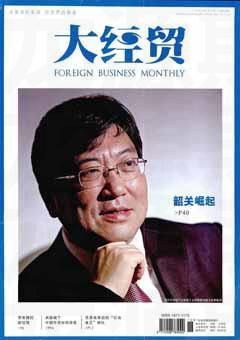政治協商規程廣州先訂先試
龍利群
在新中國成立60周年來臨之際,作為改革開放的前哨,廣州的政治協商制度正在經歷一場標志性的變革。
日前,中共廣州市委正式頒布了《中共廣州市委政治協商規程(試行)》(以下簡稱《規程》),廣州成為國內首個率先對政治協商作出明確規定的中心城市。
《規程》明確了政治協商的兩種基本方式。細化了政治協商的主要內容、形式和程序,明確規定“需要進行協商的內容,未經協商的,原則上不提交市委決策、市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市政府實施”。政治協商在政府決策過程中的效力以市委文件的形式得到強化。
這項由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親自點題的嘗試,也是繼深圳探索大部門制、順德探索省管縣、省政府試行干部公選后,廣東省開展的又一引人注目的改革舉措。
省委書記親自點題
這份被稱為指導新世紀新階段廣州政治協商工作的重要規范、廣州市委推進民主法制建設和多黨合作的重要文件。經歷了一年的醞釀,出臺過程頗為謹慎。
早在去年8月,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一次提案辦理會上的講話中,提出要求廣東省率先制定《政治協商規程》和《辦理政協提案規程》。據廣東省政協研究室主任廖珍玉介紹,這項任務當時交由省政協代為起草。文稿完成后,提交給省委辦公廳。但接下來并未在全省推出。汪洋要求廣州發揮民主法制建設試點城市的作用,開展制定和實施政治協商規程的探索。在全省先行先試。
個中緣由,廖主任表示,主要是由于后來經濟形勢的影響,感覺當時民主政治試驗的大環境不是太好,廣東還是全國都看著的地方。為了確保穩妥,汪洋提出,可以從一個條件比較成熟的市做起。
由于廣州是廣東省民主法制建設的試點市,同時廣州市委書記朱小丹曾擔任過廣東省政協副主席、省委統戰部部長,對政協工作比較熟悉,汪洋選擇了廣州,并給朱小丹“當面交任務,明確提要求”。
根據省委和汪洋的要求,廣州市委將制定政治協商規程列入了推進民主法制建設試點工作計劃。根據汪洋的指示,2008年11月,朱小丹在全省經濟特區工作會議上表示廣州要“完善重要問題政治協商制度,制定政治協商規程,科學界定和具體細化政治協商的內容,明確規定政治協商的程序”。
今年“兩會”后,代擬《規程》的具體任務交到了廣州市政協黨組手上。
據參與起草《規程》的廣州市政協有關人士介紹,接到任務后。廣州市政協由主席朱振中牽頭,兩位秘書長和幾位研究室成員組成了一個起草小組專門負責該項工作,反復征詢各方意見。
在征求意見的過程中,除書面征求、召開座談會等外,朱振中親自帶著起草小組成員挨個走訪了8個民主黨派以及工商聯。“過去開會是大鍋飯,8個民主黨派一起來。每個人發發言,一次性征求,這次我們是跑了9個單位。”該人士表示。從3月到9月,經過“征求意見稿”、“代擬稿”、“代擬送審稿”等程序,字斟句酌。十易其稿。有一些“步子邁得更大”的意見,考慮到實行難度,《規程》沒有完全吸取。“政治改革要循序漸進,不能一口吃成胖子。我們已經邁出了一大步。”參與《規程》起草的廣州市政協有關人士表示。
《規程》草案完成,廣州市委常委會討論通過之后,呈報省委書記汪洋,得到批示:“感覺《規程》總體是成熟的,可以在廣州試行。如試行順利,明年下半年適當的時候向全省推廣乙”汪洋很謹慎,在批示中不忘加上:“似還可請省政協黨組提出意見”。因此《規程》最后的定稿根據省政協意見,又作出了一定修改。
9月3日,《規程》正式頒布。“嚴格說起來不止十稿。”參與起草《規程》的廣州市政協有關人士透露。
政協不再做“虛工”
“《規程》是比較實在的。不能像以往那樣認為是花架子,至少從文本來看,它注重實實在在的內容。”對于謹慎醞釀出臺的《規程》,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肖濱給出了如此評價。這也是幾位受訪者的共識。
具體而言,《規程》共六個部分,除前言和附則外,主體部分有四個章節。廣州市政協主席朱振中在9月7日廣州市、區、縣級市政協主席會議上的講話中,將《規程》的亮點歸納為十個方面。
綜合幾位受訪者的意見,《規程》最主要的突破有五個方面:
——明確把政治協商納入市委市政府的決策程序,這意味著,以后政治協商是市委市政府的重大決策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廣州市政協副主席、民革廣州市主委李勤德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這是《規程》最為突出之處。同時,《規程》具體規定了兩種協商方式(市委同市各民主黨派的政治協商,以及市委在市政協同市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代表人士的政治協商)。
——規定了兩種協商方式下協商的十項具體內容。在“市委同市各民主黨派政治協商的主要內容”中,“中共廣州市代表大會和委員會的重要文件”、“本市經濟社會發展的中長期規劃”、“本市有關城鄉建設的總體規劃和行政區劃的重大調整”等是根據需要首次提出來的。
廣州市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廣州市政協常委陳立認為這條規定尤為重要。他表示:“以前也有一些原則性的規定,要求重大事項的決策‘三在前(即在市委決策之前、人大正式表決通過之前、政府執行之前進行協商),但這只是規定了一個大的框架,長期以來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原因就是沒有細化。比如重大事項如何界定?誰來界定?這樣就存在比較大的隨意性。只有明確協商的主要內容,才有可能真正把這些原則在實際工作中貫徹落實。”
——協商形式有比較具體的規定,如民主協商會、專題座談會、談心會、書面建議等,并對每種形式舉行的頻率和出席人員有著清晰的規定。陳立表示。雖然“座談會、談心會這幾種協商形式,實際上都不是創新的地方”,但《規程》把這幾種形式明確通過書面形式固定下來。并對每種形式做了具體的要求,比如民主協商會,就規定每年至少舉行兩次。
——規定了兩種協商方式的主要程序,即制定協商計劃、做好協商準備、開展政治協商、匯總協商成果、協商成果辦理與反饋等五個程序。其中,首次明確市委每年1月底前要制定年度協商計劃。而在做好協商準備部分,清楚表明“市委召開民主協商會,一般提前十五個工作日由市委辦公廳書面通知市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和工商聯,提前十個工作日向參加協商的市各民主黨派及有關人員提供協商材料或相關的資料”。
——具體提出了政治協商的保障和考核。比如具體要求市委辦公廳牽頭,建立政治協商的督辦落實聯席會議制度,召集市政府辦公廳、市政協辦公廳、市委統戰部。市委政研室等部門定期召開會議。
基于這些內容,肖濱認為。“《規程》在政治協商工作運作的具體細節上,有了更扎實的制度性規定,很多內容可以量化,提供了一個政治協商的規范性框架,一方面,執政黨可以通過這個《規程》檢查自己,我的承諾究竟做得怎么樣,另外民主黨派也可以對執政黨進行考核和評估。從這個角度來講,《規程》在雙重向度上,提供了一個政治協商運作框架的藍圖。這對確保執政黨與其他民主黨派的協商有推進作用,進而也有助于推進中國的協商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