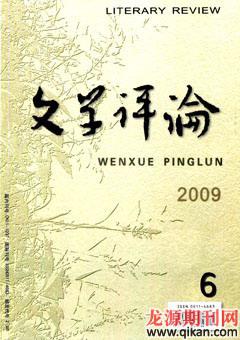白璧德人文主義運(yùn)動(dòng)與現(xiàn)代新儒學(xué)
劉 聰
內(nèi)容提要:白璧德人文主義運(yùn)動(dòng)在中國(guó)產(chǎn)生的最重要效應(yīng)是成為催生現(xiàn)代新儒學(xué)運(yùn)動(dòng)的重要思想資源,其目的不是保守而在于推進(jìn)中國(guó)文化的現(xiàn)代化。白璧德的中國(guó)弟子們是在尋找儒家文化現(xiàn)代化路途上與白璧德結(jié)緣,白璧德為他們提供了闡釋和發(fā)揚(yáng)儒學(xué)的新方法新學(xué)理。由于白璧德主要是以文學(xué)批評(píng)為業(yè),在學(xué)科分化的現(xiàn)代中國(guó),其中國(guó)弟子們的成就主要體現(xiàn)在文學(xué)批評(píng)領(lǐng)域。現(xiàn)代新儒學(xué)運(yùn)動(dòng)是包含理學(xué)、禮教、詩(shī)教的廣義文化思潮,將學(xué)衡派及梁實(shí)秋等人納入現(xiàn)代新儒學(xué)運(yùn)動(dòng)詩(shī)教一維,將為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拓展出開(kāi)闊的學(xué)術(shù)視野。
本文之所以要探討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6-1933)人文主義運(yùn)動(dòng)在中國(guó)的反響與現(xiàn)代新儒學(xué)運(yùn)動(dòng)的關(guān)系,是因?yàn)槲易⒁獾剑阻档碌娜宋闹髁x思想在20世紀(jì)初期和20世紀(jì)末期兩次進(jìn)入中國(guó)時(shí),都與現(xiàn)代新儒學(xué)運(yùn)動(dòng)呈現(xiàn)出一種非常親密的學(xué)術(shù)因緣。按照學(xué)術(shù)界的一般觀點(diǎn),20世紀(jì)中國(guó)的現(xiàn)代新儒學(xué)運(yùn)動(dòng)濫觴于1920年梁?jiǎn)⒊摹稓W洲心影錄》,梁?jiǎn)⒊臍W洲之旅所感受到的“西洋文明破產(chǎn)論”瓦解了他對(duì)西方文明的信仰,使他轉(zhuǎn)而呼吁用西方的學(xué)術(shù)方法維護(hù)和發(fā)揚(yáng)中國(guó)文化,并推動(dòng)中國(guó)文化擔(dān)負(fù)起拯救世界危機(jī)的使命。美國(guó)白璧德等人提倡的人文主義運(yùn)動(dòng)也是西方文明危機(jī)的產(chǎn)物,它于1920年前后由中國(guó)留美學(xué)生傳播到中國(guó),旨在重新闡揚(yáng)包括中國(guó)儒家文化在內(nèi)優(yōu)質(zhì)人類文化,“進(jìn)而解決道德思想之根本問(wèn)題,以拯救人心之危與群治之亂,使全世界均蒙其福利焉”。這兩場(chǎng)運(yùn)動(dòng)擁有同源性文化發(fā)生背景,且在對(duì)待中國(guó)文化的態(tài)度及方式方法上也具有非常一致的同構(gòu)性。1980年代之后,在再度掀起的中西文化碰撞高潮中,我們既看到了現(xiàn)代新儒學(xué)運(yùn)動(dòng)的復(fù)蘇,又可以看到與白璧德相關(guān)的學(xué)術(shù)話題成為熱點(diǎn)。這種現(xiàn)象使得我們不能不認(rèn)真探討其中的原因。
一“新孔教運(yùn)動(dòng)”:白璧德
人文主義運(yùn)動(dòng)的中國(guó)效應(yīng)
20世紀(jì)初期,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后,整個(gè)西方世界科學(xué)主義甚囂塵上,物質(zhì)文明畸形發(fā)達(dá)沖毀了社會(huì)價(jià)值體系,造成了整體性的社會(huì)危機(jī)和精神危機(jī)。在這種背景下,美國(guó)哈佛大學(xué)的白璧德與穆?tīng)?Paul Elmer More,1864-1937),汲取東西方人文主義的精髓,發(fā)起了一場(chǎng)人文主義運(yùn)動(dòng),意在為現(xiàn)代社會(huì)提供“解藥”。為此,他們“致力于恢復(fù)和支持世界范圍內(nèi)眾多圣賢人士的地位”,“主要目標(biāo)是要將當(dāng)今誤人歧途的人們帶回到過(guò)去的圣人們走過(guò)的路途之上,”也就是“用歷史的智慧來(lái)反對(duì)當(dāng)代的智慧”。由于白璧德在這場(chǎng)運(yùn)動(dòng)中的重要地位,所以研究界通常稱之為白璧德人文主義運(yùn)動(dòng)。
白璧德人文主義運(yùn)動(dòng)的發(fā)端可以1908年他的《文學(xué)與美國(guó)大學(xué)》出版為起始。在他的一系列著述中,所有的思想理論都有著積極強(qiáng)烈的現(xiàn)實(shí)指向,正如與他親炙最久的梅光迪所言,他“不是對(duì)某些偏遠(yuǎn)問(wèn)題做研究的專家,作出某個(gè)結(jié)論,在一潭死水的學(xué)術(shù)界;驚起一點(diǎn)點(diǎn)稍縱即逝的波瀾;更不是那種高高在上,與世隔絕的哲學(xué)家,建立一個(gè)別致的思想體系,但僅供觀賞,與實(shí)實(shí)在在的日常生活毫無(wú)關(guān)聯(lián)。相反,他是一位相當(dāng)實(shí)際的學(xué)者,極為關(guān)注自己的思想理論的直接效應(yīng)”。
1921年,白壁德在美國(guó)的中國(guó)留美同學(xué)會(huì)上發(fā)表了一篇演說(shuō),從中可見(jiàn)他極為看重自己所倡導(dǎo)的人文主義運(yùn)動(dòng)在中國(guó)的反響,他指出“孔子始終是一個(gè)人文主義者”,并鄭重呼吁:“我所希望者,此運(yùn)動(dòng)若能發(fā)韌于西方,則在中國(guó)必將有一新孔教之運(yùn)動(dòng),擺脫昔日一切學(xué)究虛文之積習(xí)而為精神之建設(shè)。要之,今日人文主義與功利及感情主義正將決最后之勝負(fù),中國(guó)及歐西之教育界固有一休戚也”。由此可見(jiàn)白璧德把中國(guó)的“新孔教之運(yùn)動(dòng)”看作是自己倡導(dǎo)的國(guó)際人文主義運(yùn)動(dòng)的重要環(huán)節(jié)。這是最早將20世紀(jì)初期的儒學(xué)現(xiàn)代化稱為“新孔教之運(yùn)動(dòng)”的聲音,這個(gè)聲音不是來(lái)自中國(guó),而是來(lái)自推崇孔子學(xué)說(shuō)的自璧德。
白璧德把中國(guó)人文主義運(yùn)動(dòng)的希望放在自己的中國(guó)學(xué)生們身上。吳學(xué)昭在研究吳宓與白璧德的通信中看出“白璧德對(duì)他中國(guó)學(xué)生的關(guān)心”,“他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命運(yùn)的擔(dān)憂。尤其是對(duì)儒學(xué)命運(yùn)的擔(dān)憂。”在給吳宓的信中,白璧德不無(wú)焦慮地指出:“正如你所了解的那樣,我最感興趣的是偉大的儒學(xué)傳統(tǒng)以及其中所包含的令人欽佩的人文主義因素。這個(gè)傳統(tǒng)需要被賦予新的活力并調(diào)整到一種新的狀態(tài),在我看來(lái),任何企圖徹底打破這一傳統(tǒng)的做法,都將對(duì)中國(guó)造成嚴(yán)重的災(zāi)難,并且最終將影響到我們所有人的生活。”白璧德得知吳宓翻譯了介紹自己思想的《白璧德的人文主義》一文后,非常欣慰地說(shuō):“這種翻譯的價(jià)值在于,它可以為中國(guó)的人文主義運(yùn)動(dòng)者與西方國(guó)家中那些有志于發(fā)起類似運(yùn)動(dòng)的人們打開(kāi)一條合作的道路。同時(shí),西方世界渴望接受到比過(guò)去更適當(dāng)?shù)娜寮胰宋闹髁x思想的闡釋,正如你所了解的那樣,這是我樂(lè)于敦促你和其他既熟知中國(guó)文化背景又有良好的西學(xué)知識(shí)的人來(lái)完成的一項(xiàng)任務(wù)。”
白璧德的中國(guó)弟子主要是學(xué)衡派成員和梁實(shí)秋。在梅光迪眼中,“儒家思想可能是除了佛教以外,對(duì)白璧德品性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的一大因素。”而且白璧德的理想就是要成為儒家彬彬有禮的學(xué)者,假如白璧德出生在中國(guó),“他會(huì)成為儒家理想另一位舉足輕重的代言人。”在與白璧德的交談中,梅光迪發(fā)現(xiàn)他“深以孔學(xué)之衰落為可惜,于中國(guó)之門人殷殷致其期望”。在梅光迪看來(lái),“白璧德對(duì)儒家人文主義的評(píng)價(jià)從某種角度上來(lái)說(shuō),向他的中國(guó)學(xué)生指明了中國(guó)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為他們?cè)诋?dāng)今形形色色的文化價(jià)值觀和文化主張中指明了正確的道路。在其影響下,他的學(xué)生們?cè)诳创緡?guó)的文化背景時(shí)有了新的視角和方法——這種方法的基礎(chǔ)要比以前更具批判性態(tài)度和技巧。這種評(píng)論方法并沒(méi)有使諸多年輕的中國(guó)知識(shí)分子更快地背叛自己的文化,反而更堅(jiān)定了他們的信仰。”正因?yàn)閺陌阻档逻@里找尋到了令“古老的儒家傳統(tǒng)”“更具陽(yáng)剛之氣”的辦法,所以梅光迪“幾乎是帶著一種頂禮膜拜的熱忱一遍又一遍地讀著當(dāng)時(shí)已面世的白璧德的三本著作”。
1922年,學(xué)成歸國(guó)的白璧德弟子在國(guó)內(nèi)創(chuàng)辦了同人雜志Ⅸ學(xué)衡》。這一刊物以及由此產(chǎn)生的學(xué)衡派是白璧德人文主義運(yùn)動(dòng)在中國(guó)的重要反響。梅光迪甚至把學(xué)衡派的學(xué)術(shù)活動(dòng)直接稱為“中國(guó)的人文主義運(yùn)動(dòng)”。
學(xué)衡派向國(guó)內(nèi)引介白璧德時(shí),使用的是“人文主義”一語(yǔ),這一詞語(yǔ)是由學(xué)衡派主將胡先骕譯定的,原詞是Humanism。1916年,還在哈佛從學(xué)白璧德的梅光迪,曾將其試譯為“人學(xué)主義”,因?yàn)槊饭獾弦幌蜃詰M英文水平低,在與胡適的通信中,他還猶豫不定地問(wèn)胡適“姑譯之為‘人學(xué)主義可乎”?此后,他也許是覺(jué)得這一譯詞不能直觀體現(xiàn)白璧德思想的本質(zhì),所以棄之不用。后來(lái)吳宓又將其譯為“人本主義”,這一譯詞也沒(méi)能得到學(xué)衡同人及學(xué)術(shù)界的普遍認(rèn)同。直到1922年,胡先騙使用歸化翻譯法,以儒家典籍中與白璧德思想大致相同的“人文”一詞再加上一個(gè)“主義”的后綴,譯定為“人文主義”,既消解了白璧德文化思想的異域色彩和陌生感,使之容易為中國(guó)的讀
者領(lǐng)會(huì)和接受,又直接點(diǎn)明了白璧德思想與中國(guó)儒家思想的親和與相近。于是“人文主義”成為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知識(shí)分子指稱白璧德思想的權(quán)威名詞。而“白璧德”這一姓氏,也是胡先骕使用歸化翻譯法的妙筆,讓人幾乎一望而知白璧德身為西方學(xué)者卻具有中國(guó)儒家君子品德的特點(diǎn)。此前吳宓曾將其譯為“巴比陀”,這一缺少中國(guó)文化特色的譯名最終還是被“白璧德”三字取代。
“人文”在中國(guó)最早出現(xiàn)于《易經(jīng)》,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shí)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唐代孔穎達(dá)的《十三經(jīng)注疏·周易正義》將“人文”闡釋為“詩(shī)書禮樂(lè)”的制作,乃是以儒家經(jīng)典教化天下。
吳宓是白璧德中國(guó)弟子中實(shí)踐其人文主義思想最為勤勉的一位。在他眼中,白璧德“在東方學(xué)說(shuō)中,獨(dú)近孔子。他高度肯定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主體——儒學(xué),并把它視為世界反對(duì)資本主義物化與非理性化斗爭(zhēng)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吳宓實(shí)踐白璧德思想的具體做法就是強(qiáng)調(diào)孔子所代表的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對(duì)現(xiàn)代中國(guó)的重要性,他強(qiáng)調(diào)“今日之要?jiǎng)?wù),厥在認(rèn)識(shí)孔子之價(jià)值,發(fā)明孔教之真理”。而“孔孟之人本主義,原系吾國(guó)道德學(xué)術(shù)之根本,今取以與柏拉圖、亞里土多德以下之各學(xué)說(shuō)相比較,融會(huì)貫通,擷精取粹,再加以西洋歷代名儒巨子之所論述,熔鑄一爐,以為吾國(guó)新社會(huì)群治之基。如是,則國(guó)粹不失,歐化亦成,所謂造成新文化,融合東西兩大文明之奇功,或可企致”。
1931年,吳宓在自己主持的《大公報(bào)·文學(xué)副刊》第199期上,以“新孔學(xué)運(yùn)動(dòng)”為題目,報(bào)道了學(xué)衡派成員郭斌穌的一篇題為《孔學(xué)》的英文演講,這篇演講的主旨在于倡導(dǎo)發(fā)起“新孔學(xué)運(yùn)動(dòng)”,并指明“新孔學(xué)”即“一種人文主義”。學(xué)衡派的另一成員張其昀則在1932年的《時(shí)代公論》第15號(hào)“時(shí)事述評(píng)”一欄,發(fā)表了《教師節(jié)與新孔學(xué)運(yùn)動(dòng)》一文,署名“昀”,充分肯定并重申郭斌穌的“新孔學(xué)運(yùn)動(dòng)”主張。吳宓隨后又在1932年9月26日的《大公報(bào)·文學(xué)副刊》第247期上發(fā)表了一篇《孔誕小言》,再度指明白璧德的文化思想在新孔學(xué)運(yùn)動(dòng)中的重要指導(dǎo)意義。在《悼白璧德先生》一文中,吳宓一一列舉了白璧德的中國(guó)弟子以及讀白璧德書而受其影響的中國(guó)學(xué)人,然后指出,自己與郭斌穌是所有人中“最篤信師說(shuō),且致力宣揚(yáng)者”。由此可見(jiàn),吳宓等學(xué)衡派人士是以倡導(dǎo)“新孔學(xué)”的方式來(lái)實(shí)踐其師白璧德的思想主張,而這一行為方式也正是身在美國(guó)的白璧德所渴望看到的效應(yīng)。
綜上可見(jiàn),白璧德的人文主義思想進(jìn)入中國(guó),不論從白璧德本人的愿望來(lái)看,還是從他的思想在中國(guó)激發(fā)的反響來(lái)看,其主要目的都是指向一場(chǎng)“新孔教運(yùn)動(dòng)”或“新孔學(xué)運(yùn)動(dòng)”。
學(xué)衡派諸人所使用的“新孔教運(yùn)動(dòng)”或“新孔學(xué)運(yùn)動(dòng)”,與現(xiàn)代新儒學(xué)運(yùn)動(dòng)雖有字面上的差異,其內(nèi)涵卻是非常一致的。在白璧德的英文原文中,他表述這一意思時(shí)使用的是“Neo-Confucian movement”一詞。目前西方學(xué)術(shù)界對(duì)20世紀(jì)以來(lái)的現(xiàn)代新儒家的描述是“New-Confucianism”。這兩個(gè)概念的主體部分沒(méi)有本質(zhì)意義上的差別,不同之處在于前綴,“new”和“neo-”雖然都可翻譯為漢語(yǔ)的“新”,但“neo-”所說(shuō)的“新”有更復(fù)雜的含義,它比“new”多了一重“復(fù)興、模仿(copy)先前事物”之意味,也就是說(shuō),“neo-”比“new”更強(qiáng)調(diào)繼承傳統(tǒng)、復(fù)興傳統(tǒng)基礎(chǔ)上的創(chuàng)新。因此,白壁德所使用的“Neo-Confucian movement”一詞,與現(xiàn)代新儒學(xué)的特征更貼近。
在那些后來(lái)被指認(rèn)為新儒家的學(xué)者們中,雖然梁漱溟在1922年就出版了被譽(yù)為現(xiàn)代新儒學(xué)運(yùn)動(dòng)開(kāi)山之作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xué)》,對(duì)儒家文化做出了新的闡釋,但并沒(méi)有旗幟鮮明地打出“新儒學(xué)運(yùn)動(dòng)”的旗號(hào),倒是1921年嚴(yán)既澄在《評(píng)<東西文化及其哲學(xué)>》一文中,以“近代化的孔家思想”來(lái)概括梁氏的思想。此后直至1935年1月,才有新儒家的邊緣人物張東蓀在《現(xiàn)代的中國(guó)怎樣要孔子?》一文中,將張君勱的儒學(xué)研究稱為“新儒家”。至1941年,現(xiàn)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賀麟才在《儒家思想的新開(kāi)展》中,首次用“新儒學(xué)”和“新儒家”來(lái)指稱在20世紀(jì)借鑒西洋文化而重新發(fā)揚(yáng)儒家思想的學(xué)術(shù)和學(xué)人,也就是我們現(xiàn)在所理解的現(xiàn)代新儒學(xué)文化思潮。而30年代馮友蘭和錢穆最初使用“新儒家”一詞時(shí),指的只是先秦漢初儒學(xué)和宋明理學(xué)。相比較而言,白璧德以及受白璧德人文主義思想影響的中國(guó)學(xué)者們,在倡導(dǎo)新儒學(xué)運(yùn)動(dòng)方面要比那些被稱之為新儒家的學(xué)者們有更鮮明更緊迫的意識(shí)。
在我看來(lái),首次打出現(xiàn)代新儒學(xué)運(yùn)動(dòng)的賀麟,極有可能是在吳宓的影響下才有這樣的行為。也就是說(shuō),新儒學(xué)這一概念的提出是現(xiàn)代新儒家們從白璧德的中國(guó)弟子這里獲取了靈感。因?yàn)橘R麟是吳宓在清華大學(xué)執(zhí)教時(shí)的學(xué)生,自稱深受吳宓影響而確立了自己終生的“志業(yè)”。吳宓也將他視為“志同道合之友生”,在所有的朋友中,賀麟是吳宓最珍視的一位。
現(xiàn)代新儒家不僅從白璧德的中國(guó)弟子這里代用了新儒學(xué)運(yùn)動(dòng)這一概念,還借用了“人文主義”這一白璧德思想中國(guó)式表達(dá)的概念。人文主義是現(xiàn)代新儒家們密集使用的關(guān)鍵詞語(yǔ)。被認(rèn)為現(xiàn)代新儒家的典型代表的馮友蘭和當(dāng)代新儒家思想集大成者的牟宗三都深人討論過(guò)人文主義。馮友蘭認(rèn)為“儒家之思想乃極人文主義的Humanistic”。牟宗三則表達(dá)得更為明確,在《道德的理想主義》一書中,他對(duì)“人文主義的基本精神”做過(guò)專章論述,概括了“人文主義的基本特征”為:“消極方面是反物化(主要是唯物論——筆者注)反僵化(指教條主義傾向——筆者注),積極方面便是價(jià)值觀念之開(kāi)發(fā)。”并由此指出:“儒家學(xué)術(shù)的發(fā)展正需要有第三期的發(fā)展。吾人今日之講人文主義,正應(yīng)此時(shí)代之要求而擔(dān)當(dāng)此使命。”牟宗三對(duì)人文主義的界定正是白璧德人文主義的基本特征,他明確地把它納入了新儒學(xué)的意義范疇之內(nèi)。
事實(shí)上,1930年代,梅光迪在《人文主義與現(xiàn)代中國(guó)》一文中,已經(jīng)將那些雖然不是白璧德弟子卻鐘情于儒學(xué)現(xiàn)代化的學(xué)人,一起納入了他所謂的“中國(guó)的人文主義運(yùn)動(dòng)”當(dāng)中。他說(shuō)“需要指出的是,這當(dāng)中許多人,像柳先生(學(xué)衡派重要成員之一柳詒徵——筆者注。)一樣,都是在中國(guó)這片土地上,完全在中國(guó)文化的熏陶之下成長(zhǎng)起來(lái)的·不過(guò)他們也都發(fā)現(xiàn)自己與白璧德的嫡系弟子們有著不少大同小異的觀點(diǎn)——這一事實(shí)表明,美國(guó)批評(píng)家的人文主義精神在世界范圍內(nèi)都頗具吸引力。而且,從整體性來(lái)看,東西方文化本質(zhì)上也有一致性。”
在現(xiàn)代新儒學(xué)研究界有這樣的常識(shí),認(rèn)為20世紀(jì)中國(guó)的現(xiàn)代新儒學(xué)運(yùn)動(dòng)濫觴于1920年梁?jiǎn)⒊摹稓W洲心影錄》,梁?jiǎn)⒊臍W洲之旅所感受到的“西洋文明破產(chǎn)論”瓦解了他對(duì)西方文明的信仰。他號(hào)召青年學(xué)子:“第一步,要人人存一個(gè)單重愛(ài)護(hù)本國(guó)文化的誠(chéng)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學(xué)問(wèn)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綜合起來(lái),還拿別人的補(bǔ)助他,叫他起一種化合作用,成了一個(gè)新文化系統(tǒng)。第四步,把這新系統(tǒng)往外擴(kuò)充,叫
人類全體都得著他好處。……大海對(duì)岸那邊有好幾萬(wàn)萬(wàn)人,愁著物質(zhì)文明破產(chǎn),哀哀欲絕的喊救命,等著你來(lái)超拔他哩……”
上面的引述是梁?jiǎn)⒊稓W游心影錄》的中心意旨,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讓粱啟超確信西洋文明已經(jīng)破產(chǎn),應(yīng)當(dāng)轉(zhuǎn)而發(fā)揚(yáng)中國(guó)文化的是一個(gè)美國(guó)著名的新聞?dòng)浾摺6诿绹?guó),制造并宣揚(yáng)這一思想最為有力的是白璧德、穆?tīng)枴⒀柭热税l(fā)起的新人文主義運(yùn)動(dòng),白璧德被認(rèn)為是“20世紀(jì)前30年西方的領(lǐng)袖思想家”,“當(dāng)世批評(píng)界之山斗”,“每書一出,歐美各大雜志,莫不汲汲稱之”。在哈佛這個(gè)學(xué)生生源遍及世界的頂級(jí)學(xué)府,其思想借由課堂、講座、文章、著作而廣泛影響于美國(guó)和其他各國(guó)。因此我們雖不能說(shuō)白璧德人文主義思想是影響梁?jiǎn)⒊奈ㄒ凰枷耄辽倏梢钥隙ǎ怯绊懫渌枷氲闹匾枷胭Y源之一。
二儒學(xué)的現(xiàn)代解碼:白璧德人文主義
對(duì)中國(guó)弟子們的文化意義
學(xué)衡派和梁實(shí)秋之所以心儀白璧德,是因?yàn)榘阻档聻樗麄兲峁┝艘环N從現(xiàn)代化立場(chǎng)重新闡釋和發(fā)揚(yáng)儒家學(xué)說(shuō)的解碼。也就是說(shuō)白璧德的中國(guó)弟子們對(duì)白璧德選擇,是基于一種現(xiàn)代化的立場(chǎng),而不是保守的文化立場(chǎng),雖然白璧德當(dāng)時(shí)在美國(guó)正被當(dāng)作保守主義者而遭到批判。
在白璧德最有影響的著作《盧梭與浪漫主義》中,他開(kāi)宗明義地宣布了自己的現(xiàn)代立場(chǎng),他說(shuō):“現(xiàn)代這個(gè)詞常常、并且無(wú)疑是必然地被用來(lái)描述比較近的或最近的事情,但這并不是這個(gè)詞的惟一用法。歌德、圣伯夫、勒南和阿諾德這些作家也用過(guò)這個(gè)詞,但并不是只用了這種意思。這些作家所謂的現(xiàn)代精神是指一種實(shí)證的、批判的精神,一種拒絕信賴權(quán)威對(duì)事物進(jìn)行取合的精神。例如,當(dāng)勒南稱彼特拉克為‘文學(xué)中現(xiàn)代精神的創(chuàng)立者時(shí),他所說(shuō)的就是這個(gè)意思,而當(dāng)阿諾德解釋為什么偉大的希臘人在我們看來(lái)似乎比中世紀(jì)的人更現(xiàn)代時(shí),他所說(shuō)的也是這個(gè)意思。我現(xiàn)在努力要做的就是想成為這種意義上的徹底的現(xiàn)代人”。吳宓在介紹他的老師白璧德時(shí),相當(dāng)敏銳地捕捉到了白璧德思想的精要之處,他認(rèn)為白氏所要建立的精確的人事之律,“如何而可以精確乎,日絕去感情之浮說(shuō),虛詞之詭辯,而本經(jīng)驗(yàn),重事實(shí),以察人事,而定為人之道,不必復(fù)古,而當(dāng)求真正之新,不必謹(jǐn)守成說(shuō),恪遵前例,但當(dāng)問(wèn)吾說(shuō)之是否臺(tái)于經(jīng)驗(yàn)及事實(shí),不必強(qiáng)立宗教,以為統(tǒng)一歸納之術(shù),但當(dāng)使凡人皆知為人之正道,仍可行個(gè)人主義,但當(dāng)糾正之,改良之,使其完美無(wú)疵”。
在白璧德和吳宓的這兩段話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與其老師標(biāo)榜的現(xiàn)代姿態(tài)相一致,吳宓從老師那里發(fā)現(xiàn)的也是其思想的“真正之新”。而同樣身為自璧德弟子的梁實(shí)秋也認(rèn)為白氏的“人文主義的思想,固有其因指陳時(shí)弊而不合時(shí)宜處,但其精意所在絕非頑固迂闊。可惜這一套思想被《學(xué)衡》的文言主張及其特殊色彩所拖累,以至于未能發(fā)揮其應(yīng)有的影響,這是很不幸的。”梁實(shí)秋自稱在認(rèn)識(shí)了其思想的博大精深之后,“明白其人文思想在現(xiàn)代的重要性”。
白璧德所稱道的“現(xiàn)代性”的核心就是重新證明和建立“人的法則”。白璧德深知在經(jīng)歷了新古典主義(他稱之為“偽古典主義”)時(shí)期之后,整個(gè)社會(huì)對(duì)秩序與規(guī)范充滿了厭惡的情緒,而“法則”一詞無(wú)疑會(huì)給他招致“反動(dòng)”或“傳統(tǒng)主義”的罪名。但他強(qiáng)調(diào):“現(xiàn)代精神的先驅(qū)應(yīng)該拒絕亞里士多德以及他一直支持的傳統(tǒng)秩序,這無(wú)疑是再自然不過(guò)的。然而如果他們更現(xiàn)代一些的話,他們或許會(huì)將他看成是自己的一個(gè)主要的前驅(qū)。他們或許會(huì)從他身上學(xué)會(huì)如何擁有標(biāo)準(zhǔn),同時(shí)又不被局限于教條之中。”整個(gè)現(xiàn)代實(shí)驗(yàn)面臨著失敗的威脅,原因只是它現(xiàn)代得還不夠。因此,“人只有借助于東方和西方的世俗經(jīng)驗(yàn),提出一種真正現(xiàn)代性的觀點(diǎn),而與此相比,我們聰明的年輕激進(jìn)派似乎是洪水以前的人,這時(shí)他才應(yīng)真正滿意”。在這段話中,白璧德顯示出了建構(gòu)合理的“現(xiàn)代性”話語(yǔ)的努力。
白璧德推崇亞里士多德,他稱“自己正在試圖發(fā)展的觀點(diǎn)為亞里士多德主義的”,而且他又在中西傳統(tǒng)文化對(duì)比研究的基礎(chǔ)上,認(rèn)為“儒教與亞里士多德的教誨也是一致的,而且總的來(lái)說(shuō)與自希臘以來(lái)那些宣布了禮儀和標(biāo)準(zhǔn)法則的人也是一致的。若稱孔子為西方的亞里士多德也顯然是對(duì)的”。正是在這個(gè)意義上,學(xué)衡派與梁實(shí)秋在現(xiàn)代性——白璧德人文主義——孔子(或儒教)——這樣一種思維鏈條上,建立起了基于儒家思想,借鑒白璧德人文主義,打造中國(guó)文化與文學(xué)現(xiàn)代化的途徑。
因此,白璧德中國(guó)弟子們的目的不在于成為中國(guó)文化現(xiàn)代化進(jìn)程的羈絆,而是要為中國(guó)文化的現(xiàn)代化提供一個(gè)自認(rèn)為最合理的方向。正如梅光迪在《人文主義和現(xiàn)代中國(guó)》一文中所說(shuō):“《學(xué)衡》的特別之處更在于它以各種方式告示國(guó)人,建立一個(gè)新中國(guó)唯一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是民族傳統(tǒng)中的精粹部分。”“只有這一類人才能擔(dān)當(dāng)實(shí)現(xiàn)中國(guó)現(xiàn)代化的重任,哪怕要通過(guò)仿效西方來(lái)完成這項(xiàng)任務(wù);只有這一類人才知道該如何模仿西方,因?yàn)樗麄儾粫?huì)讓自己成為沒(méi)有民族特色的人,或者至多成為歐美的二流翻版,他們會(huì)在本‘質(zhì)上保持自己作為中國(guó)人的特色,盡管他們都接受過(guò)現(xiàn)代化的訓(xùn)練,都持有現(xiàn)代派的觀點(diǎn)。”“中國(guó)文化真正的創(chuàng)造力在本國(guó)的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同樣可以大有作為”。
在此,我們有必要考察一下,白璧德的幾個(gè)重要中國(guó)弟子走向白璧德的學(xué)術(shù)因緣。
梅光迪是白璧德的第一個(gè)也是從學(xué)時(shí)間最長(zhǎng)的一個(gè)中國(guó)弟子。他在成為白璧德的弟子之前,就已經(jīng)是一個(gè)極度虔誠(chéng)的孔教復(fù)興者。他躊躇滿志地說(shuō):“吾人復(fù)興孔教,有三大要事,即new interpretation,1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新的闡釋、領(lǐng)袖、組織——筆者譯)是也。耶教有此三者,所以能發(fā)揮光大,吾人在此邦宜于此三者留意。滬上有人發(fā)起孔教會(huì),此亦未始非孔教復(fù)興之見(jiàn)端也。”身在美國(guó)的梅光迪,以自己對(duì)中西文化的了解,意識(shí)到中國(guó)儒家文化對(duì)中國(guó)和世界的重要性,同時(shí)也意識(shí)到,要想讓儒家文化煥發(fā)生機(jī),就必須對(duì)儒家文化進(jìn)行新的闡釋和發(fā)揚(yáng)。所以他在給胡適的信中說(shuō):“惟此邦(歐洲亦然)道德退化已為其本國(guó)有心人所公認(rèn),彼輩方在大聲疾呼,冀醒迷夢(mèng),非迪之過(guò)激也。足下忠厚待人,其意良佳,然我輩決不能滿意于所謂modernization civilization”,必求遠(yuǎn)勝于此者,以增世界人類之福,故我輩急欲復(fù)興孔教,使東西兩文明融化,而后世界和平可期,人道始有進(jìn)化之望。正是抱著這樣的初衷,在美國(guó)四處擇校以實(shí)現(xiàn)抱負(fù)的梅光迪投入到白璧德門下。他以朝圣般的心態(tài)跟隨在白璧德身邊,并且成為白璧德的中國(guó)弟子中最了解白璧德的學(xué)生。他發(fā)現(xiàn)白璧德始終“密切地留意著真正意義上的儒家學(xué)說(shuō)的復(fù)興運(yùn)動(dòng),這種運(yùn)動(dòng)支持歷史繼承性和中國(guó)國(guó)民生活的自主性,其中也融合了一定的現(xiàn)代西方的因素以進(jìn)行合理的調(diào)整”。
吳宓走近白璧德也是出于一種學(xué)術(shù)上的因緣。在清華學(xué)校讀書時(shí)期,吳宓就是一個(gè)儒家文化的擁護(hù)者,在1915年10月5日的日記中,他已經(jīng)立下志愿,要在將來(lái)辦一報(bào)刊。名為“Renaissance”(“文藝復(fù)興”)意在“國(guó)粹復(fù)光”。
吳宓在清華學(xué)校的密友,白璧德非常看重的另一個(gè)中國(guó)弟子湯用彤,在1914年時(shí),即在《清華周刊》上發(fā)表了《理學(xué)譫言》的文章,認(rèn)為“理學(xué)者,中國(guó)之良藥也,中國(guó)之針砭也,中國(guó)四千年之真文化真精神也。”“理學(xué)為天人之理,萬(wàn)事萬(wàn)物之理,為形而上之學(xué),為關(guān)于心的。科學(xué)則僅為天然界之律例,生所之所由,馭身而不能馭心,馭軀形骸而不能馭驅(qū)精神。”也就是說(shuō),在走近白璧德之前,吳宓和湯用彤就已經(jīng)懷抱著強(qiáng)烈的復(fù)興儒學(xué)的愿望。1916年,清華學(xué)校的學(xué)生們?cè)谌珖?guó)學(xué)校中領(lǐng)先發(fā)起成立“孔教會(huì)”,這是全國(guó)第一個(gè)由在校學(xué)生組織的“孔教會(huì)”,吳宓和學(xué)衡派的另一個(gè)重要成員湯用彤都是發(fā)起人之一。梁實(shí)秋則是清華孔教會(huì)的重要成員。他不僅是孔教會(huì)的評(píng)議員之一,還是孔教會(huì)下設(shè)的“鄉(xiāng)村教育研究所所長(zhǎng)”,同時(shí)擔(dān)任清華孔教會(huì)的會(huì)刊《國(guó)潮》周報(bào)的編輯。當(dāng)清華學(xué)校中反對(duì)孔教的學(xué)生王造時(shí)發(fā)表文章責(zé)難孔教會(huì)時(shí),梁實(shí)秋與另一同學(xué)聶鴻達(dá)當(dāng)即做了一篇《駁王君造時(shí)孔教問(wèn)題》予以反駁,這篇文章對(duì)維護(hù)清華孔教會(huì)的聲譽(yù)起到了有力的辯護(hù)作用。從《清華孔教會(huì)宣言書》中,我們可以看出孔教會(huì)員們共同的文化立場(chǎng),宣言中說(shuō):“我清華之設(shè)也,固將以研精西學(xué),用補(bǔ)我之所缺然,亦欲使學(xué)者博采乎歐風(fēng),廣詢乎美俗,而有以改良吾之社會(huì)也。茍不明乎己,將何以取擇諸人,茍忘其國(guó)本又何以保不見(jiàn)化于人,是不可不慎也”。在筆者看來(lái),清華孔教會(huì)雖然是康有為、陳煥章等倡導(dǎo)的孔教會(huì)之回應(yīng),但這一由清華學(xué)子設(shè)立的孔教會(huì),擁有得天獨(dú)厚的文化機(jī)遇,那就是清華學(xué)校(前身是庚款留美學(xué)務(wù)處)本身就是一個(gè)中西文化碰撞的文化環(huán)境,清華孔教會(huì)員良好的西學(xué)教育使他們比國(guó)內(nèi)其他維護(hù)孔教的人搶先占有西學(xué)資源,尤其當(dāng)他們直接進(jìn)入西方親身體驗(yàn)西方文化之后,對(duì)中西文化的深透了解,使他們較早探尋到了儒學(xué)現(xiàn)代化的有效方式。
由此可見(jiàn),白璧德的中國(guó)弟子們走近白璧德的過(guò)程正如保羅·科埃略的小說(shuō)Ⅸ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中所描寫的那樣:一個(gè)去埃及金字塔尋寶的少年,在金字塔旁找到的不是寶藏,而是有關(guān)寶藏的秘密——一個(gè)人告訴他:寶藏并不在神秘的埃及,而就埋在他的家鄉(xiāng),在他每天睡覺(jué)的廢舊教堂的老榕樹(shù)下面。白璧德的這些中國(guó)弟子們都是一些為國(guó)家民族外出尋寶的英雄,但他們?cè)诋愑蛘业降牟皇菍毑兀侵袊?guó)傳統(tǒng)文化寶藏的解碼。
我們可以引吳宓的一段話來(lái)對(duì)證,他說(shuō):“孔孟之人本主義,原系吾國(guó)道德學(xué)術(shù)之根本,今取以與柏拉圖、亞里土多德以下之各學(xué)說(shuō)相比較,融會(huì)貫通,擷精取粹,再加以西洋歷代名儒巨子之所論述,熔鑄一爐,以為吾國(guó)新社會(huì)群治之基。如是,則國(guó)粹不失,歐化亦成,所謂造成新文化,融合東西兩大文明之奇功,或可企致”。梁實(shí)秋在與現(xiàn)代文壇對(duì)話時(shí),批評(píng)者們非常清楚地看出了梁實(shí)秋是運(yùn)用白璧德人文主義思想來(lái)重新闡釋儒家文化。林語(yǔ)堂在批評(píng)梁實(shí)秋的文學(xué)批評(píng)時(shí)說(shuō),白璧德的學(xué)說(shuō)“頗似宋朝的性理哲學(xué)。所以白璧德極佩服我們未知生焉知死的老師孔丘,而孔丘的門徒也極佩服自璧德”。在魯迅與梁實(shí)秋論戰(zhàn)中為魯迅辯護(hù)的韓侍桁也批評(píng)梁實(shí)秋是“孔子抱了白璧德主義”。向梁實(shí)秋的《文學(xué)之歷史背景》一文發(fā)難的姚濁波則諷刺說(shuō):“中國(guó)的中庸主義,已是死的東西,梁教授卻企圖在死的東西上再創(chuàng)造出另一個(gè)‘王國(guó)來(lái)。”而在批判儒家思想的新文化氛圍中,梁實(shí)秋自己說(shuō)得很明白:“儒家的倫理學(xué)說(shuō),我以為至今仍是大致不錯(cuò)的,可惜我們民族還沒(méi)有能充分發(fā)揮儒家的倫理”。他指出:“中國(guó)舊文學(xué)的觀念似乎是已經(jīng)崩潰而不可收拾,然而中國(guó)的固有的文化思想仍有未可厚非者,我們?nèi)粽沓鲆粋€(gè)合乎理性的中心思想,再參加一點(diǎn)健全的西洋批評(píng)學(xué)說(shuō),新的批評(píng)標(biāo)準(zhǔn)不是不可能的。”
三現(xiàn)代新儒學(xué)運(yùn)動(dòng)詩(shī)教之維:研究白璧德
與中國(guó)文化關(guān)系的新視野
由于本文是從廣義上來(lái)探討現(xiàn)代新儒學(xué)運(yùn)動(dòng),所以主要是從其作為一個(gè)文化運(yùn)動(dòng)所具有的文化共性上來(lái)使用這一概念,而這一共性即是方克立先生對(duì)現(xiàn)代新儒家的權(quán)威定義:“現(xiàn)代新儒家是產(chǎn)生于本世紀(jì)20年代、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以接續(xù)儒家‘道統(tǒng)、復(fù)興儒學(xué)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學(xué)(特別是儒家心性之學(xué))為主要特征,力圖以儒家學(xué)說(shuō)為主體為本位,來(lái)吸納、融合、會(huì)通西學(xué),以尋求中國(guó)現(xiàn)代化道路的一個(gè)學(xué)術(shù)思想流派,也可以說(shuō)是一種文化思潮。”
這種界定是目前研究界對(duì)現(xiàn)代新儒家和新儒學(xué)的公認(rèn)的權(quán)威界定,也非常客觀地描述出了20世紀(jì)新儒學(xué)文化思潮的主要特點(diǎn)。
其實(shí),即使不從發(fā)生學(xué)的角度探討白璧德人文主義與現(xiàn)代新儒學(xué)運(yùn)動(dòng)之間的關(guān)系,單就白璧德人文主義與現(xiàn)代新儒學(xué)運(yùn)動(dòng)作一種比較研究,也會(huì)發(fā)現(xiàn),白璧德期待的“新孔教運(yùn)動(dòng)”以及其中國(guó)弟子們倡導(dǎo)的“新孔學(xué)運(yùn)動(dòng)”與上述特點(diǎn)非常一致。首先,二者都體現(xiàn)著一種文化現(xiàn)代化的訴求。其次,二者都提倡用西方的學(xué)術(shù)方法來(lái)闡釋發(fā)揚(yáng)儒家思想。再次,白壁德的思想的核心是人性二元論,在他看來(lái)人性并不是純善的,而是善惡二元,善惡之間的斗爭(zhēng),首先不是存在于社會(huì),而是存在于人內(nèi)心理性與欲望的斗爭(zhēng),所以他強(qiáng)調(diào)入的“內(nèi)在制約”,并進(jìn)而將依據(jù)“內(nèi)在制約”的程度將人生分為宗教,人文、自然三個(gè)等級(jí)或者三個(gè)境界。理性過(guò)度的境界是宗教境界,欲望過(guò)度的境界是自然境界,這二者都是他所批判的,理性與欲望中庸合度的境界即是他所贊賞的人文境界。顯然,白璧德的人性二元論、內(nèi)在制約、以及人生三境界說(shuō)與中國(guó)宋明理學(xué)尤其是心性之學(xué)極為相似,林語(yǔ)堂曾經(jīng)說(shuō)過(guò),白璧德的學(xué)說(shuō)“頗似宋朝的性理哲學(xué)”,宋明心性之學(xué),也被稱為“人本主義的哲學(xué)”,是一種“道德本體論”,帶有形而上學(xué)的色彩。而本體論的最重要特點(diǎn)就是世界劃分為本體世界與現(xiàn)象世界的二分模式,也就是柏拉圖所謂的“一”與“多”的關(guān)系,和宋明理學(xué)家們所提倡的“天人合一”、“萬(wàn)物一體”。“一”與“多”的問(wèn)題也是白璧德著作中一個(gè)非常重要問(wèn)題,他說(shuō):“如果一個(gè)人要想成為一個(gè)健全的個(gè)人主義者,一個(gè)有人性標(biāo)準(zhǔn)的個(gè)人主義者……他就必須牢牢地把握柏拉圖所謂有‘一和‘多的問(wèn)題。”人性善惡二元論和性三品說(shuō)一直是儒家學(xué)說(shuō)的重要范疇,前者發(fā)韌于先秦,后者起于漢儒董仲舒,二者都是宋明心性之學(xué)的重要思想來(lái)源,強(qiáng)調(diào)內(nèi)在的道德節(jié)制是其共同特點(diǎn),這也是宋明心性之學(xué)被稱為道德本體論的原因。
目前,由白璧德的第一批中國(guó)弟子為中堅(jiān)組成的學(xué)衡派,已經(jīng)開(kāi)始進(jìn)入現(xiàn)代新儒學(xué)研究者們的視野,如柴文華先生指出,20世紀(jì)初的國(guó)粹派、東方文化派、學(xué)衡派、現(xiàn)代新儒學(xué)都屬文化保守主義一派,而“現(xiàn)代新儒學(xué)作為‘典型的文化保守主義的代表,它的學(xué)術(shù)理念與上述文化保守主義派別有著難以割舍的內(nèi)在聯(lián)結(jié),這證明了其他文化保守主義派別的學(xué)術(shù)思想是現(xiàn)代新儒家產(chǎn)生和構(gòu)成的重要學(xué)術(shù)淵源”。對(duì)白璧德的人文主義做過(guò)專門研究的曠新年先生則指出“學(xué)衡派對(duì)于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化的思考具有許多合理的因素,而且其對(duì)于傳統(tǒng)的態(tài)度與思考也為現(xiàn)代新儒家開(kāi)了先路。”郭齊勇先生指出學(xué)衡派與現(xiàn)代新儒家“同
屬于一個(gè)大的文化思潮,大的文化群落,但它們之間有不小的區(qū)別。‘現(xiàn)代新儒家主要研究哲學(xué),‘學(xué)衡派的研究對(duì)象主要是文學(xué)與史學(xué)”。更有研究者直接將吳宓與馮友蘭都指認(rèn)為現(xiàn)代新儒家。學(xué)衡派張歆海的文化思想也被指認(rèn)為現(xiàn)代新儒學(xué)范疇。可惜的是,目前學(xué)衡派與現(xiàn)代新儒學(xué)運(yùn)動(dòng)的關(guān)系只是以一筆帶過(guò)的形式被這樣提及,并沒(méi)有人對(duì)此展開(kāi)具體的研究和論證。
既然白璧德人文主義思想及其影響下的中國(guó)學(xué)人與現(xiàn)代新儒學(xué)運(yùn)動(dòng)有如此密切的學(xué)術(shù)因緣,那么將其納入現(xiàn)代新儒學(xué)運(yùn)動(dòng)的研究框架就勢(shì)在必行。
在20世紀(jì)中國(guó),“新儒學(xué)運(yùn)動(dòng)”一語(yǔ)的最早使用者是被稱為現(xiàn)代新儒家的賀麟。他在發(fā)表于40年代的《儒家思想的新開(kāi)展》一文中,認(rèn)為“廣義的新儒家思想的發(fā)展,或儒家思想的新開(kāi)展,就是中國(guó)現(xiàn)代思潮的主流。我確切看到,無(wú)論政治社會(huì)學(xué)術(shù)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里爭(zhēng)取建設(shè)新儒家思想,爭(zhēng)取發(fā)揮新儒家思想。”并將“發(fā)揮新儒家思想,蔚成新儒學(xué)運(yùn)動(dòng)”視為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化的主要特征。他指出:“儒家思想包含有三個(gè)方面:有理學(xué),以格物窮理,尋求智慧。有禮教,以磨練意志,規(guī)范行為。有詩(shī)教,以陶養(yǎng)性靈,美化生活。”“儒學(xué)是合詩(shī)教禮教理學(xué)三者為一體的學(xué)養(yǎng),也即是藝術(shù)宗教哲學(xué)三者的和諧體。因此新儒家思想之開(kāi)展,大約將循藝術(shù)化,宗教化,哲學(xué)化之途徑邁進(jìn)。”
從這些表述中,我們可以看出,雖然目前的研究者僅僅在哲學(xué)史學(xué)意義上研究“新儒家”和“新儒學(xué)”,但“新儒學(xué)”、“新儒家”、“新儒學(xué)運(yùn)動(dòng)”在現(xiàn)代新儒家們眼中,是一場(chǎng)廣義上的文化思潮、文化運(yùn)動(dòng)。它們的內(nèi)涵并不僅局限于哲學(xué)史學(xué)。正如賀麟所言“過(guò)去儒家,因樂(lè)經(jīng)佚亡,樂(lè)教中衰,詩(shī)教亦式微,對(duì)其他藝術(shù),亦殊少注重與發(fā)揚(yáng),幾為道家所獨(dú)占。故今后新儒家之興起,與新詩(shī)教,新樂(lè)教,新藝術(shù)之興起,應(yīng)該是聯(lián)合并進(jìn)而不分離的。”也就是說(shuō)以廣義的藝術(shù)為內(nèi)涵的詩(shī)教是新儒學(xué)運(yùn)動(dòng)的題中應(yīng)有之義。在80年代末,方克立先生針對(duì)把現(xiàn)代新儒家僅視為哲學(xué)思潮的現(xiàn)象提出:雖然“現(xiàn)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都是有哲學(xué)的”,但是“現(xiàn)代新儒家是現(xiàn)代中國(guó)的一個(gè)重要學(xué)術(shù)流派。是一種廣泛的文化思潮,而不僅僅是一種哲學(xué)思潮”。
詩(shī)教是傳統(tǒng)儒學(xué)的一個(gè)文論術(shù)語(yǔ),也稱“儒家詩(shī)教”或“孔門詩(shī)教”,《禮記·經(jīng)解》篇里有這樣一段話:“孔子日:‘入其國(guó),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shī)》教也。”這里的詩(shī)教指的是《詩(shī)經(jīng)》的教化作用,由于《詩(shī)經(jīng)》既是一部詩(shī)歌總集,又是儒家經(jīng)典,由此也就形成了綿延了兩千多年的兩個(gè)詩(shī)教范疇,一者是廣義的的詩(shī)教,即以“助人倫,成教化”為旨?xì)w的儒家文學(xué)和文藝?yán)碚擉w系。一者是狹義的詩(shī)教,指由《詩(shī)經(jīng)》延續(xù)下來(lái)的詩(shī)歌的理論體系。本文借鑒廣義的詩(shī)教范疇,也就是賀麟的詩(shī)教含義。而賀麟對(duì)新儒學(xué)思想開(kāi)展途徑的這一認(rèn)識(shí),被認(rèn)為是“賀麟思想中最富有啟發(fā)意義的”創(chuàng)見(jiàn)。之所以有此評(píng)價(jià),是因?yàn)橘R麟的這一思想不僅拓展了40年代以后新儒學(xué)自身的發(fā)展路徑,也使研究新儒學(xué)的學(xué)者們關(guān)注儒學(xué)在文學(xué)和文論領(lǐng)域內(nèi)的開(kāi)展。但事實(shí)上,對(duì)新儒學(xué)詩(shī)教體系的研究卻嚴(yán)重滯后。
大陸學(xué)術(shù)界對(duì)新儒家們的研究已經(jīng)有了二十年的歷程,集中于哲學(xué)史學(xué)方面的成果已經(jīng)頗為可觀。但新儒家們的詩(shī)教文本卻罕有人關(guān)注,侯敏先生于2003年出版的《有根的詩(shī)學(xué)——現(xiàn)代新儒家文化詩(shī)學(xué)》是第一部研究現(xiàn)代新儒家文論的學(xué)術(shù)專著,作者的選題是基于這一研究的空白而進(jìn)行的。之所以會(huì)形成空白,正如作者在書中所言,對(duì)現(xiàn)代新儒家們來(lái)說(shuō),“哲學(xué)和思想史研究是其學(xué)術(shù)思想的主旋律,而詩(shī)學(xué)則是他們思想的一個(gè)組成部分,他們時(shí)隱時(shí)現(xiàn)于新儒家的學(xué)術(shù)著作中,為思想整體所涵蓋和包容。倘若不能靜下心來(lái)捕捉與梳理,我們就難以掘發(fā)新儒家學(xué)術(shù)話語(yǔ)中蘊(yùn)涵的詩(shī)學(xué)世界”。這種現(xiàn)象是對(duì)現(xiàn)代新儒家的詩(shī)教進(jìn)行研究所要面對(duì)的必然現(xiàn)象,因?yàn)楸环Q為新儒家的學(xué)者們都是從哲學(xué)史學(xué)上起步的,終身以哲學(xué)或史學(xué)為業(yè),文學(xué)是做為文化的一個(gè)方面被論及的。在他們筆下,文學(xué)并不是文學(xué)自身,而是志道據(jù)德依仁的思想注腳。因此這一部以研究現(xiàn)代新儒家文論的著作也只能冠之以“文化詩(shī)學(xué)”的概念,而無(wú)法形成現(xiàn)代意義的文學(xué)理論研究。另外還有兩部著作,分別是先后出版于2004年的《儒家文藝美學(xué)》和《現(xiàn)代新儒家文化觀研究》,前者將“原始儒家到現(xiàn)代新儒家”的上下兩千多年的儒家文藝思想做了綜合研究,后者則研究了20世紀(jì)出現(xiàn)的第一代新儒家,如梁漱溟、張君勱、馮友蘭等人的文化觀,并且把這些新儒家的文藝?yán)碚撟鳛槲幕^的一部分來(lái)觀照。這兩部書的研究也面l臨了與侯敏先生同樣的問(wèn)題,作者在研究的過(guò)程中一直是很艱難地將這一批新儒家的文學(xué)思想從哲學(xué)思想中撕扯出來(lái)。
20世紀(jì)二、三,四十年代的現(xiàn)代新儒家群體中,較早對(duì)藝術(shù)問(wèn)題作過(guò)專門論述的當(dāng)推馮友蘭,但他也只是在《新理學(xué)》中的一個(gè)章節(jié)《藝術(shù)》中,用不過(guò)萬(wàn)字的篇幅闡述了他的新儒學(xué)藝術(shù)觀;在《新事論》中以《評(píng)藝文》一小節(jié)概論了新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的歐化與現(xiàn)代化問(wèn)題。這些文字根本不可能為現(xiàn)代新儒學(xué)撐起詩(shī)教的理論框架。而張君勱及錢穆、唐君毅、牟宗三、方東美、徐復(fù)觀等人,雖然在其著作中談及文學(xué)藝術(shù),但他們的著作面世時(shí)已是在30年代末以后,在新文化運(yùn)動(dòng)之后至30年代末的這個(gè)時(shí)段,他們沒(méi)有提供可以與新文化爭(zhēng)鋒的文學(xué)話語(yǔ),而且他們的文學(xué)話語(yǔ)寄身于哲學(xué)史學(xué)文化話語(yǔ)之內(nèi)的特點(diǎn),也使這些文學(xué)話語(yǔ)被歷史奇異地?cái)R置了,既無(wú)法真正參與文學(xué)領(lǐng)域內(nèi)的對(duì)話,也無(wú)法在文史哲領(lǐng)域內(nèi)得到認(rèn)可,也即沒(méi)有獲得學(xué)術(shù)生命,在當(dāng)時(shí)沒(méi)有為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發(fā)展提供有效資源。這也是朱棟霖先生驚訝于新儒家文論研究空白的重要原因。
在20世紀(jì)的語(yǔ)境中,現(xiàn)代新儒學(xué)的詩(shī)教體系應(yīng)該意味著一套以現(xiàn)代新儒學(xué)基本價(jià)值為本的現(xiàn)代文學(xué)理論體系,唐君毅在現(xiàn)代新儒家中是較早具有這種自覺(jué)意識(shí)的人,他在1943年的《中西哲學(xué)思想之比較研究集》一書中,曾期望有獻(xiàn)身藝術(shù)領(lǐng)域的專業(yè)學(xué)人能夠“重建一種中國(guó)文學(xué)理論之體系。”但他這個(gè)期待比新儒學(xué)運(yùn)動(dòng)發(fā)起的時(shí)間晚了二十多年。事實(shí)上有人比他更早提出這一構(gòu)想,至40年代時(shí)也已經(jīng)有了身體力行的成果。這就是學(xué)衡派以及梁實(shí)秋等受白璧德人文主義思想影響的學(xué)人。
近現(xiàn)代以來(lái),學(xué)科分化導(dǎo)致了不同學(xué)科間的學(xué)術(shù)壁壘,現(xiàn)在從事現(xiàn)代新儒學(xué)和新儒家研究的學(xué)者,主要是哲學(xué)史學(xué)專業(yè)學(xué)者,專業(yè)知識(shí)結(jié)構(gòu)局限定了他們的研究視野,使他們疏于發(fā)現(xiàn)現(xiàn)代新儒學(xué)運(yùn)動(dòng)的文學(xué)藝術(shù)內(nèi)涵;而現(xiàn)代文學(xué)領(lǐng)域的學(xué)者又因?yàn)楝F(xiàn)代新儒家們的哲學(xué)史學(xué)建樹(shù),視現(xiàn)代新儒學(xué)為非本專業(yè)領(lǐng)域,遂造成了現(xiàn)代新儒學(xué)運(yùn)動(dòng)的詩(shī)教一維遺落于兩個(gè)學(xué)科的視野邊界線上,形成了研究上的“雙盲”現(xiàn)象。事實(shí)上,毋須論證我們也應(yīng)該意識(shí)到,儒家思想作為中國(guó)文化傳統(tǒng)的主脈,一向是以文史哲一體的形式傳承和發(fā)展的,進(jìn)入20世紀(jì)以后,隨著學(xué)科分化,它也勢(shì)必會(huì)在文、史、哲三個(gè)學(xué)科中,以符合各個(gè)學(xué)科規(guī)范的形式得到新的開(kāi)展。
白璧德雖然是一個(gè)思想家,但主要以文學(xué)批評(píng)為業(yè),所以走近他身邊受他直接影響的主要是一些致力于文學(xué)批評(píng)的中國(guó)學(xué)生。而白璧德及穆?tīng)柕热宋闹髁x者對(duì)自己特別注重文學(xué)批評(píng)有這樣的解釋:“所以多從事于文學(xué)批評(píng)者,亦以人生無(wú)窮之動(dòng)機(jī)與究竟,表于文學(xué)中者,較在他處更為顯然。而彼等職務(wù)之實(shí)行,可常使文學(xué)本體更能自覺(jué)其為一種之人生批評(píng)也。”梅光迪深得其中三昧,遂在哲學(xué)與文學(xué)批評(píng)二者之間,選文學(xué)批評(píng)為業(yè),他說(shuō):“文學(xué)批評(píng)與哲學(xué),雖同為研究人生,然實(shí)有別,(一)哲學(xué)多趨抽象,或不切近人生,文學(xué)批評(píng)重事實(shí),而為具體之討論。(二)哲學(xué)多用專門文字,非個(gè)中人不能了解。文學(xué)批評(píng)用普通文字(文學(xué)創(chuàng)作亦然),易為人人了解。(三)哲學(xué)家思想或高,而文字未美,能為樸實(shí)之說(shuō)理之文,而不能為藝術(shù)之文,若文學(xué)批評(píng)家之文,則兼說(shuō)理與藝術(shù)矣。”可以說(shuō),白璧德對(duì)中國(guó)學(xué)生的直接影響,就是促成了現(xiàn)代新儒學(xué)運(yùn)動(dòng)在文學(xué)批評(píng)領(lǐng)域內(nèi)的開(kāi)展,并間接影響到與白璧德中國(guó)弟子關(guān)系親密、志向相同的其他學(xué)者。將學(xué)衡派及梁實(shí)秋等人納入現(xiàn)代新儒學(xué)運(yùn)動(dòng)詩(shī)教一維,將為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拓展出開(kāi)闊的學(xué)術(shù)視野。
- 文學(xué)評(píng)論的其它文章
- “文學(xué)研究文化政治與人文學(xué)科”國(guó)際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綜述
- 教育部社會(huì)科學(xué)委員會(huì)語(yǔ)言文學(xué)新聞傳播和藝術(shù)學(xué)學(xué)部2009年度工作會(huì)議暨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召開(kāi)
- 讀周曉風(fēng)《新中國(guó)文藝政策的文化闡釋》
- 讀徐德明《中國(guó)現(xiàn)代小說(shuō)敘事的詩(shī)學(xué)踐行》
- 評(píng)饒艽子楊匡漢主編的《海外華文文學(xué)教程》
- 評(píng)曾棗莊《宋文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