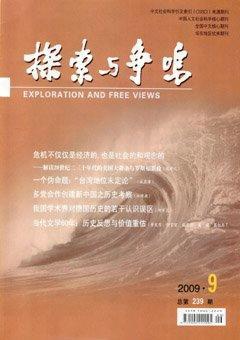本土文學資源的激活與重鑄
黃發有
當西方文學的價值系統被視為優越于中國文學傳統的“現代性”,現代西方被等同于在時間維度上領先的“新”,古典中國被等同于在歷史進程中滯后的“舊”, 片面的追新逐異隱藏著割裂漢語文學傳統的危險,中國文學的現代化就成了缺乏對西方話語進行辨析與批判的唯西方化。魯迅、胡適、錢玄同等人深入傳統內部清理并反思傳統,而一些當代作家卻因為對傳統的無知而拋棄傳統,以至于試圖通過生硬的文化嫁接將西方傳統當成自己的文化根基。讓人納悶的是,一個多世紀以來為什么總是有人理所當然地把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當成水火不容的東西,甚至心安理得地認為割裂傳統是“現代化”的必要代價。
在“十七年”文學中,《林海雪原》、《紅旗譜》、《山鄉巨變》、《三里灣》等作品都留下了繼承本土文學傳統的審美烙印。但是,作家對本土文學資源的自覺認同與深入開掘,更為集中地體現在“文革”后文學的發展進程中。在文化自新意識的推動下,不斷有當代作家以自己的創作實踐,探索本土文學傳統重新鑄造的可能性,其藝術成就也更具有文學史價值。正如韓少功所說的那樣:“我們有民族的自我。我們的責任是釋放現代觀念的熱能,來重鑄和鍍亮這種自我。”[1]一邊是盲目的反傳統所導致的文化虛無主義,另一邊是外來文化的強勢沖擊所催生的文化自卑主義。在這種內外交困的情境中,為了避免使自己成為平均化的全球公民,一些作家以外來文化作為鏡子,開掘沉睡于腳下的土地之中的民族文化記憶,抗拒遺忘,將厚重的傳統資源轉化為社會發展的動力,打破封閉的心理定勢,激活曾經長期被正統文化所抑制的民間文化的創新能量,形成互動共生的良性循環格局。
“尋根文學”常常被視為新時期初期立足本土經驗的文學探索的先驅與典范。確實,尋根作家筆下原汁原味的風情展示彌散出民族化的審美情調,盡管其中也不無模仿拉美魔幻現實主義與福克納式意識流的痕跡,但恰恰是外來刺激強化了其文化認同,在其藝術借鑒中貫穿著一種兼收并蓄、和而不同的本土化情趣,在藝術上也顯現出一種追求民族同一性的身份自覺。事實上,“尋根”文學承續了以汪曾祺、劉紹棠、鄧友梅、馮驥才、林斤瀾為代表的地域風情小說的文化追求,那種沖淡平和的審美風格、寵辱不驚的出塵趣味與傳統士大夫游移于進退之間的入世情懷,與當時呼嘯而過的“傷痕”與“反思”文學大異其趣。雖然這些作品注定不會大紅大紫,但這種疏離文學主流的選擇,恰如汪曾祺在《受戒》中所說:“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是主流。”[2]但是他們對于源遠流長的地域文化的審美表現,卻具備了更加銳利的審美穿透力和更加長久的藝術生命力。
文化尋根的審美追求在詩歌創作中的覺悟要來得更早一些。1982 年楊煉就推出了《半坡》組詩, 1984 年又陸續寫出模擬《周易》思維結構的繁復的《自在者說》。1984年7月以石光華、宋渠、宋煒、楊遠宏為主將的四川“整體主義”詩群宣告成立,江河在1985年初發表了組詩《太陽和他的反光》。楊煉的《諾日朗》和《半坡》、《敦煌》、《西藏》等組詩,從楚騷精神到文化遺址和經典文本,以朝圣者的虔誠從歷史文化中追尋現代啟示的精神源頭。詩人及其后來者通過對遠古神話的激活,尋求現代意識與原始精神展開對話的隱秘通道,在破譯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本原的基礎上,建構 “現代史詩”,瞭望中華民族的來蹤去影的高塔,追索向整體存在趨近的可能性。以廖亦武、歐陽江河為代表的“新傳統主義詩群”則對文化傳統背后隱藏的巨大黑洞進行長驅直入的內在爆破。他們一方面以審父意識沖決正統文化培育奴性的牢籠,另一方面是對一種隱性的、被壓抑的、被遮蔽的民間文化傳統的重新發現,從大地母親蓬勃強健的野性活力中尋找孕育新希望的文化搖籃。在回歸與批判的深入追問中,詩歌對于傳統的多向撞擊開啟了與傳統對話的新空間。
關于本土審美資源的現代轉化,以孫犁、汪曾祺為前驅的新筆記小說的形式探索與文體建構的功績常常被忽略。新筆記小說情節淡化,文字淡雅,意味深長,回歸中國筆記小說傳統并不意味著簡單移植傳統,而是通過主體意識的高揚來擺脫僵化的規范,在舒展性靈的自由選擇中擴展文體的藝術容量和思想含量。這種文體在松散處有暗流涌動,在留白處韻味叢生,在散文化的體式中埋藏詩眼,一些作家對于心理描寫、人性悲劇、象征效果、幽默色彩、寓言風格的探索,猶如在舒緩的田野上挖一口深井。
1980年代中后期以來,文學的本土化探索可謂異彩紛呈,這最為典型地反映在新歷史小說的創作實踐中,作家的價值選擇和形式建構也更加多樣化:
首先,在文本的歷史形態中,創作主體的想象力呈現出自由發散的狀態,從多個角度對民族歷史進行闡釋與重構。和再現真實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歷史小說”不同的是,“新歷史小說”借歷史的軀殼來復活作家心目中的文化精魂,從不同側面拓展歷史敘述的可能性。概括而言,主要表現為:(1)民間野史對廟堂正史的反諷與解構,通過對那些被遮蔽的史料的重新發掘與敘述,通過官史文本的矛盾與裂縫揭露皇權政治的虛偽,批判權力意志對于民間疾苦的漠視及其反人性傾向,代表作品為劉震云的《故鄉相處流傳》和《溫故一九四二》、莫言的《檀香刑》、王小波的《青銅時代》等;另一方面,在主流規范的邊緣處發掘沖決壓抑和馴化的原始生命力,從野地的狂歡中尋覓點燃酒神精神的野性火種,突破腐朽的禁忌,拯救枯竭的靈魂,重新獲得與世界本體融合的快樂,代表作品為莫言的《紅高粱家族》、張煒的《九月寓言》等。(2)虛構原則對信史原則的疏離,從史傳傳統中突圍而出,強調歷史的審美性與想象性,使文學想象從歷史的依附地位中獨立出來,使敘事結構打破了一貫性的時序、因果、整體化結構,回憶、聯想、閃回、蒙太奇、抒情等手段的運用為歷史敘述帶來了豐富性。(3)個人的、心靈的歷史從群體歷史的普遍性中脫穎而出,把歷史看作一種敘述的權利,通過想象找尋到深入人的精神世界的途徑,用情感與內心的歷史來對抗“勝者為王敗者寇”的庸俗的歷史邏輯,張承志的《心靈史》、余華的《在細雨中呼喊》、王安憶的《紀實與虛構》、李洱的《花腔》,都是個體與歷史展開深層對話的文本。
其次,在價值形態上,道德理想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歷史虛無主義與歷史相對主義是兩對雙胞胎,他們互為犄角,有時又相互融合,譬如《白鹿原》的“鏊子說”和《故鄉相處流傳》“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權力鬧劇,居然在歷史循環論的岔口奇妙地匯合。道德理想主義立場倡導回歸到以自然、原始、群體、道德為本位的理想主義,《白鹿原》在精神還鄉之旅中對民族文化從背叛到重新皈依的過程,在向后看的沉醉中寄托了作家渴求民族文化復興的夢想與希望。而懷疑一切的傾向所導致的相對主義與虛無主義,將主體對虛假的、欺騙的價值規范的否定,引向對價值關懷本身的否定,在拋棄虛妄的理想、正義、幸福的同時,也拋棄了所有的意愿、意義與目的。
再次,在形式建構上,“村落與家族”敘述是一種流行的風尚,因為家族制度是中國文化的根底,而村落文化是農耕文明鮮活的細胞。作家們大都以一種詮釋“大歷史”的抱負,要從一個橫斷面來表現現當代或20世紀中國的曲折歷程,進行全景式的審美觀照,反映出建構“氣魄宏大、規模巨大”的文化史詩的形式自覺。但是,作家圍繞家族的想象與編織的故事如何避免歷史與想象完全同構的陷阱,是普遍沒有解決好的藝術難題。
最后,作家們自覺通過對民間傳統的激活來尋找審美的新突破,譬如《檀香刑》中的茂腔(作品中為貓腔)唱詞,《秦腔》中的秦腔戲,《圣天門口》內嵌的民間說唱《黑暗傳》,都成為作品重要的結構元素。而《白鹿原》對于藍田縣志以及其中的《鄉約》文本的創造性化用,使其具備了人類學視野中作為文化收藏形式的民族志風格。此外,《金瓶梅》對《廢都》的影響,在賈平凹、尤鳳偉的“匪行小說”中搖曳的《水滸傳》的文化投影,《儒林外史》對知識分子題材作品的啟示,都是當代文學與古典傳統展開多元對話的表現形式。阿來的《塵埃落定》、《空山》的形式的獨特性,也離不開藏地民間的靈動啟示,作家也坦承“是民間傳說那種在現實世界與幻想世界之間自由穿越的方式,給了我自由,給了我無限的表達空間”[3]。
王小波、李馮、崔子恩、李修文等作家對歷史和中國古典文本進行戲仿的小說顯露出另外一種才情,尤其像《青銅時代》在對唐傳奇的拼貼式重寫中釋放出一種變形的“文革”記憶。這類小說的缺點在于,作家缺乏節制的戲仿,往往只能是以一種荒唐嘲笑另一種荒唐,價值基點的缺失使戲仿成為價值迷惘的文化表征。不過王小波的《青銅時代》的戲仿并沒有迷失在形式主義的泥淖中,它對滅絕人性的權力覆蓋和軀體摧殘的戲謔式描述,勃發著一種酷烈、沉痛、激憤的抗訴。正是在此意義上,戲仿小說無法割斷與反諷的血脈相連的聯系,否則,戲仿就會成為一種純粹的形式舞蹈。
中國文學要得到世界的尊重,關鍵是要向世界提供“人無我有”的獨特奉獻。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當英語和英語文學的版圖不斷擴張時,越來越多的少數族群的語言與文學正在消亡,審美經驗也呈現出逐漸趨同的一體化傾向,世界文學資源的多樣性、豐富性和復雜性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機。在這種情景下,中國文學如何發掘傳統資源,如何在與外來資源的互動認知中,通過對傳統形式的創造性轉化孕育僅僅屬于中國的藝術形式,這是中國作家應當承擔的歷史使命。只有這樣,中國文學才能生發出別樣的審美情趣,猶如在黑暗盡頭的輝煌日出,照亮全新的視野和無限的可能性,為世界提供無可替代的藝術享受。
參考文獻:
[1]韓少功. 文學的“根”. 作家,1985(4).
[2]汪曾祺. 關于《受戒》. 小說選刊,1981(11).
[3]阿來. 文學表達的民間資源. 民族文學研究,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