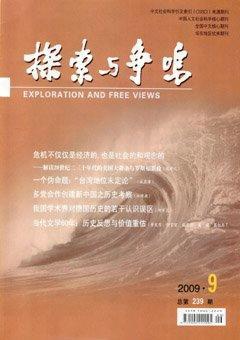當代文學正在喪失反映現實的能力
張光芒
反思當代中國文學的缺失可以有多種角度,至今也形成了許多說法,諸如當代文學缺乏思想穿透力、向消費主義投降、主體性喪失、想象力匱乏、語言水平太低等等。無論是過激地譴責當代文學是“垃圾”,還是溫和地說當代文學“有杰作無大師”,都無一例外地顯示了人們對當代文學極大的失望。失望的來由顯然與此有關:當代文學60年較之于現代文學30年雖然時段長一倍,但總體成就遠遠低于后者;貧窮戰亂年代大師輩出,而在和平時期包括20多年來的經濟盛世,文學精神卻空前地萎縮,本應更多地產生大師的時代卻產生不了大師。各種反思和批評的說法無疑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認為這些還不是最深層的根源之所在,還只是病相而非病灶、病理和病根,更本質的問題要歸之于中國作家自己背叛了生活,當代文學正在喪失反映現實的能力。
一般而言,文學反映現實生活是最基本的要求,由此談論當代文學的缺失不無浮淺之嫌,然而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又是最高的要求。雖然無論對于最平庸的作品,還是對于最偉大的作品,我們都可以說它反映了現實生活,但反映現實的深廣度、切入生活的層面視野、挖掘表相背后之真相的力度,以及在此基礎上藝術地創造生活的能力,卻有天壤之別,也存在著千差萬別的層次。當人們尖銳地抨擊文學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如此墮落與無恥、骯臟與丑陋,如此缺乏人性價值、人文精神和崇高信仰的時候,實際上是在做著情緒化的道德評價和價值判斷,尚不是文學本性上的理性評判。而且這樣的反思路向也往往會使問題本末倒置,甚至有時候恰恰把轉型期某些帶有進步意義和現代性價值的特點歸為病因。比如,當有批評家批判當下作家寫不出表現崇高信仰的作品時,有人就非常有力地反駁說,我們恰恰“應該慶幸當代作家寫不出《紅巖》”,畢竟價值一元化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只要回到文學最基本的問題和閱讀最基本的感受上,我們就會發現,閱讀當代創作,無論是大部頭還是小制作,無論是哪一類描寫題材還是哪一種文學形式,它們最根本的問題是不能揭示生活的真正本質,不能挖掘復雜表相背后的真諦,自然也難以激起人們的共鳴,難以引發人們的深思。文學與現實的距離要么太近,近到與紀實文學、追蹤報道無異;要么太遠,遠到與現實生活無關。近年文壇上的歷史題材熱、古裝戲盛行亦與此有關。文學與生活的關系要么過于傳奇化,要么過于表面化,要么過于私人化,要么過于趣味化。人們對于文學的真正失望來自于文學不能幫助我們擦亮我們觀察置身其中的現實生活的雙眼,不能牽動我們身陷其中的點點滴滴的真切徹骨的心靈痛楚,不能提供給我們更多的理解社會現實的角度,不能帶給我們一線走向未來的光亮。
當代文學真正喪失的首先是展示生活本身、反映現實的能力。這也正是文學成為當今社會生活的裝飾和點綴、成為單純的娛樂渠道和消費品的根源。從近年理論界興起的“審美反映論”的角度看,反映現實的能力之大小取決于審美創造水平的高低,而喪失對于生活本身的開掘意識及深刻感悟能力,則是對于文學本質的悖離。這種意識與能力一旦喪失,連文學價值的高低大小也談不上,更遑論文學的“大道”和神圣的境界了。
總體而言,當代文學首先喪失了展現當代社會全貌與生活整體性的能力,其次喪失的是挖掘生活真相與反映現實復雜性的能力,再次喪失的是描摹文化現狀與人性現狀的能力。
具體說來,第一種喪失并不意味著要求某一部作品或某一位作家去展現整體,而是指文學面對社會生活整體性的無力。且不說對生活有充分的反映能力的創作總是將題材之大與小、整體與局部、典型性與普遍性高度融合為一體,整體性與個別性總是辯證地和審美地耦合起來,單單是當代生活領域的某些引起人們身心極大改變的重要題材在當代創作中也幾乎付之闕如。比如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政治、文化與人們心理的極大改變這一段現實在當代作品中竟然難覓蹤跡。假如以題材有禁區為理由來解釋反映現實能力的喪失是根本站不住腳的,因為作為具有最大的虛構權利的藝術創作本來就有著各種各樣的曲徑通幽的路數與方法。迄今為止,只有個別創作涉及到它。再如對于2003年那次牽動億萬人心的非典事件,也只有個別創作描寫得比較細致到位,更多的則是漠視和遺忘,即使有所反映,也是像徐坤《愛你兩周半》那樣僅僅將非典視為一個營造故事的藝術背景,敘述的中心卻是以欲望為核心的“非典型愛情”,而非它所引起的整體性社會生活的急遽轉變。當然以此題材去弘揚主旋律的文本不計其數,但它們的使命乃是圖解政策而非反映生活,自然更不在我們討論之列。今天根本的問題尚不在于男作家80%在寫偷情,女作家80%在寫離婚,真正讓人擔心的是“作者們的視野狹窄和感覺封閉”[1]。正如韋勒克所呼吁的,“藝術避免不了同現實打交道,不管我們怎樣縮小現實的意義或者強調藝術家所具有的改造或創造的能力”[2]。
文學不僅要緊貼大地,更要傾聽來自地下的呻吟。從第二種和第三種能力的喪失來看,現實生活中許許多多事件的表面邏輯,以及人們習以為常的理解邏輯并非真實的邏輯,真實的邏輯與幾乎所有人看到或理解的邏輯甚至完全相反,這在1990年代以來社會文化與現實生活日益走向多元化后尤其如此。即以一直以來很流行的反腐創作來說,清官好于貪官就是普遍的邏輯,然而早在黑幕文學盛行的晚清,劉鶚就極為警醒地指出清官比貪官更易殺人誤國。真相是有些“真清官”毫無作為,始終做著永遠正確但危害深遠的事情,有的“清官”則只是因為更加謹慎尚未敗露而已。昆德拉曾指出:“極權國家作為這些傾向的極端集中,將卡夫卡小說和現實生活之間的緊密關系變得顯而易見。”他甚至認為,即使西方民主社會看不到這種關系,那也不是因為真的不是這樣,而是因為“人們已經徹底失去了現實感”[3]。由之,“清官”誤國、“圣賢”害民、善惡倒置的生活真相和真實邏輯就這樣被無能的文學遮蔽了。進而言之,至今少有作品有能力揭示出這一新型狀況:卑鄙者載譽、崇高者蒙羞已經成為我們文化的某種常態。
強調文學反映生活的問題絕非是單純地呼喚現實主義,相反,為了更真實地、深刻地和獨具匠心地反映現實,有時候恰恰需要運用新的超越現實主義的藝術原則,有時候恰恰是現實主義方法不能真實地反映羅伯?格里耶所說的那種“浮動的、不可捉摸的現實”。比如近年來文壇上最熱鬧的“底層敘事”、“打工文學”,就往往落入概念化想象和道德化敘述的窠臼,一方面本來就不存在一個孤零零的“底層”,另一方面真正的底層話語卻被敘述的底層曲解了。換言之,許多底層敘事用現實主義方法創作了偽現實主義作品。只要我們不把“反映”二字機械地理解為再現,文學反映生活的能力即文學與現實對話的能力始終深刻地決定著文學價值的本身。就像魔幻現實主義文學所要表現的,并不是魔幻,而是現實,實際上我們會發現,能在更本質的意義上接近我們文化真相的恰恰不是現實主義沖擊波之下的現實主義作品,而是閻連科的《受活》、余華的《兄弟》、莫言的《生死疲勞》等非現實主義的文本。
上述三個方面綜合起來也可以歸結為一點,那就是當代文學沒有充分反映出當代生活以及人性現狀從未有過的畸變及其趨勢。文學反映現實的能力遠遠跟不上生活改變的速度。由于這些能力的喪失,我們很難在1990年代以來社會生活題材的文學創作中找到大于我們身邊瑣事碎聞帶給我們的感悟,以1980年代為敘述對象的創作尚不如我們記憶中的1980年代生活更深刻更有當代價值更為豐富多彩。即使是成績相對大一些的“文革敘事”、“十七年敘事”類文本,在閱讀接受中也常常難以達到許多親歷者在社會現實中感受到的心靈震撼的程度,以及它對于未來生活影響的強大力量。歷史就是過去的現實,現實就是歷史的延續,當歷史或現實的真實比小說更精彩,當現實的痛苦比小說中的更痛苦或者當現實的幸福比小說中的更幸福,當人們普通地感到生活比文學有更高更復雜的真善美,生活也比文學有著更齷齪更令人發瘋的假惡丑,這個時候文學就必然地顯示出它極其低能的反映力量和頹敗相。
參考文獻:
[1]韓少功.當代文學病得不輕.科學時報,2006.12.19.
[2]韋勒克.文學研究中的現實主義概念.批評的概念.北京: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1999:216.
[3]米蘭?昆德拉,董強譯.小說的藝術.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133-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