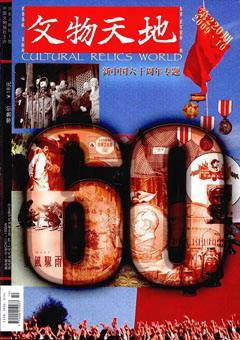十年舊事話曾經
燾 如



一
如果不計算日子,一天天昏頭巴腦的過,倒也不覺得什么,所謂三飽一倒而已。可我們人是社會中一分子,道義責任總要在肩上扛上一些,如果現實和環境是顛倒的、錯誤的,那就難免發生激烈的碰撞。我們假定是處在弱勢,可能不會有表面的行為,但內心的抵觸應該是非常強烈的。當某些事情積淀在心底,總會有爆發的一天。所以,有時想糊里八涂或者說忘性大點兒的過日子,隱忍忘卻,還是很難的事兒。尤其是那些艱難的歲月,那些令人百感交集、魂縈夢牽、痛苦異常的往事,不是你說忘就忘得了的,記得革命導師列寧說過的一句話:“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不忘記過去,可能是回憶某些美好,不忘記過去,也有前車之覆后車之鑒的目的。古大德說得更好:“今而無古,以知不來;古而無今,以知不去。若古不至今,今亦不至古,事各性住于一世,有何物而可去來?”
那么歷史對于我們來說,就有總結、借鑒、提升的多種含義在里面,忽略歷史,漠視它的存在,至少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文革”時期,學校里大興“講用課”之風,那時節逢到這個時候,我總是怕得要命,因為真是不敢講,生怕講錯了被人抓了“小辮子”,用那時候的話說叫“炮打”,那還得了了!于是只能悶頭猛用。記得每當這個時侯,老師說“講用課”開始,那些勇敢的同學,子彈箭頭似的沖向前去,爭先恐后。他們“講用”的文章寫得極好,“引經據典”結合實際,既大膽地剖析自己,又毫無隱瞞表揚自己,令坐在底下的我,真是無地自容,唯有盼著下課鈴響,心里禱愿著早點下課,否則輪到我了,連硬著頭皮上去的勇氣都沒有,按北京人話說:真是憷窩子到家了!但每回“講用課”的這個時候,同學們都是長篇大論、滔滔不絕。萬幸的是,“文革”時期,我還真沒有“講用”過。但“講用”的總結意義,直到今天都影響著我。那么今天我也就肆無忌憚的“講用”一下,目的不在總結,只是憶舊。所以說:痛苦歸痛苦,回憶還得回憶,不能“難得糊涂”。
“文革”十年對某些人來說,是噩夢的十年;“文革”十年對某些人來說,是逍遙的十年;“文革”十年對某些人來說,又是“陽光燦爛”的十年。法國哲學家帕斯卡爾曾經說過:
“克婁巴特拉的鼻子當時若是短一些,整個世界的面貌會不同的。”在那個顛倒的時代,如果不是大革文化命,后面的發展,當不是一個曲折艱難的過程。但無情的事實是,自上世紀60年代初,《“有鬼無害”論》開始,接踵而來的《評<海瑞罷官>》到后來的《5·16通知》文化大革命的開始,風起云涌的、讓人難以忘卻的就是樣板戲,而樣板戲的定型,不管它后來怎樣定論,至少造成了八億人民八臺戲的一個事實。在那只能唱八臺戲的時候,人人會哼個個會唱上兩句,這是它專橫不容他人的霸道反映,同時卻又造成了區別于傳統京劇極大地普及一面。那時節,廠礦機關學校逢到演出,粉墨登場的幾乎都是郭建光、李玉和、少劍波、楊子榮、楊偉才等英雄人物……
二
在現代革命樣板戲中,凡是出現的所有英雄人物,出奇清一色的都是清教徒,《紅燈記》中的李玉和一家人是三個不同姓的革命同志組織起來的,李家祖孫三代人為了革命事業幾乎沒有什么家庭感情的表現,即便表現也放在了革命的理想主義這個前提下。原本《革命自有后來人》中,李玉和有愛喝幾口兒的毛病,經常遭到李母的訓斥,可在《紅燈記》中,將李玉和的愛喝酒這一節沒了,其實這個生活上的小事,是增加英雄可信度的一個基礎,所謂:“人非圣賢孰能無過”?可是在革命樣板戲中,一個英雄人物有愛喝酒的小毛病,多少都顯得“小”,于是,既不能突兀也要有所交代,就改成了李母在兒子被鳩山“請走”時拿酒為兒子壯行,而且還加上了一段臺詞:“孩子,你平時愛喝酒,媽不叫你喝,今天媽請你喝,孩子,你把這碗酒喝了下去!”這一改雖然不是翻天覆地,但卻借酒升華了革命英雄主義,和原來生活中的愛喝酒,是人物的一個小毛病相比,尤其怕人誤解成“酒膩子”“酒鬼”等,這個英雄人物就幾近完美,可以說是煞費苦心。當然,根據劇情需要,李玉和沒有革命伴侶,生按一個也未免顯得牽強。但是,我們發覺,沒有愛情可以理解,怎么連一個小缺點也都給抖落干凈了呢?這是一個。
另一個是《智取威虎山》,這是根據曲波同志的《林海雪原》小說改編的。小說中自茹和少劍波的愛情故事,并不是暗線預伏,而是寫得挺明白的,這本書凡是看過的,大概都不能否認這個情節。可是在《智取威虎山》中,這一段就略去了,當然這又和“三突出”的創作原則有關。這出戲的英雄是楊子榮,“智取”只是小說中的一個段落,于是在戲中理所當然是楊子榮唱主角,如果再摻進少劍波和白茹的愛情故事,不僅淡化了主題,而且還多頭緒,削弱了楊子榮這個英雄人物,那是萬萬不行的。當年京劇《智取威虎山》的改編者不知是誰,按今天的話說,說他是“達人”,應該并不為過。小說中的少劍波是年輕人,代號203,年輕穩重,而楊子榮呢,至少要比少劍波大好多歲,老成持重,深謀遠慮,機智過人。電影《林海雪原》中這個“老楊”,抽煙道具用的是老大爺的旱煙袋,不僅借用道具隱喻他的老成足智,還交代了他和少劍波的年齡差距。電影中楊子榮往往一袋煙過后,招兒就想出來了,假扮土匪深入虎穴,就是他想出來的。在京劇中,則變成了集體的智慧。再回過來說,如果按京劇行當來論,這個楊子榮根據小說提供的實際年齡,應該是老生,而少劍波則應該是小生。當年電影《林海雪原》的少劍波是由張勇手同志演的,楊子榮是由王潤身同志演的,這二位都是表演藝術家,王潤身同志已經過世了,可他塑造的楊子榮,那可是沒說的,連江青都不得不說:“比土匪還土匪”。江青當時的一句話就是圣旨,她認為即便是楊子榮深入虎穴,也應該是英雄的模樣,所以我們比較電影和京劇中的楊子榮,那可是截然不同表現,電影中的楊子榮真是土匪中的“土匪”,京劇中的楊子榮那可是打入土匪內部中的偵察英雄。為了不讓英雄“匪”化,連土匪的黑話也精簡了許多,當年的孩子大人們,人人都知道并學會了幾句黑話,什么“天王蓋地虎”“寶塔鎮河妖”,“么哈,么哈,正晌午時說話,誰也沒有家”,而“想啥來啥,想吃奶……,一座玲瓏塔,面向青帶背靠沙……”這樣的黑話,只有成年人知道,或者在小說中“偷著”領教了。當我們再看到經過改編后出現在京劇舞臺上的這兩個人物時,少劍波的年齡就大了許多,而楊子榮反倒成了年輕人,這樣一來,少劍波就和白茹談不成戀愛了。
再一個就是《紅色娘子軍》,記得謝晉導演后來闡述電影《紅色娘子軍》時,特別覺得惋惜的就是洪常青和瓊花的一段愛情故事沒有被通過,當時他是拍了這個情節的,因為在他認為,只有這樣表現,人物才能完全,才能打動
人,并不僅僅是為了一個充滿理想與浪漫的愛情故事。情在我們這個世間,恐怕濃郁得伴隨我們每個人的一生,當特殊較之于一般,情感戲是最能打動人的地方,是最能催人淚下的,而且能永遠銘記在心的。你像《刑場上的婚禮》這個電影,恐怕我們現在誰誰誰演的都已經記不得了,但電影中反映他們臨刑前“讓敵人的槍聲變成我們婚禮的禮炮……”的話語,但分是看過的,一定不會忘。事業愛情,如果再加上革命,那種英雄主義浪漫主義的東西,就絕不是一般纏綿悱惻的愛情故事所能替代的了!恰恰相反,革命現代舞劇《紅色娘子軍》又略去了這一段描寫。人俗啊,在一般老百姓看來,不管是革命與否,兩個男女青年在一起,還是要發展成兩口子的好,那多圓滿啊!可江青偏偏不,在她看來,樣板戲中的英雄人物一律都要高大完美,性情開朗,長相漂亮,不談戀愛,只談革命。于是,我們看到逃出南霸天魔爪的吳清華,接受常青指路,后又到紅區相會,最終在戰斗中成長以及常青英勇就義等一連串的場景中,始終看不到我們想要看到的,始終都是怪怪的兩個人在理想中“掙扎”,忘了自己是人,忘了這個世界上的情,簡直變成了不食人間煙火的。
那時,懂得的人,自然懂得,不懂得的,是不諳人情世故的孩子,還以為兩個革命男女在一起就是為了革命而生存而奮斗呢!談男女感情那是低級的,有這樣的想法的人在那個時代可不是少數。江青他們塑造的所謂崇高,其實并不真實,說教的成分太大。“文革”前有部電影叫《戰火中的青春》,是由王蘇婭同志主演的,她在片中飾演一個女扮男裝的戰士,和當時英俊小生龐學勤聯合主演,片子中表現的既有對革命理想的追求,又不是住在空中樓閣中的神仙人物,有情有義,看完讓人是覺得腳踏實地,而不是喊了半天,腳底下終歸有點虛。但是,當時的革命樣板戲似乎是只要為了理想、主義,可以不要家庭、愛情。這么看來,愛情是永恒的主題并不適用于現代革命樣板戲。不信你數數,獵戶老常,老伴跳崖身亡,阿慶嫂家的阿慶,從沒露過一面兒,跟沒有一樣,“十八棵青松”個個是單身漢,李玉和不用說,打了一輩子光棍,少劍波剿匪在外,家里也從來少于過問,《奇襲白虎團》中的楊偉才、《海港》中的方海珍均是單身,包括后來樣板戲催生出來的二代,《龍江頌》中的江水英、《杜鵑山》中的柯湘,不一一細數了……
我記憶深刻的一件事情,是到當年父母下放的部隊中去看望他們。
那時節,沒有今天人們稱之為的娛樂,不論是看演出還是看電影,那都是受教育,都是學習。受教育自然都是革命傳統教育,學習的自然都是革命前輩前仆后繼,不怕流血犧牲,勇于為革命事業獻身的崇高精神。那時的電影除了《地道戰》《地雷戰》《南征北戰》和一些八個樣板戲的舞臺紀錄片之外,唯一能看到高鼻深目的外國影片,就是《列寧在十月》、《列寧在1918》了,到后來還能看到被毛主席稱之為“歐洲一盞社會主義明燈”阿爾巴尼亞的影片和朝鮮影片,其中阿爾巴尼亞電影中的一些服裝、穿著,曾給清一色統著干部服的城市居民不少有益的啟發,據說有的女同志為了做一件衣服、編織一件毛衫,這類電影不知看了多少遍!尤其是“薇拉”發式,曾經被許多女青年效仿,“薇拉”頭,也就風靡一時。朝鮮影片《賣花姑娘》和歌劇《血海》也曾讓那時的人們哭倒一片,感動異常。當然,那是很晚的事兒了。早先這“三戰”和“二列”無疑是經典中的經典,看過上百遍的大有人在。要擱現在,人們可能用“厭煩”、“膩透了”來形容,可當時在教育學習的前提下,真可謂:百看不厭呀!大多數那個時期過來的人都能對上述影片中的每一個細節記憶深刻,而且至今仍津津樂道,如數家珍。
而我要說的這段,笑的里面有淚,淚的里面有一種悲哀,不知人性是否應該如此,悲哀的是我們這些蕓蕓眾生,還是非要把我們小小老百姓弄成神仙的“上帝使者”,而他們自己卻躲在一邊去看好萊塢的《出水芙蓉》、《鴿子號》,把北海公園關了,變成了私人的娛樂場的人。
部隊在“文革”時期,也要給戰士們放電影,讓戰士們接受革命傳統教育。我記得才到部隊不久,隨著大人去看《列寧在十月》,其中列寧從芬蘭乘火車秘密返回俄羅斯,準備十月革命起義。在工作的間隙,列寧關心他的警衛員瓦西里,讓他回家看看妻子娜塔莎,在這一場戲中,經典的臺詞莫過于“面包會有的……”,但是讓我意想不到的是,當久別重逢的夫妻二人相見正要親吻的時候,忽然露天場子里統一出一個聲音“——擋!”我正詫異這個詞兒,銀幕上忽然漆黑一片。少頃,復又光明,吻戲不見了。頭一回領略的人當然是莫名驚詫,可我看周邊的戰士們正襟危坐,一副正經的樣子嘴邊卻掛著一絲絲幽默的笑……不少人當初挺得意吻戲這口兒,就像這部電影中一幫水兵看《天鵝湖》舞劇,王子與奧杰塔雙人舞那場,演到情深時,癡狂地鼓掌一樣,這是當時年輕人喜歡看的,至于怎么背著人吻自己的愛人,似乎也要從影片中學習。不想,在部隊放映時,斍把這一節給擋了!這倒不奇怪,奇怪的是戰士們的“擋”字喊在前面,可見他們已經習以為常。這就是我說的笑的后面的悲哀,這不是把群眾當阿斗嗎?
幾十年后,每每想起這個事兒,好笑之余引發的是更加深刻地思索。那個時代將人們憑空拔高到理想、主義的高度,脫離了社會發展的規律性,背離了人性的根本,無視現實,讓革命者都變成了清教徒,委實是一種很霸道、無知的做法。
三
年輕的時候不知道什么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萊希特,只知道梅蘭芳,而到了后來才知道,這三個人竟代表著三大表演體系。
再后來,看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論演員的修養》和布萊希特的《高加索灰闌記》,才感覺到斯氏、布氏的某些東西和我們中國人的暗合,那就是概括、寫意、程式化。如果從歷史的記憶來看,“文革”時期的樣板戲對于那個時期從未接受過傳統戲劇熏陶年輕人來講,他們眼中的京劇,特別是舞臺上的布置,可能他們會認為從來京劇的舞臺就是這樣的,《沙家浜》就該有“春來茶館”“蘆葦蕩”“刁德一家”等等布置,《紅燈記》中就該有“粥棚”“憲兵隊”“李玉和家”等,《智取威虎山》就該有“林海雪原”“訪貧問苦的獵戶家”“威虎廳”等等,其實,這已經不是京劇的東西了!
記得當年看《智取威虎山》,楊子榮的扮演者童祥苓經過小分隊支委會的討論通過,毅然只身假扮許大馬棒的飼馬副官胡彪,前往威虎山。其中有一段唱叫“迎來春色換人間”,配合著這段唱,楊子榮穿林海、跨雪原,騎馬馳騁在茫茫雪原上,那個舞臺布景,極有縱深感,美得不行。我手邊還有當年的劇照,楊子榮足蹬翻毛靴子,身著皮大衣,內穿虎皮坎肩兒,頸間一條白圍巾,頭上皮帽,手持馬鞭兒,在林海雪原中穿行……但舞臺上這樣的置景,卻
是典型的話劇舞臺美術方法,林海、雪原的置景都相當寫實,可楊子榮手中的馬鞭兒,卻是十足的寫意,這至少說明這些人不得已還得尊重傳統,否則,牽匹馬上臺,還不亂了套了?!
自打徽班進京之后,發展到今天,經過多少代人的辛勤耕耘,逐漸固定下來一種高度程式化的藝術表現,不僅要求演員必須具備唱念做打的基本功夫,觀眾也不應該只是看看熱鬧的,而是通過臺上臺下的多年磨合,進而達到一種默契,也就是“懂戲”。舞臺美術也是高度概括、寫意的方式服務于劇情,往往演員一個眼神兒觀眾就能知道所要表達的內涵,一個動作就能知道演員要干什么。《秋江》中只須借用一下船槳,便能讓人意會有船,《秦瓊賣馬》只須拿著馬鞭兒,就能讓人感覺有馬,至于說開門、上樓等均用身體語言來表達并沒有實景配合而無不準確、可信。臺上的一招一式,臺下的心領神會,演員自是難當,可觀眾也不白給,什么時候該這樣,什么時候該那樣,一點兒都不能錯,錯了給你喊倒好兒。演員必須尊重觀眾,因為自己的前程是“座兒”給的。
而樣板戲的觀眾,就不需要這樣的修養了,這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革新,看任何一部樣板戲,不需要基本觀劇知識儲備,看了就能明白,唱詞兒也不咬文嚼字,不僅明白易懂而且還經過一些文化人的潤色,就那個時代而言,還是相當美的。但樣板戲的舞美改變了傳統京劇中的寫意和象征的方法,用西洋繪畫的寫實布景、道具、服裝代替了過去寫意概括的方法,削弱了人們的想象空間,不知這算是進步還是倒退。像前面說的唱念做打這些個基本功,演員是從這四個方面去練的,觀眾也是從這四個方面去看的。不可否認的是,樣板戲中唱,豐富了傳統京劇中的唱腔。它們其中的一些唱段,至今聽起來還是非常好聽的,以至于“紅色經典”再度風靡的時候,像《沙家浜》中的“智斗”一場,《杜鵑山》中的“亂云飛”、“家住安源”,《智取威虎山》中的“迎來春色換人間”“誓把反動派一掃光”“甘灑熱血寫春秋”等,都還受到人們的熱烈歡迎。不論今昔,拋開它們曾經的政治意義,單就唱腔來聽,還是令人百聽不厭的。至于念與做,樣板戲和傳統京劇就差別大了,傳統京劇中的各行當道白特點鮮明,往往他們開口一說,不用往臺上看,就能知道是什么角色,而樣板戲中就含混得多了,盡管也分,但特點不那么鮮明。尤其是做,傳統京劇和樣板戲可以說是各走一端,傳統京劇《貴妃醉酒》,唱腔的好不必說了,單就身段而言,那個美是極其經典的,前人備述盡矣,無需我再置喙。可樣板戲中的身段,一律走陽剛的路子,因為要表現英雄嘛,三突出就是要“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一個英雄怎能夠走起路來款款而行?怎能夠蜂腰窄步?傳統戲中的“做”都用不上了,像阿慶嫂、李鐵梅、方海珍,乃至后來的江水英、柯湘等,不論坐科還是戲校,都沒當重點教過,要說史無前例,樣板戲確是先河,可以想見當時演員們的改是何等艱難的事兒!
四
記得“文革”尾聲時期,人們開始厭煩了無休無止的運動,能躲就躲了。我那時住在早就當了逍遙派的姑父家。姑父喜歡古典音樂,不知他什么方法,從一個朋友家借來很多外國交響音樂、協奏曲、獨奏曲的唱片,因為不愿獨享,拉上一家人晚上掛上窗簾偷偷地圍坐在一起聽,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老柴的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那時候也不管什么資產階級什么封建主義,一種封閉很久的靈魂似乎要沖破頭頂上的束縛,野馬蒼鷹的去大千世界馳騁翱翔,為的是求得精神解放,聽點柔和的舒廣的,因為“鏗鏘”的東西打擊我們心靈太久了。為小提琴協奏的樂團記不得了,只知道小提琴的演奏者是奧伊斯特拉赫,一個絕不亞于海菲茲的俄羅斯演奏大師。他詮釋的柴可夫斯基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是我聽過的最好版本之一。那種美感囿于當時的環境,聽起來仿佛是來自于另外一個世界,那種愉悅屬于無知、乍一聽到,然后被強烈地感動了……仿佛找到一個久別的朋友,和你交談,向你傾訴,一霎時就懵懂了,“我這是在哪兒啊?”當時心里真就這么問自己,撩開窗簾,推開窗戶,真想讓所有的人聽一聽,分享一下,可外面仍舊是漆黑的夜。那時節,晚上九點鐘,街上就基本靜了,昏暗的路燈下,風吹得燈罩東搖西晃的……只有看到這些,才回到現實,才知道我還在這兒,“哦,剛才我聽的是外國音樂,是柴科夫斯基的D大調,是被稱之為蘇修那個國家的人。”
聽古典音樂的緣起,還是一位音樂學院靠邊兒站的教授和我閑聊時說起的。作為樣板戲的舞劇,一部是《紅色娘子軍》,另一部是《白毛女》。我家有個堂兄上海音樂學院畢業后就分到了上海舞蹈學校,在樂隊里擔任弦樂部的演奏員,凡是他們進京演出,都會有我的票,可以說是《白毛女》看得最熟了。可偏巧,在這兩部舞劇中,我偏愛《紅色娘子軍》。當時《紅色娘子軍》中的“萬泉河水清又清”這支曲子,可以說是人人皆會哼唱,按現在的話說,應該算“流行歌曲”了。“文革”末期時,政治環境不是那么咄咄逼人了,因為閑的,也無課可上。無聊之余,彈鋼琴解悶兒,那時可以放心大膽彈的曲子,革命的是理所當然地放在第一位,能涉及洋的,最沒事兒的就是練習曲,什么拜耳、布格繆勒、車爾尼299、599、849等。但是由于環境和每天超級灌輸的原因,不用看譜隨手就能來的就是樣板戲,“萬泉河”是其中之一,記得當時我反復彈這個曲子,碰巧那位教授買菜回來,推門就進來聊,他告訴我目前這支“萬泉河”的曲子不如以前杜鳴心寫的那首好,他從我眼神里看出狐疑就說,你不知道吧,我給你彈彈,不過你先得把門窗關了,免得讓別人聽見,又說我在這里散毒,我急忙把門窗都關嚴實了,靜靜地坐下來聽他彈,他一邊彈一邊告訴我,杜鳴心是留蘇回來的,曲子里帶點俄羅斯的味道,這可是封資修里面的“修”啊,要批判著學習,我當時的體會,他不是要我批判而是學習,可不能不把批判加在前面。
他的話引發了我去尋找外國的古典音樂的念頭。但是,真正從內心引起一種震撼的,應該還是樣板戲。因為聽音樂和看音樂又是兩碼事兒,聽的音樂你不是置身現場,很難體會那種真實的音響,銅管樂的嘹亮高亢,穿透與震撼,弦樂部抒情的廣緩、莊嚴,戲劇般地急速而熱情,當這些通過喇叭再傳到你耳朵里時,多少經過一些“過濾”,而現場,即便是有些“噪音”,那都是真實的美好……
傳達給我美好的,不能不歸功于《革命交響音樂沙家浜》和《鋼琴伴唱紅燈記》,當時為錢浩梁、劉長瑜、高玉倩伴唱的鋼琴,是著名的鋼琴演奏家殷承宗。有時我不得不感慨歷史上有些“異想天開”卻能成為一種“可能”。西洋歌劇演員不論是用鋼琴伴唱,還是用交響樂隊,他都要看指揮的手勢和要聽好從第幾小節起唱。京劇就不一樣
了,我們現在看每一部傳統京劇演出,可曾見過有指揮的?只有鑼鼓弦子彈撥樂器,這些被稱之為“場面”的,家伙一響,調門兒一出,演員自然就知道該從哪兒起唱。試想,用鋼琴伴唱京劇,沒有京胡“帶路”,“難度”是應該有一些的,更重要的不是這個,不是說這兩個藝術沒法兒往一塊兒碰,關鍵是碰到一塊兒是否能行?記得先父曾跟我們說過一個故事,他跟吳祖光先生是朋友,祖光先生跟先父說:“風霞讓孩子用鋼琴給她吊評劇嗓子……”當年我也就這么一聽,如今細想一下,怎么不可以呢,鋼琴伴唱《紅燈記》不就是鐵證嗎?但這個故事更重要是講了新鳳霞同志雖然身殘,但矢志于藝術的勇氣,著實讓人敬佩!
作為一種嘗試,西洋樂器介入民族傳統,在當時沒有傳統京劇可以比較的情況下,《革命交響音樂沙家浜》和《鋼琴伴唱紅燈記》很容易就被人們,尤其是年輕人接受了,不管演奏者和歌唱者磨合得有多難,可畢竟是成功了。據有關媒體報道:“2007年1月2日,40年前轟動海內的鋼琴伴唱《紅燈記》和首次國內公演的鋼琴組曲《紅色娘子軍》將在北京保利劇院隆重上演。屆時,這兩部作品的原創作者、首演者、中國最富盛名的鋼琴演奏家殷承宗先生將再次奏起40年前的熟悉旋律。”這就是風靡一時的“紅色經典”,過來的人重溫舊夢,80后的年輕人聽起來新奇好玩,大家拋開了“噩夢”,單純地作為音樂欣賞,聽時激動,過后或者津津樂道或者一笑了之,沒有了咬牙切齒的“痛恨”,它能存在下來,很能說明問題。其實,在“文革”時期,“封資修”的東西一律打倒,“封”的東西自不必說,“資”的東西和“修”的東西,人們噤若寒蟬,但是貝多芬、舒伯特、柴可夫斯基等人的作品也不能演,尤其是有一陣子大批德彪西,批無標題音樂,甚囂塵上。不知他們是怎樣對這些人進行階級劃分的,但總是知道,斷章取義是當時批判文章的一大特色。總之,交響音樂的作者可以打倒,這種音樂形式總還得保留,于是我就看到了我平生第一次領教的“交響音樂沙家浜”。
我第一次觀看演出的是上海樂團曹鵬指揮的這個節目,演唱者的名字忘記了,只記得當時倆眼只盯著演唱者后面的舞臺,從弦樂部到銅管部再到打擊部,那些發出令你贊嘆的聲音,你不得不佩服管弦樂隊的表現和力量,毋庸諱言,我們民族樂隊的深度與廣度尤其是低音部分,在音樂表現上,是有不小的缺憾的,聽了當時僅能聽到的這個“交響音樂沙家浜”,用震撼和感動來形容是不為過的。
“文革”十年,歲月荏苒。
讓我們記住應該記住的,總結應該總結的,然后輕裝上陣,去迎接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