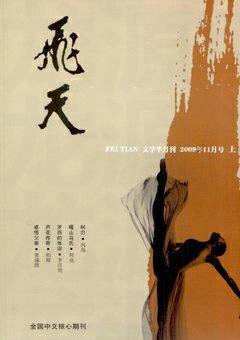一個欄目和一位編輯
汪曉軍
從《甘肅文藝》到《飛天》,60年即將過去了,這本立足甘肅、面向全國的純文學刊物,以其獨特的魅力,影響著一代又一代文學讀者,也培養和扶持了一批又一批文學作者,在甘肅這片大地上,說她是文學的殿堂、作家的搖籃,似不為過。記得在我少年時代,第一次讀到剛復刊的《甘肅文藝》,父親告訴我,有一部電影,就是根據這本雜志發表過的一篇小說改編拍攝的,叫做《昆侖山上一棵草》,霎時間,這本雜志在我眼里神奇而光彩奪目,我成了她的忠實讀者。后來,我在大學里終于看到了剛剛開禁復映的《昆侖山上一棵草》,影像之后,總有《甘肅文藝》的影子晃動,那感覺,有些特別。恰是在我讀大學期間,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撥亂反正,解放思想,國家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勃勃復興,《甘肅文藝》更名為《飛天》,成為校園文學社團十分歡迎的刊物。而《飛天》的編者們放眼全國,器局不凡,不但面向全國組稿,而且在全國文學刊物里率先開設了“大學生詩苑”欄目,受到大學生的熱情追捧。
“大學生詩苑”的創辦,有著良好的社會背景和基礎。當時,以傷痕文學為標志的短篇小說逐漸降溫,青春勃發的新詩,正在成為文學青年的時尚追求,大學生的傾情創作成為一道亮麗的文學風景。以蘭州地區的文學活動為例,影響廣泛的青年詩歌學會,就是以大學生為主體的。《飛天》在這樣的形勢下創辦“大學生詩苑”,無疑避開了地緣邊遠之弊,占盡了天時、人和之利。很快,這個欄目就在全國聲名遠播。最初幾輯,欄目還以甘肅及西北地區高校學生的作品為主,后來便是五湖四海匯聚。名牌大學的詩作者,許多也是從這里起步,走向全國,馳名詩壇的。
由于“大學生詩苑”,《飛天》在我們的校園,成為大家爭相傳閱的熱門雜志,每期一到,大家都想盡快知道誰的作品又上了“大學生詩苑”,這些同學的詩作,又出自校園的油印詩刊《我們》的哪一期上。而“大學生詩苑”的編輯,我們已經熟知了大名:張書紳。在我們的心目中,張書紳先生的形象,就和名字一樣,是儒雅名士型的文人,令人崇敬。那時候,《飛天》的不少編輯都曾來過學校,或參加文學社團的活動,或開講座,總是不見張書紳先生的身影,又讓我們多了幾分神秘。
我的同班同學董培勤,是校園里十分活躍的詩人之一,他發表在《飛天》上的組詩《唱給巴丹吉林的戀歌》,被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出版的新詩選本《紅葉集》,他十分高興,從書店買了好幾本送人。這一天,他特意告訴我,要去《飛天》文學月刊社,給張書紳先生送書,還要帶我一起去,讓我順便為他在東方紅廣場拍幾張照片,手持《紅葉集》,以志紀念。
實話說,見到張書紳先生,我多少有些意外。那些日子,我也見過不少的作家詩人編輯了,雖然形貌各異,個性有別,都還是有些所謂文化人的氣質。眼前這位在大學生中鼎鼎有名的編輯,卻是樸素得有些寒傖,普通得無以描述,說話是地方口音,抽煙挺兇的,與我們寒暄,是平易隨和的家常話。我的感覺,從外貌到言談,與我插隊時的鄉村干部沒有什么兩樣。說白了,土里土氣的,與我所見的文化人很不相像。想到就是這么一位土里土氣的人在操持著時尚、新銳、前衛、先鋒的“大學生詩苑”,我等時代驕子投寄的熱情洋溢的詩篇,須得經過他的檢視選擇,我還是有些愕然和茫然。好在董培勤與他熟稔,相互遞煙、對火,自然從容地聊了起來。董培勤的《唱給巴丹吉林的戀歌》,正是張書紳先生編發的,他很熟悉,他翻閱《紅葉集》,對這組詩居然和一流大詩人艾青等人的作品收在同一本書里,非常滿意。他們談起幾位著名的校園詩人的新作,張書紳先生好像沒有高談闊論的興致,間或一句“寫得不錯”,“有些空了”,“太實了”,就無話再說了。正在這時,我們的另一位同學王鈞釗(筆名黃祈)來了,遞給張書紳先生一疊詩稿。張書紳先生瀏覽一遍,又遞給董培勤和我傳看,也沒有直接的評價,只是說先放下,他回頭仔細看看。我這時候才注意到,狹窄的辦公室,四張辦公桌,兩兩倚墻擺放,編輯們是面壁而坐的,此時辦公室只有張書紳先生一人,我們就坐在其他編輯的椅子上。這么局促的辦公環境,當然不是我們可以久坐的地方,董培勤吸完一支煙,便招呼我們向張書紳先生告別,走了出來。
回學校的路上,董培勤、王鈞釗仍然很興奮,說起張書紳先生的認真、負責、眼光獨到,充滿敬佩。據說,張書紳先生批閱有修改基礎的詩稿,非常細致,很讓詩作者受益、感動。我記得我當時心情挺復雜的,當時我的書包里揣著相機,卻沒有勇氣提出拍個合影,有些懊喪;再就是我投稿多次,卻沒有見到張書紳先生的批閱意見,可見我寫的東西連個修改基礎都沒有,心里不免有些悻悻然。
這是我唯一一次見過張書紳先生,以后我雖然時常讀“大學生詩苑”,這習慣甚至保持到參加工作以后,我卻再也沒有見過這位編輯老師。不過,這一次的拜訪,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做編輯兩三年以后,毅然鼓動同辦公室的同事將辦公桌倚墻而立,多少是受了那一次張書紳先生辦公室的影響,而且工作效率明顯提高了一些。而當我每天拆閱大量來稿,手忙眼花腦袋發木,我才覺出,能說出“不錯”“空了”“太實了”幾句話,須得兢兢業業,保持頭腦始終的清醒,再若能寫出些比較得體的意見,不用功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進了出版行業,所見如張書紳先生一樣老農般樸素的前輩多了,我對他們學養豐富卻敏于行訥于言的行事方式崇敬有加,更不敢以貌取人了。后來,在甘肅省紀念共和國成立30周年的文學選本里,我讀到張書紳先生的一篇演唱材料,大約創作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通俗質樸,適合農民理解,我恍然明白,好的編輯,正是在不斷積累、不斷學習、不斷適應時代、不斷超越自己的。由此,才有了張書紳先生,才有了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大學生詩苑”。在《飛天》的發展歷史上,“大學生詩苑”是值得重彩描述的一筆。
從《甘肅文藝》到《飛天》,張書紳先生這樣的編輯,只是眾多資深編輯當中的一員;“大學生詩苑”,也只是許多精彩欄目當中的一個。之所以讓我銘記不忘,是我明白,一份好的刊物,支撐它的主干,還是一支有水準、有學養、有眼光、有奉獻精神的編輯隊伍,主干高標粗壯,自然枝繁葉茂,百鳥朝會,八方來儀。張書紳先生和“大學生詩苑”,就是一個縮影吧。我相信,《飛天》走過60年以后,新一代的編輯,薪火相傳,拜新時代所賜,一定會創造出更豐富更燦爛的文學成果。
責任編輯 子 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