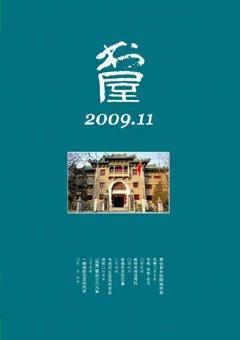爭鳴·寬容·民主
蔡家園
2004年春季印度大選之前,阿瑪蒂亞·森訪問一個偏遠、貧窮的孟加拉村莊,一位目不識丁的農民對他說:“想讓我們沉默不難,但那并不是因為我們不會說話。”這句話對森產生了強烈的震撼,他突然意識到:人們對于觀點的記錄與保存往往偏向于有權勢者或受過良好教育的人,而實際上許多有價值的觀點與下層社會成員有關。那么如何讓這些弱勢者自由表達出來呢?這就涉及一個重要的時代命題——如何保障大家都有說話的權利。森進一步展開了思考,在印度歷史上,有讓每個人自由表達的傳統嗎?假若存在自由表達,那又是通過什么樣的途徑實現的呢?這對于印度的今天,又有什么現實意義呢?
在人們的印象中,阿瑪蒂亞·森是一位卓有建樹的經濟學家。他的研究領域除了發展經濟學以外,在福利經濟學、社會選擇理論等方面亦是成就斐然。他出版了《貧困與饑荒:論權利與剝奪》、《理性與自由》、《以自由看待發展》、《身份認同與暴力》、《經濟發展與自由》、《集體選擇和社會福利》、《論經濟上的不平等》、《倫理學和經濟學》、《自由、合理性與社會抉擇》、《關于爭鳴的印度人:印度人的歷史、文化與身份論集》等十幾部專著。為了表彰他在福利經濟學和社會選擇理論方面的突出貢獻,以及他對于社會最貧窮成員所面臨問題的關心,瑞典皇家科學院將1998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他。森窮其一生研究如何根據社會公眾的生活狀況來評估政府的經濟政策是否得當,因而被稱作“經濟學界的良心”。其中,關于饑荒原因研究的著作影響深遠。他的研究成果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為有效地防止或減輕食物短缺提供了可行的解決方法,從而獲得世界性的聲譽。但是,森的思考遠不止于此,他總是越過經濟學領域,激情洋溢地進入哲學、政治、倫理學、社會學等領域,對人類文明的走向,對人的存在進行深入地探索。
與饑荒問題一樣,民主問題也始終是森思考的核心問題。
印度建國六十二年來,一共舉行了十四次大選,出現了七次和平的政黨統治輪替,除了1975至1977年因實行緊急狀態使民主制度一度中斷,印度民主的車輪一直正常運轉。在2009年4月至5月,印度進行了長達一個月的世界上最大規模的民主選舉,一千多個政黨參與競選,七億多選民參加投票。盡管國際社會對于印度民主進程也有非議,但是,民主在印度還是得到了廣泛認同。2007年,印度NDTV在全國展開過一項大規模的民意調查,超過四成的被調查者將“民主”看作印度最大的榮耀。在印度這樣一個種族、宗教、文化、語言千差萬別,人口眾多且相對貧困落后的發展中國家,民主體制良性運轉堪稱一個奇跡。一般認為,印度民主體制是英國殖民統治的遺產,歐美國家更是極力將印度褒獎為“世界最大民主國家”,視之為民主櫥窗,甚至企圖將印度拉入民主同盟,以在全球推廣西式議會民主制度。然而,印度人自己并不認為民主是西方的舶來品,而是發源于印度的古老文化傳統,如“超自然中心”、多元文化、村社自治(“潘查亞特”)甚至是種姓政治等傳統文化,阿瑪蒂亞·森則是持這些觀點的代表人物之一。
森認為,在印度文化中,民主表現的一種重要形式就是爭鳴,爭鳴過程中的自由表達是實現民主的途徑之一。他徹底放棄了西方視野而回歸到印度本土,希望從歷史的梳理中發掘印度文明中的民主文化,以推動當前的民主改革。通過對于印度爭鳴歷史的細致考察,他認為這種寬容對話的傳統對于今天印度民主制度的成功,對于捍衛其世俗政治,對于消除各種與階級、種姓、性別及社群有關的不平等現象,乃至對于南亞次大陸的和平事業,都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森認為,印度人喜好并且長于辯論的傳統始于公元前八世紀的奧義書時代。那時的人們討論祭祀儀式、物質、靈魂和人生奧秘等問題,意在尋求終極真理以及可以使人獲得解脫的知識,實際上是對于當時婆羅門祭司擅權腐化、祭儀繁縟現狀的反動。此后思考之風盛行,沙門思潮興起。沙門是當時出現的自由思想家的統稱,他們的觀點多與占統治地位的婆羅門思想相對立。公元前七至前四世紀的印度,是一個列國紛爭、動蕩不安的時代,思想上和宗教上也是百家爭鳴,宗派林立。喪失人心的正統婆羅門教陷于危機,佛教和耆那教等順應時代的需要,以各種革新面貌出現于歷史舞臺,并逐漸占據統治地位。
但是,森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對于歷史的考察并非在于強調論辯的成功,而在于闡釋論辯過程中的寬容精神。他認為,正是爭鳴體現了不同觀點之間的理解、體諒和尊重。他研究了印度歷史上四個偉大人物——阿育王、阿克巴、泰戈爾和甘地,通過他們的事例來說明,自由表達與充分寬容的精神在印度源遠流長,并對近現代的印度政治文明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阿育王(前272年~前242年在位)是孔雀王朝的第三位國君,曾經建立起古代印度最大的帝國。他殺掉了自己的兄長,通過激烈的爭權之戰獲得王位,后來又發動征服羯陵伽國的戰爭,造成了數十萬人傷亡。目睹了戰爭帶來的巨大災難,他開始幡然悔悟,決定改行和平國策,宣揚“正法”。“正法”即是少行不義,多做善事,以慈悲、慷慨、真誠、純潔為要旨,集中體現了當時積極的宗教道德。盡管他后來皈依了佛教,但他并不固守一己的信仰之私,而是以國事為重,竭盡全力消除當時已經發展得十分嚴重的教派沖突,并以詔書的形式強調,各教派要學會對話、學會互相尊重,通過教義上的爭論和切磋,消除彼此的對立,并逐步擺脫狹隘的宗派觀念。阿育王自己亦身體力行,誠懇與不同派別的宗教領袖展開對話,虛心聽取他們的意見。他的“正法”政策為經歷了數百年動蕩的印度社會帶來了較長時間的和平,階級矛盾和宗教矛盾明顯減少,百姓生活比較穩定。森很贊賞阿育王具有明確的宗教信仰,卻又能以世俗君主自期的行為方式。阿育王鼓勵不同教派的人公開表達自己觀點,體現出寬容的開明意識,森認為,這正是印度政治家民主意識的濫觴。
印度歷史上另一個具有寬容胸懷的著名君主是阿克巴(1557年—1605年在位),他是莫臥兒王朝的第三代君主。他執政期間推行開明政策,主動放棄了個人信仰的偏見,經常邀請各派宗教學者到宮廷中說法。與阿育王一樣,他還常將不同教派的領袖人物召集在一起,研討辯論宗教、社會問題,以消除誤解,化解矛盾,促進社會和諧。無論是伊斯蘭教、印度教,還是佛教、耆那教、祆教或基督教乃至無神論者,他都平等對待。他廢除了非穆斯林的人頭稅和香客稅,允許各宗教建立寺院,自由傳教,對于被迫改信伊斯蘭教的人亦聽任恢復原來信仰,政府不加干涉。政府的職位向所有人開放,不問其宗教信仰。每遇重大的非伊斯蘭教節日,皇宮也和民間一樣舉行隆重的慶典。1582年,他創立了一個具有泛神色彩的一神教——“圣教”,力圖將印度當時的所有信仰熔于一爐。他的這一嘗試最終失敗,但是他奉行的宗教寬容政策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給當時的印度社會帶來了和諧與繁榮。
森在對歷史的考察中還發現,印度歷代的統治者中不乏開明之士,像笈多王朝的三摩答剌·笈多、七世紀北印度的戒日王、十四至十五世紀的毗閾耶那伽羅王朝諸王等,都對不同宗教采取了寬容態度,容許各家爭鳴,善待異教信徒。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的寬容態度是不帶附加條件的,也就是說,并不以效忠本朝本教為異教存在的前提。在這些古代君主統治的時代,宗教寬容其實也就意味著政治寬容,平等爭鳴局面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社會和諧,推動了文明進步。
這種建立在寬容基礎上的爭鳴傳統在印度流脈不斷,到了近代則出現了兩位杰出的代表,那就是文學巨匠泰戈爾和政治偉人甘地。森討論的重點不在于他們的共性,而是他們的差異。因為出身、教育以及追求事業的不同,這兩位偉大的人物在思想理念上存在著巨大的分歧。比如,對于甘地在民族解放運動中提倡的手紡手織,泰戈爾對此不以為然,多有苛評。甘地相信它能夠使印度自我實現,均衡貧富,達到民族團結的目的;而泰戈爾則認為紡車沒有經濟上的意義,也不可能促使人思考。甘地后來喜歡獨身生活,泰戈爾則對兩性關系比較率性。甘地相信偶像在啟發民智上有其效用,泰戈爾則認為人民任何時候都不應被當做孺子來對待。在認識論上,泰戈爾相信科學,因而偏重理性;而甘地則有時會傾向于某種宗教性的臆斷,較為感性。關于民族主義、殖民主義、愛國主義、經濟與社會發展等問題,他們的看法也各不相同。森最感興趣的是,泰戈爾雖然對甘地的觀點多有批評,無所忌諱,但是對于他的品格卻極為欽佩。泰戈爾從未從個人角度批評過甘地,相反,對于他為祖國所做的一切努力,一直給予熱情贊揚。盡管他們之間存在著某些誤解,但這并不妨礙他們彼此直言,也從未傷害彼此的感情。觀點的分歧和對立,從未影響他們對對方的敬慕和尊崇。這無疑是一種偉大的情懷,在森看來,他們的身上延續著印度論辯、存異、寬容的美好傳統。
森在研究中發現,正是阿育王最早論述了寬容的必要性和非正統見解的豐富性,而且制定了指導辯論和爭執的規則,也就是“在所有場合,在每一方面,均充分尊重”對手,這充分保證了弱勢群體自由表達的權利。這一政治原則在印度后來的諸多討論會中得以實踐,逐漸成為印度政治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印度人爭鳴的種子播種在論辯的土壤之中,這種土壤的特征是寬容和忍讓。如此氛圍下形成的必是多元社會,這種多元性保證了近現代世俗主義的政體得以實施。允許弱勢群體自由表達,正是民主政治建立的基礎。當代印度奉行的現代民主制度,就是這樣逐步建立起來的。森煞費苦心地考察印度爭鳴傳統,既與他回到印度的立場有關,也是他意在從印度文明中發掘東方民主的因子,為解決世界性問題提供一種參照的思想體現。盡管當今印度的民主制度也存在種種不盡完善之處,但是森的努力讓人感受到一種赤誠和良知,自己的問題只能靠自己解決,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汲取歷史的經驗和教訓。
森關于爭鳴的考察的視野只放在了印度,假如他在東方文明中更深入一步進行考察的話,他將會發現,在另一個文明古國中國,同樣也存在著對話和爭鳴的偉大傳統。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被稱為中國“百家爭鳴”的時代。就在那時,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提出“和而不同”的思想,重視對話。這種觀點,也是在諸子百家爭鳴氛圍中營造出來的。“百家爭鳴”的形成,直接促成了思想對話的繁榮,也是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得以生成的基礎。爭鳴與對話向著“和而不同”、融會百家的方向發展,為中國后來的思想與文化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禮記·中庸》中說:“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這精辟地指出了中國古代自先秦開始的思想對話的價值觀念與思想方法。爭鳴是對話的表現形態,對話則深化了爭鳴,光有爭鳴而無對話,則可能走向對抗乃至于斗爭與毀滅。因而,爭鳴是需要道德約束的,那就是應該有一種寬容的胸懷。“百家爭鳴”的時代,彰顯了“和而不同”的中華文化的特點。在今天來看,這與印度的爭鳴傳統有著驚人的相似性。令人遺憾的是,爭鳴的種子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未能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綻放出花朵。
森說:“沉默是社會公正的強大敵人。”他在討論爭鳴問題時顯然是有著強烈的當下意識的。發表意見是追求公正的一個關鍵成分,允許發表意見則是實現公正的基本條件。爭鳴的傳統如果能夠積極運用,在抵制人類社會不平等現象和消除貧困及侵權方面當會起到良好的作用。就整個世界的發展而言,如亨廷頓所說,當今世界已經進入文明沖突的時代。種種文化的矛盾、宗教的矛盾、民族的矛盾都不可能依賴強權手段一勞永逸地解決,沒有哪一個權威能夠統治世界,人類和平相處的惟一途徑就是展開對話,在爭鳴中互相傾聽,加深了解,在寬容的心態下相互理解,積極合作,這是一種理性的姿態,也是最終達成世界和諧的通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