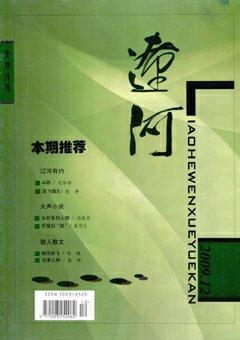冬天里的母親
崔新月
小村隆冬的早晨,從夢(mèng)鄉(xiāng)里那三兩片飄飛的雪花開(kāi)始。常常是剛剛從睡夢(mèng)中醒來(lái),還沒(méi)等睜開(kāi)眼睛,早已感覺(jué)到鼻子凍得冰涼,吸一下,呼吸已經(jīng)不再順暢,真冷。然后是母親瑟瑟索索下炕的聲音。睜眼看看,窗玻璃上凝結(jié)了厚厚一層霜花。我知道,外面早已經(jīng)是滴水成冰。我便蜷縮在被窩里,等母親把炕燒熱再鉆出被窩穿衣洗臉。
這當(dāng)然是稍微長(zhǎng)大一些的情景。在這之前,關(guān)于冬天清晨的記憶是這樣的,我穿上一件小棉襖,跪在窗前,用手在冰花上寫字或者畫畫,兼用嘴哈氣,讓窗玻璃透出一點(diǎn)光亮,好看清楚窗外陰冷的天色。夢(mèng)里的雪花并沒(méi)有真的飄落,但我常常看見(jiàn)母親推開(kāi)門外的雪,從院子里的雪堆底下掏出一捆玉米秸或者幾根干柴,急匆匆地回家,留下一個(gè)個(gè)歪歪扭扭的腳印。我看見(jiàn)她的短發(fā)隨風(fēng)飄起,像極了泥墻上在寒風(fēng)中抖動(dòng)的枯草。然后聽(tīng)見(jiàn)灶間風(fēng)箱拉動(dòng)的聲音,聽(tīng)見(jiàn)母親被煙霧嗆得大聲咳嗽的聲音,偶爾聽(tīng)見(jiàn)柴火燃燒的噼噼啪啪的聲音。透過(guò)朦朧的窗玻璃,我可以看到遠(yuǎn)處樹(shù)枝在風(fēng)中使勁搖擺著,可以看到前方幾戶人家屋頂上剛一露頭就被風(fēng)吹得無(wú)影無(wú)蹤的炊煙。我的嘴里哈出的那點(diǎn)熱氣并沒(méi)有讓窗玻璃明亮起來(lái),反而更加朦朧,直到什么也看不清,我想再重新弄出一點(diǎn)光亮,但是雙手早已經(jīng)凍得冰涼,便再鉆進(jìn)被窩。原本涼透的炕竟然有些熱氣,真好。只要有母親在,我的冬天就不再寒冷。
過(guò)了一些時(shí)候,母親帶著一身涼氣走進(jìn)來(lái),喊我們穿衣洗臉吃飯。雖然那飯菜沒(méi)有任何值得期待的,但畢竟能夠填飽肚子,而且能暖暖身子啊。吃完早飯,把碗筷收拾下去,冬閑時(shí)節(jié)沒(méi)有什么事情,母親就爬上炕,拉一床褥子蓋在腿上。我看見(jiàn)她的身體仍然在發(fā)抖。
現(xiàn)在想起來(lái),那個(gè)時(shí)候的母親或許是凍透了,我無(wú)法想象,她是怎么用自己溫潤(rùn)的雙手去握住凍得冰涼的家什的,無(wú)法想象,她在那一瞬間臉色是不是凍得鐵青,她的牙齒是不是一直在打戰(zhàn)。我想,那個(gè)時(shí)候的母親一定是凍透了,以至于多年之后,每到冬天,她總是那樣瑟瑟索索地走路或者做事,她那單薄的身軀必定經(jīng)受不住寒風(fēng)的侵襲,早已經(jīng)變成寒風(fēng)中的一片枯葉了。那個(gè)時(shí)候還算年輕的母親,卻已經(jīng)永遠(yuǎn)留在了冬天。
留在冬天的母親似乎很怕冷。或許是冰凍從她的指尖偷偷溜進(jìn)她的身體,然后把她的原本沸騰的熱血凍成了冰河。即使是坐在滾燙的火炕上,她的血液里也流淌著冰碴,那些無(wú)法融化的冰碴一定會(huì)刺痛母親的筋骨。所以,我還記得,即使是春天來(lái)臨,總還是有春寒料峭的時(shí)候,見(jiàn)我們想要早早脫了冬衣,母親總是厲聲勸阻,告訴我們春捂秋凍,千萬(wàn)別著涼。可是到了秋天,母親卻也是早早地穿上厚厚的衣服,在秋雨連綿的日子里總還是腰酸腿疼得整夜睡不著。
很多時(shí)候,我沒(méi)有注意到母親的冷,很多時(shí)候,我只是注意到了我自己匆匆行走的腳步,從冬天走到春秋,從童年走向成年,從兒子走成父親。我就這樣走著,看我的兒子咿呀學(xué)語(yǔ),繼而一天天茁壯起來(lái)。可是看看母親,她還在冬天里凍著。我用再厚重的羽絨服包住她,也已經(jīng)化不開(kāi)她身體里的冰層。即便是如今,我?guī)е迌夯剜l(xiāng),冬夜在母親炕頭享受著大火炕的舒適和愜意,清晨醒來(lái),母親也總是不知何時(shí)就早早下地,依舊用那瑟瑟索索的聲音燒炕,煮飯,然后喊兒孫起來(lái)穿衣洗臉吃飯。我以一個(gè)孩子的視角看著走在冬天里的母親,看她的皺紋一道道延伸到歲月深處,一直延伸到我的記憶里。
只要有母親在,我的冬天就不再寒冷。
可是母親呢,她是不是把自己燃成了一捆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