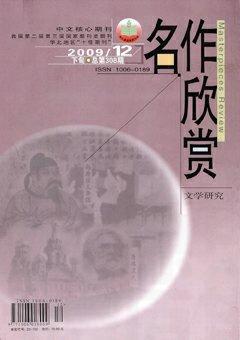沉穩平靜中的奮起與繁華
陳劍暉 王小玲
關鍵詞:當代散文 散文觀念 藝術創新
摘 要: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散文,雖不似小說、詩歌那樣大紅大紫、亢奮熱鬧,但散文也有自己的發展軌跡和品格。散文善于在默默無聞中積蓄力量,在沉穩平靜中奮起前進,并在上世紀90年代之后到新世紀之初達到其創作的高點,形成繁華似錦的局面。其特征是:一、走向大氣的散文格局和理性精神的增長;二、是心靈世界的開拓與生命的體驗;三、是藝術思維的多元化和文體的解放。當前的散文要發展,還必須進一步打破常規,一方面要堅持個人的體驗;另方面要面對現實生活,面對真實,面對大地,要將個人性與社會、時代及與人類共有的體驗連接起來。
一、對六十年散文創作的總體評價
20世紀50年代以來,與小說、詩歌的大紅大紫、亢奮熱鬧相比,當代的散文創作在大部分時間里都是沉穩平靜,甚至可以說是默默無聞,是十分冷落蕭條的。即使被譽為“散文時代”的90年代以來的散文創作,在我們看來同樣尚未達到80年代鼎盛時期小說創作那樣的“轟動效應”。但影響力不及小說詩歌或者說整體的思想藝術成就不及“五四”時期的散文,并不意味著當代的散文創作沒有成就,沒有“熱點”和“亮點”。事實上,當代的散文創作的可貴之處,正在于它善于在默默無聞中積蓄力量,在沉穩平靜中奮起前進,并在上世紀90年代之后到新世紀之初達到其創作的高點,形成繁華似錦的局面。這是散文創作與其他文體創作的區別之處,也是我們必須正視的一個文學事實。
在描述當代散文創作六十年的歷程時,我們首先必須看到:當代散文創作是在一種“斷裂”的文學史背景下起步的。“斷裂”作為一種歷史存在的事實,作為一種文學史現象和文學史敘述,它不僅存在于散文,也存在于中國現當代的小說、詩歌和戲劇創作中。但相較而言,散文創作中的“斷裂”現象尤甚。就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散文創作來說,“斷裂”首先是與“五四”的散文傳統、散文精神“斷裂”;其次是與散文的審美性、與自由自在的表達“斷裂”;第三是與個人體驗、與個性和自我“斷裂”;最后是與散文的多元化和多樣化的“斷裂”。而“斷裂”的結果,是散文的人文精神喪失殆盡,散文的群體意識得以強化,與此同時散文的個人性和審美性則日益削弱。總而言之,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散文由抒寫自我的人生經驗,由多樣化地表現生活變為單一地記敘戰斗故事,歌頌新的生活或英雄或勞動模范的事跡;散文的品種則由過去的寫景抒情、自由聊天和獨語變為單一的報告文學或通訊特寫。比如50年代初期傳誦一時的《誰是最可愛的人》,以及《英雄城——平壤》、《萬古青春》、《生活在英雄們中間》等作品就是“通訊特寫式散文”的代表作。難怪有人這樣說:“新中國初建的頭幾年中,不論是從體制或風格的基本傾向看,中國當代的散文,實為40年代‘延安散文的延續。”①遺憾的是,當時這種普遍存在于散文創作界的價值觀念、審美意向和情感心理狀態或者說“斷裂”的散文創作姿態,并沒有被散文創作者和散文研究者意識到,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了五六十年代“通訊特寫式散文”的盛行以及后來衍化為“詩化散文”的創作傾向。
回顧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現于中國散文界的“詩化散文”現象及其在藝術上所取得的成就,我以為采取非歷史主義的虛無態度,隨意否定隨意抹殺是并不可取的做法。誠然,這一時期的散文創作帶有明顯的“政治+詩意”的意識形態烙印,同時由于過分強調宣傳的功用,從而使作品的內容普遍地過于虛假,作家不敢敞開心靈講真話,而在抒情方面又體現出自我封閉、人格萎縮的特征,在藝術結構上則表現出模式化、雷同化的弊端。即使如此,我們也不應一概否定五六十年代的“詩化”散文。因為這時期的散文在意境的營造、意象構成的比興化,以及語言錘煉上的優雅精致等方面,都有值得后來的散文學習借鑒之處。因此,我十分贊同吳周文教授的觀點。他認為17年尤其是60年代前后出現的“詩化”散文是取得了一定的藝術成就,對當代散文的發展是作出了貢獻的。“我們不能因為這時期的散文受到‘左的思想的影響,不能因為它們欠缺真實性而否認其在藝術上的成就,這樣的判斷并不是歷史主義的態度。”②也就是說,我們一方面要看到散文在特定的歷史時期臣服于政治、自我矮化的困境;一方面又要看到這時期的散文在皈依傳統,追求散文的審美性上所作出的努力,并在文學史的背景上給予準確的評價和確認。
正是抱著這樣的理解和立場,我不同意一些散文研究者將20世紀80年代的散文說得一無是處,更不同意所謂的“末路論”和“消亡論”。③在這些“消亡論”、“末路論”者看來,整個80年代的散文簡直是一派冷落蕭颯的景象,期間除了幾位老作家之外,偌大的整個散文界幾乎空無一物。然而事實并非如此。早在20年前,在《論新時期散文的藝術發展——兼與“散文消亡論者”商榷》一文中④,我們就對此做出了回答。在我們看來,80年代的散文,在告別了“挽悼”散文之后,在作家的隊伍、題材的開拓、主題的挖掘和藝術表現手法上都有所拓展。這時期,巴金、秦牧、孫犁、楊絳、陳白塵等一批老作家煥發了青春,寫出了《隨想錄》、《干校六記》、《將飲茶》、《老荒集》、《晚華集》、《云夢斷憶》等一批敢于“抒真情,說真話”的作品。除此之外,以賈平凹為代表的一批中青年散文家的崛起,壯大了當代散文的創作隊伍。特別是賈平凹,在80年代,他先后出版了《月跡》、《愛的蹤跡》、《人跡》、《商州初錄》等一批散文集,不但數量多,且以其獨特的“味道”和“語調”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賈平凹的散文創作,代表了80年代散文創作的最高水準,甚至其質量和影響一度超過了他的小說創作。80年代的散文創作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即女性散文作家特別活躍。這時期較有名的女性散文家有王英琦、葉夢、蘇葉、唐敏、周佩紅、李佩芝、韓小惠、呂錦華、曹明華等等,在短短幾年間出現了這樣一個女性散文作家群,而且其作品都有鮮明的個性,達到了較高的藝術水準,這在過去的散文史上并不多見,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散文“末路論”、“消亡論”的荒謬可笑。當然,與轟轟烈烈的小說、詩歌、報告文學創作相比,80年代的散文創作的確是較為平靜平淡的。這里有散文作家自身的散文觀念、審美情趣、藝術修養等方面的問題,也有文藝體制、社會環境、時代氛圍等方面的原因。這一切都預示著:在80年代,散文創作的春天尚未到來。
散文創作春天的到來或者說,一個真正散文時代的到來,應是在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這一時期,由于政治的相對寬松,散文生態環境的改善,加之公共空間的拓展和出版界的推波助瀾,以及小說家、詩人和學者的加盟,散文創作的隊伍空前擴大,當代散文一改以往的邊緣姿態,一躍成為最受讀者歡迎的“時代的文體”。當然,也有人認為90年代以來的散文繁榮是一種“虛熱”,是“繁華遮蔽下的貧困”,是“蒼白”與“浮躁”的世紀末的大眾狂歡,甚至斷言當今的散文已進入了“侏羅紀末期”。然而,對90年代以來散文創作的有意貶低乃至冷嘲熱諷,除了讓讀者看到一些批評家的“酷評”本性,以及固執的學科偏見外,這樣的“酷評”并不能改變90年代以來散文創作的整體成就已遠遠超越了詩歌、戲劇和報告文學,甚至可以與小說創作比肩這一事實。因為每一個客觀公正的批評家或研究者都應看到,這時期的散文不僅是最受讀者、出版家歡迎的文體,而且這一時期還出現了諸如史鐵生、韓少功、王小波、張承志、賈平凹、余秋雨、王充閭、周濤、張煒、劉亮程等一大批優秀的散文家,這種盛況在以往是很少見到的。再說,這時期的散文一方面數量極大;一方面則是精品迭出。比如,史鐵生的《我與地壇》,賈平凹的《秦腔》,韓少功的《夜行者夢語》、《性而上的迷失》,張承志的《英雄荒蕪路》,王小波的《椰子樹與平等》,余秋雨的《這里真安靜》,劉亮程的《寒風吹徹》等等,都是思想性藝術性俱佳,經得起時間檢驗,甚至有的是可以傳世之作。特別值得指出的是:這時期還出現了不少新的散文品種,比如“文化大散文”、“學者散文”、“思想散文”、“新散文”、“新媒體散文”,乃至“小女人散文”、“行走散文”、“打工散文”等等,這些散文品種可以說都是90年代以后的產物。至于散文觀念的現代化,散文表達上的自由自在,散文藝術形式的多樣化,散文表現手法的各種革新,也是這一時期散文的特點。這一切都彰顯了這樣一個事實:90年代以來的散文創作不但超越了“十七年”和80年代的散文創作,甚至可以這樣認為:它的總體成就已經十分接近“五四”時期的散文了。而更可貴的是,這時期的散文創作不像小說和詩歌那樣急功近利,不是“跑馬占地”就是“各領風騷三五天”,而是根據自己的本性,按照自己的節奏和步伐,雖平靜緩慢但是穩健扎實地向前邁進,而這正是散文繁榮的可喜標志之一。
由于篇幅所限,我們無法全面探討六十年散文創作的起落興衰的原因,也無法對各時期散文的思想內涵和藝術特征作全面的梳理分析,我們只是在對六十年來散文創作進行整體把握的前提下,考察各時期散文的總體創作傾向和感情基調,并在此基礎上重點考察90年代以來散文創作的特征和變化。
二、變革中的散文新因素
20世紀90年代以來散文創作的開拓和創新是全方位、多方面的。比如在散文品種上,出現了以余秋雨為代表的“文化大散文”和張中行為代表的“學者散文”,這兩類散文的題材選擇、價值取向和藝術志趣都大異于以往的散文。此外,通俗閑適散文的崛起,也開拓了這一時期散文的題材領域。不過在這里,我們擬從散文創作的格局和精神,從人格主體、個性的復蘇對創作主體心靈世界的開拓與生命的體驗,以及藝術思維的多元化和文體的解放三個方面,來探討變革中散文出現的新因素。
新因素之一:走向大氣的散文格局和理性精神的增長
90年代的散文之所以超越了十七年和80年代的散文,一個明顯標志,就是散文越來越走向大氣。不容否認,90年代也有許多只停留于小山小水,書寫個人的一點小小悲歡的“小景”散文;但同樣不容否認,90年代也出現了不少大氣的散文。這些散文的一個共同特點,一是篇幅長(有不少超過萬字);二是這些作者都傾向于思考各種大命題。比如,史鐵生的《我與地壇》、《隨筆十三》,思考的是生與死、命運與生存的問題;韓少功的《夜行者夢語》、《性而上的迷失》、《佛魔一念間》,探討的是“后現代”、性的形而下與形而上、宗教與人心等問題;張承志的散文篇幅雖然不長,但他對于時代、國家、民族、宗教,以及如何活得美,活得崇高和戰勝污臟卑小的思考同樣具備了大命題的內涵;而周濤的《游牧長城》、《鞏乃斯的馬》,則是人的意志與嚴酷自然環境的對峙,在對歷史的追問和思索中表現出大氣魄。
其他像郭保林寫黃河、寫秋天的篇什,像林非的一些散文,不僅寫得大氣,且透出學者的人間情懷。而更重要的是,這種大氣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內在的呈現。這種大氣是一種理性精神的內化,一種博大的情懷,一種人格智慧的閃光。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作品不但寫得大氣,有較高的文化品位,而且自始至終透出一種理性精神。這是十分可喜的新散文現象。因為如前所說,在以往的散文觀念中,人們一直認為散文應寫得優美精致,而且只適宜于抒情而不長于說理,加之中國人天生傾向于感悟而不善于理性思辨,這就使得自“五四”以來我國散文中的理性精神十分薄弱。盡管80年代中期,也有一些散文家力圖對歷史和生命進行思考,但因知識儲備的不足或思想認識的局限,這些帶有理性特征的散文總的來說還不盡如人意,更缺乏世界優秀散文中的那種理性力量。
而現在,余秋雨等人的散文,卻把這種理性精神的立足點上升到20世紀現代人文的哲學高度。比如余秋雨,他的散文不是沒有抒情的成分,也不是舍棄敘事與描寫,不過構成他散文的重要部件,卻是他的獨到的文化眼光和理性議論。他從從容容、有條不紊地介紹他所經歷的名山古跡特別是書院、藏書閣一類的文化重鎮,分析其歷史背景、考證其文化源流、描述活躍于其中的人事,還時不時結合個人對歷史的感受和理解,穿插進一些富于情趣又體現了作家的人格色彩的議論,于是,透過那些獨到的議論、深邃的剖析和自省,讀者不僅感受到中國文化的韌性和苦難歷程,中國文化人的悲劇性命運,不僅感覺到作家本人對中國文化的摯愛、不倦的求索和求索中的苦澀而又不乏悲愴的心境,同時也體驗到一種理性的力量、理性的美。而這樣的散文創作格局和理性精神,無疑是對以往散文的超越。
新因素之二:心靈世界的開拓與生命的體驗
十七年的散文,由于受到政治氣候的影響,總體來看過于強調“文以載道”,強調外在地歌頌與抒情。散文作者一般都不敢面向心靈世界,真實地袒露自我。80年代,雖然出現了巴金等一批“說真話”的作品,但因這些散文在藝術上沒有新的突破,終不免給人以淺白直露之感。而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這一切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首先是葉夢的“新潮散文”,她以意識流的表現手法,輔之以隱喻、象征、暗示等藝術技巧,大膽地袒露了女性在初潮來臨、做新娘時的期待、喜悅和恐懼的心理活動。如果說,葉夢的散文,在坦露心靈世界時還不夠自然從容,過于晦澀費解的話,則程黛眉、斯妤的散文,顯然自然成熟多了。程黛眉的《如期而歸》,以十足詩意的筆調,靈動飄忽的情思,寫一個女孩子在“深秋的落葉紛紛搖曳”的黃昏的心路歷程。這篇散文沒有按照時間邏輯順序進行程黛眉語言編排,而是讓情緒的片斷、生活細節隨著“如期而歸”的意識流動自行涌,因而它是無序的,不確定的,但卻是心靈化的、個性的。程黛眉的許多散文,比如《浪人的家園》等,都具有“內心獨白”的特點,每一篇幾乎都是一次心靈的跋涉。斯妤是90年代以來頗受讀者歡迎的一位女散文家,她的作品的最引人注意之處,便是對于“心的形式”的探究。在《心的形式》、《心靈速寫》、《幻想三題》等作品里,斯妤從女性的角度,將外在社會現實與內在生命相融合,心理的時間與物理的時間相交織,于是,人生的短暫,青春的逝去,對往事的苦澀回憶,現實的苦難,宇宙的永恒,便超越了具體的人生經驗,而升華為“心靈的模式”,以及對人類終極意義的追問。在90年代的散文中,能夠從“心的形式”探究人的生存狀態和生命意義,而且內容和形式結合得較完美的作家,應該說還不是很多,因此斯妤在這方面的努力才顯得彌足珍貴。至于斯妤的后繼者如胡曉夢、曹曉冬、王子君、于群等人,她們的“心靈獨白”一方面表現了年輕一代的理想和人生態度;另方面證明了散文的“向內轉”,已經成了一種時尚、一種趨勢。
90年代的散文,在重視抒寫心靈的同時,十分注意人生的感受和生命的體驗。在這方面,史鐵生的散文堪稱典范。他的《我與地壇》借地壇的一角,思考死與生、命運與生存意義等永恒問題,史鐵生顯然沒有張承志的激烈狂傲,他也不像張承志那樣發誓要獻身于一場“精神圣戰”,但他們對于人性的體察,他們為人為文的高貴卻是相通的。史鐵生以對人世的洞察和至宥至慈的寬容,對苦難做出了一種完全迥異于世俗的解釋。他發現了苦難也是財富,虛空即是實在,而生存不僅需要勇氣,更需要選擇,需要承擔責任與義務。他從地壇,從古園的老樹、荒草、鳥蟲、墻基、青苔感受到生命的純凈與輝煌,萬物的永恒與和諧,而這一切,均離不開他的輪椅,離不開他的靜思和自語。
新因素之三:藝術思維的多元化和文體的解放
藝術思維的多元化,首先帶來了敘述方式的變化。敘述,本來屬于小說詩學的范疇,由于它帶有虛擬性的因素,過去的散文家對此并不重視。可是近年來,一方面由于小說家的加盟;另方面由于散文家們對傳統的單一而權威的“我”的敘述方式的不滿,同時對散文的“想象和虛構”問題有了新的理解,這樣敘述問題便越來越成為散文家的一種藝術的自覺。舉例說,在傳統的散文中,一般采用第一人稱的“我”展開敘述,而且這個建立在“真實”基礎上的“我”具有不容動搖的牢固地位,別的敘述方式皆因有悖于散文的“真實原則”、怕造成“閱讀障礙”而遭到擯棄。而現在不少散文中的“我”竟消失了,或者在一篇散文中,在“我”之外又有其他敘述視角,如余秋雨的《這里真安靜》,史鐵生的《我與地壇》,鐘鳴的《旁觀者》,桑桑的《旗語》等作品,就有這樣的敘述特點。再如在敘述中大膽吸收其他文類的特長,再輔之以象征、隱喻、通感、意象組合等表現手法,從而使敘述豐富而多變。如劉燁園、鐘鳴、葦岸等的散文就常用此法,這種敘述方式在以往的散文中極少見到。凡此種種,都使我們有理由確信:進入90年代,散文的敘述已經由單一走向開放,由確定明朗變為模糊和非確定。
藝術思維多元化的第二方面,是散文中大量出現了建立在藝術感覺上的意識流動。即是說,在90年代,作為一種現代創作方法的“意識流”表現手法的介入瓦解了傳統散文按部就班的敘述和描寫進程,使散文表現生活的空間驟然擴大了。比如上面分析過的程黛眉的《如期而歸》,斯妤的《心的形式》、《心靈速寫》、《幻想三題》等作品就是如此。它們沒有簡單地根據順敘、倒敘,插敘進行組合,而是伴隨著意識流動,讓時空切換、場景重疊,現在、過去、未來交錯。不過我們也注意到,也許由于更傾向于內心,受理性的約束較少的緣故,女性散文家在“意識流”手法的運用上較男性作家更為普遍,也更為出色。像周佩紅的《偶然進入的空間》、《一抹心痕》,斯妤的《心靈速寫》,馬莉的《黑色蟲子及其事件》,蝌蚪的《家·夜·太陽》,黑孩的《醉寨》等作品,幾乎都是以情緒的奔涌加以隨意拼貼連接;或者,捕捉偶然浮現的情緒、感覺,乃至幻覺、潛意識,將散文寫得虛幻又真切,呈現一種靈動朦朧且不確定的詩的意蘊。當然,這方面走得最遠的是一批更為年輕,被有的批評家稱為“新生代”的作者,比如胡曉夢、于君、曹曉冬、黃一鶯等等,她們的散文不僅在思想內容方面向傳統發起了大膽和直率的挑戰。在藝術方面,則是淡化敘述的現實,增加虛構和想象的成分,讓一個個的意象,一系列的動作、感覺、潛意識紛至沓來,它們像一連串大幅度游移跳躍的音符,構成了散文的外在狀態和內在的律動。
藝術思維多元化在第三層面的表現,是散文結構的開放性。我們看到,90年代以來的散文已經徹底告別了傳統的“三段式”結構套路,而呈現出形態各異的結構狀態。像史鐵生的《我與地壇》,其外在結構是記述“我”與“地壇”的緣分,以及活躍在“地壇”的人對“我”的生命拯救。由于作者在敘事時將過去時態中的“我”、精神世界里的“我”和寫作時的“我”交錯重疊,再加上作者在描述中又穿插進關于“四季”的天籟般的想象,以及諸如“小燈籠”之類的意象不斷重復出現,于是,《我與地壇》的結構便呈現出這樣的特點:它一方面條分縷析、層層推進,直迫生命的內核;另方面又虛實相間、伸縮自如,顯示出極大的結構上的張力,這種表面看起來似散漫和不經意,而內里卻無懈可擊、十分縝密的結構形態,的確顯示出史鐵生過人的藝術功力。此外,周佩紅的《偶然進入的空間》,趙玫的《以愛心,以平靜》,韓小蕙的《有話對你說》等散文,采用的也是這種以“情緒”、“意象”為線索的結構方式。至于在“新生代”那里,采用“情緒—意象式”的結構方式就更普遍了。這也從一個側面顯示了90年代以來散文隨筆的開放和進步。
通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90年代散文正在發生著變化,即散文不但更加真實,而且更加貼近心靈,貼近人生,貼近生活本身了。散文的這種變化,是時代生活的變化使然,也是散文家們更新散文觀念的結果。這一方面表現了散文的自覺;另方面也提高了散文表現生活的深度和廣度,使散文發揮出更大的作用,同時更易為讀者接受。
三、關于新世紀散文的幾點思考
散文在90年代以后獲得了全面的豐收,形成了建國以后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但現在還不是高奏凱歌,盲目樂觀的時候,因為在散文繁榮的背后,的確還存在著“蒼白”與“虛浮”的現象。因此,在肯定散文創作成就的同時,我們還要進一步拓展散文的思想藝術空間。我以為,面對新世紀的散文,我們思考和解決好如下幾個問題:
散文如何進一步強化個性,解放心靈的問題。
新世紀的散文要發展,還必須進一步解放心靈。如果有很多的思想顧慮,有很多的精神束縛,怎么能寫出自由瀟灑的散文呢?我們讀一些散文,覺得作者很真誠,題材很有意思,文字也很好,就是寫得太拘謹、不夠灑脫,這正是心靈還不夠解放的表現。我們看一些古代散文家寫的散文,包括現代的周作人、梁實秋、林語堂等人的散文,都是自由自在,心靈是較解放的。這樣即使他們寫得很隨便平淡,但是里面有一種內在深沉的東西。今天我們正處于一個改革開放的時代,我們的散文要敏感而真實地表現出我們時代中最有詩意、最激動人心的畫面,倘沒有精神的解放,心靈的自由,那么我們的散文創作將永遠落后于時代生活,無法創作出既體現了現代人的理想追求、精神氣質,又具備較高藝術水準的大作品。正是基于這個原因,我十分贊同林非先生關于散文現代化的意見。我覺得散文的現代化問題,實際上也就是心靈解放的問題。有了現代意識,有了新的文化精神,就能夠沖破落后、保守、僵化的東西,建造起全新的當代散文的大廈。
散文必須進一步打破常規。
散文要繁榮,還必須打破常規,一切為我所用。散文的本質在于一個“散”字。“散”,即以“自然”的形態和真實的情感體驗追蹤不斷發展的生活,這是散文特殊的審美功能,也是散文有別于其他文體的重要標志。魯迅說,散文的體裁是大可以隨便的,便是將散文當作很散漫的文學形式來看待。蘇軾將散文比作“水”,說它“隨物賦形”,不擇地而出,流到哪里算哪里,大概也是取其“散”,取其沒有條條框框的意思。但當代的有些散文家散文卻有很多條條框框。五六十年代是“詩化”、“形散神不散”,是楊朔、秦牧、劉白羽的條條框框,到了時下,又有“文化大散文”等的條條框框,仍然在束縛著許多散文家的手腳。這樣怎能寫出真正自由自在的散文呢?因此,我們的散文要超越前人,就要敢于用越軌的筆,寫出一大批離奇古怪,甚至是“四不像”的東西來。這是時代和讀者對于當代散文家的要求。
散文如何面向現實生活的問題。
考察當代六十年的散文創作,我深感當前應大力倡揚散文面向現實生活,面對大地的“在場”寫作,以此來抵御一味迷戀歷史后花園的文化大散文寫作,以及迎合俗眾的商業寫作,還有幾十年如一日的風花雪月、小橋流水的寫作。當然,面向現實生活,面對大地的寫作也是形態各異的,不能一概而論。比如,張煒、劉亮程筆下的鄉村大地,固然美好富于詩意,但往往被過度美化,它們離真正的現實還有距離。以周曉楓為代表的“新散文”寫作,有較強的個人的體驗,有獨特的表現生活的視角,他們的散文十分強調“在場”,但是過于推崇個人性,甚至把個性推向極致,反對將個人性與社會、時代和人類聯結起來。
此外,“新散文”的某些散文為了反對崇高、反對優美、反對抒情,故意展示一些生活中很丑陋的東西,這不是一種健康的寫作。相較而言,我們較欣賞夏榆的《白天遇見黑夜》這樣用下層人的眼光來看下層人的生活,有作者的血肉和痛感觸貫其間的作品,只不過,《白天遇見黑夜》境界還不夠高,還需要精神和美學上的提升。
由此可見,當前的散文一方面要堅持個人的體驗,要有獨特的生活視角,要有生命的投入,有感情的溫潤,有精神性的維度;另方面應面對現實生活,面對真實,面對大地,總之要將個人性與社會、與時代、與人類共有的體驗聯結起來,這樣當代的散文創作才有可能迎來一個生機勃發的散文的時代!
作者簡介:陳劍暉,華南師范大學教授,中國現代散文研究中心主任;王小玲,廣東青年干部管理學院講師。
① 佘樹森:《當代散文之藝術嬗變》,《北京大學學報》1989年第5期。
② 吳周文:《20世紀散文觀念與名家論》,遠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頁、第46頁。
③ 黃浩:《當代中國散文:從中興走向末路》,《文藝評論》,1988年第1期。
④ 《新東方》1990年創刊號。
(責任編輯:呂曉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