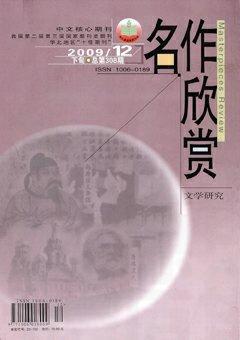西部民間倫理與西部鄉土敘事
關鍵詞:雪漠 生存狀態 西部民間倫理 精神生態系統 創作視界
摘 要:雪漠的系列長篇以沙漠邊緣沙灣村的普通農戶老順一家的日常生活為背景,真實地還原了西部農民的生存狀態,敘寫了現代性背景下普通農民痛苦而艱難的精神裂變的過程,揭示出西部貧窮的根源在于欲望的膨脹和西部人巨大深厚的精神惰性,而西部人的精神生態系統也限制了作者的創作視界。
2000年,上海文化出版社推出西部鄉土作家雪漠的長篇小說《大漠祭》,并在小說封面上稱之為“真正意義上的西部小說和不可多得的藝術精品”,引起了評論家和讀者的極大關注,小說不僅多次再版,還進入了中國小說學會2000年度小說排行榜,獲得“第三屆馮牧文學獎”等,《獵原》獲2004年度“中國作家大紅鷹文學獎”。雪漠小說中充滿艱辛與磨難的西部農村生活和西部農民自然原始、粗獷堅硬的個性,以及他們在苦難中頑強堅守的西部精神與倫理,深深震撼了讀者的心靈,為讀者提供了一個新奇陌生的審美想象空間,那種獨特的生存方式像田園牧歌一樣充滿了詩意,仿佛一縷清新的風滋潤著那些沉溺于欲望之海中浮躁、焦渴的心靈。
一、西部民間倫理是維系西部農民生存的精神紐帶
《大漠祭》之后,雪漠連續推出系列長篇《獵原》、《白虎關》等,以西部鄉土敘事而備受文壇關注,這幾部長篇都以騰格里沙漠邊緣沙灣村的普通農戶老順一家的日常生活為背景,《大漠祭》真實生動、飽含深情地敘寫了西部農民艱難、嚴酷、悲涼的生存境遇和他們堅韌、頑強的生命力,在現代性背景下,沙灣村人那種類原始的生存方式和民間道德理念不可避免地受到外來文明的侵襲,首先是自然生態因物欲的膨脹和生存的艱難而受到嚴重的破壞,并直接威脅到他們的現實生存,即使身兼三種身份——農民、牧民、獵人,依然難以維持他們最基本的生存與尊嚴,他們不得不繼續向沙漠索取,向戈壁深處的沙窩去謀生存;在《獵原》中,他們還得應付那些偷獵者和外部文明所帶來的外國投機者、手機、電視、碟機、明星照、進口面包車等現代化符號的誘惑,沙灣村已經不再是原生態的、孤立的西部鄉土的“存在”了,它成了現代化觀照下西部沙漠邊緣的一個鄉村。大漠這個渾厚、酷厲而又蒼涼的文化意象,是即將逝去的一種文明形態和生存方式的象征,它沉寂千年,充滿苦難又飽含溫情,雪漠在新世紀的鐘聲里讓世人看到了原始而又悲愴的存在,這群農民勤勉、誠實、頑強、豁達、堅韌地活著,西部的生存環境是闊大、雄渾、嚴峻而單調的,他們有生之艱難、死之無奈、病之痛苦,也不乏愛之甜蜜,盡管他們的觀念有時顯得保守封閉愚昧,但是他們有自己獨特的人生哲學,有足以在艱難環境中維系生存的強大的精神紐帶。
《白虎關》延續了前兩部的故事和人物命運,小說的線索是為猛子娶媳婦,猛子不斷與村上的有夫之婦茍且讓老順覺得丟臉和虧欠了兒子,決定不惜代價為猛子說媳婦,夫妻倆還一廂情愿地想讓瑩兒嫁給猛子,既節省了彩禮,又可守住唯一的孫子。圍繞這一中心事件,老順家和瑩兒娘家展開了一系列的矛盾沖突,而一切矛盾的根源就在于一個“窮”字,而“窮”是相對的,作者尖銳地指出窮的根源在于人的欲望的膨脹。白虎關沒發現金礦前,大家都窮,貧富懸殊并不太大,外面的世界對沙灣村的刺激遠沒有近在咫尺的黃金那樣讓人難以忍受,老順等村民既無財力又無膽識去金窩子討生活,艷羨、嫉妒、仇恨等情緒就在沙灣村逐漸蔓延,猛子和花球偷雙福礦上的金沙被捉,被迫當沙娃又險些送了性命,于是,他和北柱掘了雙福家的祖墳,倆人墳時的對話深刻揭示了部分農民內心的扭曲與矛盾,他們承認雙福們的錢是“掙死掙活掙來的”,但雙福們的富顯出了他們的窮,雙福給村里修學校、給村人發錢羞辱了他們,挑戰了他們固有的價值觀,反而加深了村人的仇恨。“二兩酒喝一天”與“喝得起酒,喝不起時間”是截然不同的人生觀和價值觀,雪漠覺察到西部農民貧窮的文化心理根源和巨大深厚的精神惰性。仇富、掘人祖墳,從新舊道德的立場上看都是為人不齒的行為。雙福女人秀秀打心眼里蔑視掘墳者,她說掘墳者“最終把自己心里的一種東西給掘了”;她認為雙福是條“漢子”,“誰的墳,是誰自己掘的”。她對雙福的評價是中肯的,盡管在《大漠祭》中,她拒不接受20萬元的離婚費。她見識非凡,對人性的剖析透徹犀利,讓人感佩之余心生畏懼,猛子覺得她“成精了”。秀秀是雪漠系列長篇中最具有現代意識和獨立人格的人物,雖然作者將農村社會的各種矛盾聚焦在她身上,使她處于生存的困境中,但她異常清醒的現實主義精神和自主意識還是讓人覺得她在代作者立言。雪漠將她塑造成了沙灣村的“智者”或“旁觀者”,另一個是孟八爺,但孟八爺是沉浸于其中的,他身上更多農牧文化的精神素質。
在《白虎關》中,雪漠在努力探索農村貧窮的根源,并將觸角深入到人性的最隱秘陰暗的角落,他沒有簡單地將思索停留在外部社會,而是向文化心理的縱深處開掘,他的剖析是客觀深刻而公允的,既無有意識的拔高,也沒有韓少功式的夸張變形,他選擇以原生態的生活真實震撼讀者的心靈,并在事實上超越了《大漠祭》和《獵原》中對西部精神的歌詠,對農牧文明的盲目懷戀,顯然,農牧文明的田園牧歌并不是抵抗現代工業文明的良藥。他痛苦地發現將苦難崇高化的夢想已經無法抗衡現代物質文明對西部農民的強烈誘惑,西部農民的欲望在外來者或異質文明的刺激下正在畸形變態地膨脹,并逐漸形成了一種頗具毀滅性的阻力,不僅阻礙經濟的發展,甚至有可能對人性善惡和人的健康人格的形成和發展造成負面的影響,沙灣村那些損人不利己的思想行為,那種愚昧落后的思想觀念和陋習,以及人們對人性遭受踐踏的那種熟視無睹,諸如換親習俗,甘于貧窮,貪戀閑適,對女性人格尊嚴的肆意踐踏等等,也許這才是西部農村貧窮的根本原因,這種價值觀和文化心理才是阻礙人類進步的最大阻力。從這一層面看,小說立意高遠,比周大新的《湖光山色》更加深刻厚重,發人深省,但是,由于作家地處西部,宣傳力度不夠,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小說相對松散的結構和散文化的筆法使小說的敘事節奏和故事性不及《湖光山色》,在可讀性上略遜一籌。
二、西部農民精神生態系統艱難而痛苦的現代轉型
如果說《大漠祭》和《獵原》中女性是情節發展重要元素的話,那么《白虎關》就是一部西部農村女性生存、掙扎與奮斗的悲歌,蘭蘭的自我意識在一系列災難打擊下開始覺醒。對婚姻、親情、戀情先后絕望的她,把精神寄托在修行之上,而宗教也被庸俗功利的村人們褻瀆,經過痛苦的反思,她毅然走出金剛亥母洞,決定自我救贖,她和瑩兒毅然決然地承擔起為各自兄弟娶妻的責任。在貧窮落后的西部農村,為自由、愛情、尊嚴而抗爭在親人眼里是荒唐的,五四新女性的追求竟顯得那樣奢侈。在現實中,當人對現世人生絕望時就會求助于宗教或神明,當作家無力解決現實人生的矛盾與困惑時就會下意識地選擇由女性來承擔災難,激發或培育能夠拯救世界的男性,張賢亮、張煒的大多數作品在小說情節發展的關鍵處,都讓女人來拯救男人(肉體上或精神上),進而由男人來拯救世界,這種敘事模式早已被女性主義譴責和批判過。雪漠期望女性從經濟上解放男性潛在的力量,幫助他們成長。難道金錢真的能拯救猛子懵懂混沌的心靈,難道富裕真的能改變白福賭博打老婆迷信愚昧殘忍(他為生兒子遺棄并致女兒死命)的精神惰性嗎?
我們承認雪漠小說那透骨的真實,西部農村的民間道德倫理規范有它的獨特性和地域性,它對人的評價標準與現代城市有很大的差異,那始終是一個男性中心的社會,勤勞肯干、誠實守信是男人賴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素質,其他的缺陷都可忽略不計,而女性卻沒有最基本的尊嚴和人權。現實如是,作家卻不能僅僅做一個時代的記錄者,而應站在全球化、現代性的高度對西部農村社會的變遷、人心的善惡進行審美的關照。雪漠扎根西部、書寫西部,其心其情真切可感,但愛的方式似可商榷。魯迅先生對童年時代的朋友閏土在同情之余更多的是批判,而雪漠卻沉浸于西部人近乎原生態的精神生態系統之中,且影響了他對生存和生命本身的深層體驗,影響了他對現代性關照下的西部農村現實生存與發展走向的準確把握。小說對西部生存方式和道德倫理的認同,對猛子等人的寬容,都限制了作者對思想文化的挖掘和藝術想象力的飛揚。猛子在系列長篇中經歷了兄弟的生離死別,接受過保護生態環境和野生動物的思想教育,經歷了偷情戀愛,親眼目睹蘭蘭和瑩兒的災難與掙扎,偷過金沙和豆子,掘過雙福家的祖墳,開過金窩子,參與過械斗等等,遍嘗人間百味,卻始終冥頑不靈。而見識非凡、心高氣傲的秀秀緣何與他糾纏不清呢?是本能需要,還是為了報復丈夫的冷漠與背叛,或者是跟猛子之間產生了朦朧的愛情,好像都不是。秀秀無形中成為猛子成長的工具,秀秀的言行缺乏邏輯上的合理性和完整性。猛子的反思是成長的希望;而白福、花球、北柱、白狗、王禿子等卻正在放逐著自己曾經堅守過的西部精神,或以暴制暴,或向潑皮無賴滑落,這使我們憂慮而恐懼。對他們的同情和憐憫,不僅削弱了小說的現實批判性,還使敘事陷入了無意義的循環。關注轉型期西部農民如何活著固然重要,考察他們為什么這樣活著,怎樣活得更好,是一個人文知識分子神圣的使命。
面對冥頑不靈的猛子們,作者理性批判的鋒芒消失了。在西部荒原上猛子們俯拾皆是,蒼涼的荒漠還無力自發形成啟蒙者,老順、孟八爺、秀秀、瑩兒似乎都無力承擔,靈官還在漂泊的路上。猛子精神上的惰性是可怕的,他成長的艱難是由于作者對他的嬌縱,對鄉土的深沉眷戀影響了作者的價值判斷,限制了小說人物和情節的設置。或許猛子的設置是為了揭示西部生存的艱難和西部人精神成長的曲折,猛子既沒有許三多的幸運和機遇,也沒有《奮斗》中那班80后的自負和優越。無論初衷如何,猛子都讓人覺得如鯁在喉,他就像一塊沒有開化的頑石,物質和精神的貧乏使人的成長更加艱難,這或許就是猛子作為“這一個”的獨特魅力吧。
三、雪漠如何超越西部人原生態的精神生態系統
雪漠習慣于在小說的前言或后記中表明自己的創作意圖和審美價值取向,《獵原》的題記是“在心靈的獵原上,你我都是獵物”①,《白虎關》有一篇很長的后記。雪漠對許多讀者將《獵原》作為環保小說來讀頗有微詞,認為是誤讀。在文學閱讀中產生“誤讀”的原因大致有兩個:一是讀者的思想深度和閱讀水平有限,導致誤讀;一是小說本身無法完成作者所賦予的使命。《獵原》被誤讀應屬于第二種情況,即作者的創作意圖和思想高度,文本無力承擔,文本呈現的是關于野生動物保護的斗智斗勇的故事。唐達天(甘肅作家)的《沙塵暴》也敘述了人類如何與自然抗爭,沙漠步步緊逼,不斷侵蝕著人的生存空間,村人被迫移民新疆的悲壯與蒼涼,作者對人與自然、對現代文明渴盼的急功近利與對故土深沉的眷戀、市場經濟模式與傳統小農經濟等一系列矛盾的揭示,以及西部農民在外來經濟文化沖擊下的痛苦的精神裂變,都使讀者無法將它作為一部環保小說來對待。《獵原》的敘事拖沓冗長,線索單一,人物的傳奇性沖淡了人物內心世界的開掘,故事性、抒情性、地域性增強了小說的可讀性,卻削弱了小說思想的深刻性。
雪漠說:“我僅僅是想定格一種即將逝去的存在。”②作者的創作理想和審美追求自然無可厚非,巴爾扎克曾說自己是法國社會和時代的記錄員,賈平凹也曾在《廢都》中真實深刻地記錄了一個知識分子在社會轉型期所經歷的精神與肉體裂變的過程,小說因表現力和性描寫等問題招致非議,也給作者帶來煩惱。雪漠的確寫活了“一戶農民”,但這種原生態的、“活化石”式的生存模式在現代化進程中注定是要消亡的,記錄之外如何評價?是站在全球化或者至少站在中國現代化的視野下,在歷史文化的長河中來觀照它,還是站在沙漠的邊緣或者西部的某一高處來審視它、懷戀它?李建軍對《廢都》的批評很多都是中肯的,如果作者能超越現實生存層面,進入存在與文化層面對莊之蝶的人生進行審美觀照,小說就會向《紅樓夢》和《生命不能承受之輕》等經典再靠近一步。小說的格局要大,作家的精神境界和創作視界就要更加高遠。雪漠和賈平凹的作品在思想和藝術上都還有打磨、鍛造的必要和空間。
雪漠表現的是一種“靜默地忍受”的道德,老順的口頭禪是“老天爺能給,老子就能受”,但是,隱忍并不能帶來現代化,也不能阻止外來文化的沖擊和鄉土文明消亡的趨勢,如何積極面對,是雪漠和“老順們”共同的難題。早在2004年,雷達先生就注意到雪漠小說創作視界褊狹的問題,他指出:“除了沙灣這個小社會之外,雪漠還能知道多少東西?他會寫沙灣小社會,會不會寫之外的大社會?或者能不能把沙灣小社會放到大社會中去看?我覺得,他需要一種東西文化撞擊后的眼光。”③遺憾的是,《白虎關》并沒有完成這種超越。雪漠表示老順系列已經完成,以后的創作將有新的格局,但能否超越自己,關鍵在于作者能否在文化心理和精神層面完成對西部農民原生態的精神生態系統和倫理規范的超越,站在全球化和人類性的高度審視和關照現代化進程中的西部鄉土和農民。近年來,雪漠醉心研究佛教文化,他的研究能否對全球化經濟大潮下人的精神信仰危機有所裨益,并與他已有的文化心理結構相交融,成為其文學創作的精神文化資源,還很難預測。
作者簡介:李清霞,西北政法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博士后。
① 雪漠:《獵原》題記,見《獵原》扉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② 雪漠:《白虎關》后記,見《白虎關》,上海文藝出版社,2008年8月。
③ 雷達:《雪漠小說的意義》,人民日報海外版,2004年6月18日第8版。
(責任編輯:呂曉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