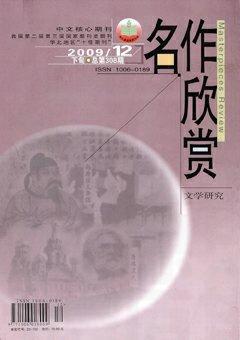剛柔間的游走
關鍵詞:生存 意義 當代 小說
摘 要:當代小說常以歷史或現實為媒介,以文學形象為符號,傳達對人性和生存意義的探討,做出關于生存意義的文學闡釋。本文選取四部有代表性的當代小說作為觀測點,嘗試對20世紀八九十年代小說中有關人性和生存意義的闡釋做一粗略描述,并對闡釋間的關聯,以及與當代社會形態變遷的聯系略做探究。
生存是古今中外思想家、文學家始終關注的大問題。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莎士比亞借哈姆雷特之口說:“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當代小說常以歷史或現實為媒介,以文學形象為符號,傳達對人性和生存意義的探討,做出關于生存意義的文學闡釋。本文選取四部有代表性的當代小說作為觀測點,嘗試對20世紀八九十年代小說中有關人性和生存意義的闡釋做一粗略描述。
一、尋覓家園的青春歌謠
家園是生存的根,有關尋覓家園的故事是探討生存意義的永久話題,《黑駿馬》是這類小說的杰作。
《黑駿馬》有表里兩層結構:表層是一個感傷的愛情故事,里層隱含著尋覓家園的主題,而尋覓家園的主題則是通過“歸來——離開——再歸來”的結構模式體現的。離開草原的“我”,成為一個不良少年,于是被父親送回草原。由于在草原之外生活過,“我”的思想中便有了一些不同于草原的準則,特別是有關婚俗的法則,最終又離開草原,走入城市。但是城市的生活法則,又是“我”完全無法接受的。在《黑駿馬》中,草原與城市成為截然對立的兩個世界。草原是民間世界的象征,城市是主流社會的縮影。“我”漂泊尋覓的過程,正體現了人物回到民間世界、離開民間世界、最終回歸民間世界的歷程。
《黑駿馬》所描繪的民間世界的美好,在于它擁有愛和寬容。而這愛和寬容在《黑駿馬》的民間世界中,主要是通過女性形象去表現的。“我”想:“女孩總該比男孩純潔些,就像索米婭比我要純潔一樣。” “女孩總該比男孩純潔些”,是《紅樓夢》“女兒是水做的骨肉”這“女尊男卑”觀念的當代翻版。《紅樓夢》的理想世界是大觀園,那是一個女兒國,是一個逃離男權壓迫的避難所,在這里大觀園表現了對男權世界的反抗。人類數千年來的社會形態主要是男權社會,文學中對主流社會的反抗常常是以反抗男權的面目出現,《黑駿馬》所展現的草原理想世界帶有濃厚的女性色彩,其本質也是對主流社會的一種反抗。《黑駿馬》似乎在說明著疏離主流社會的民間世界,才是人類生存的最好家園。
二、至剛至烈的生命歡歌
《紅高粱》被文學史家譽為新歷史小說的代表,其實是用抗日歷史外衣包裹著的人性傳奇,是在戰爭與愛情、死亡與新生的交響里講述的人性故事,是至剛至烈的生命歡歌。
《紅高粱》所歌頌的是蔑視人間法規的愛情。奶奶和爺爺的相愛,既違反法律又違背道德,但他們的愛情卻又是合乎人性的自由的男歡女愛,他們的愛情追求是對建立在金錢基礎上的婚姻的反叛,這就使這一違法而不道德的戀情變得合情合理,而這對敢愛敢恨敢哭敢笑敢作敢為的男女更得到作者的熱烈贊頌。《紅高粱》在戰爭的背景下、在死亡的陰影里,書寫愛情,書寫情欲,書寫愛的渴求與生的歡狂,將生命的活力張揚到了極點。
作者對爺爺、奶奶們充滿敬意與熱愛,他崇敬的是這些人所構成的充滿野性的民間世界——一個極端矛盾的統一體:“最美麗最丑陋、最超脫最世俗、最圣潔最齷齪、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愛”;“他們殺人越貨,精忠報國”。爺爺、奶奶等人似乎是《水滸》中草莽英雄在當代小說里的復活與再生。作者以現代人的“種的退化”與之對照,更凸顯了民間世界的強悍有力與勃勃生機。
如果說,當初《黑駿馬》對民間世界的認同還有些遲疑,到了《紅高粱》則是斬釘截鐵、義無返顧地謳歌民間世界,并對民間世界的道德觀、價值觀給予充分的肯定。如果說,當初《黑駿馬》對生命和人性的描寫還有些剛中帶柔,而到了《紅高粱》,則是在戰爭與愛情的交響中,表現死的莊嚴與生的歡狂,并將至剛至烈的人性張揚到了極點。
三、磨蝕生命的凡俗哀嘆
《一地雞毛》被文學史家譽為新寫實小說的代表,它在對現實做出另類的描述和解說中,闡釋了作者對生存本質的認識。
比起“一地雞毛”,“豆腐”的意象在小說中更為突出,它貫穿始終,意蘊豐富。小說由“小林家一斤豆腐變餿了”開始,到“老婆醒來,見他在那里發傻,便催他去買豆腐。這時小林頭腦清醒過來,不再管夢,趕忙爬起來去排隊買豆腐”結束。“豆腐”成為凡俗生活里最為重要的東西,它代表了凡俗生活的全部內容、全部追求和全部目的;而它也象征著被生活所磨蝕的生命,漸漸變得如豆腐般軟弱稀松而不堪一擊。豆腐即人生,人生如豆腐。作品活生生地勾畫出人對現實無可抗爭的處境,揭示出這處境的荒謬。這種諷刺精神來自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知識分子對自己所賴以安身立命的人生原則的絕望,從根本講是社會人生的一大悲哀。①
由《一地雞毛》可以看出,文學在20世紀90年代初,已從《紅高粱》至剛至烈的人性張揚,走向了以陰柔取勝的生存策略,這折射了文學由社會中心逐漸向邊緣的隱退,表現出作家由個性張揚走向情感內斂的時代特征。
四、至陰至柔的生存寓言
與《紅高粱》所張揚的至剛至烈的人性相比,《活著》剛好表現的是生存的另一極——至陰至柔一極。
“這是一個寓言,是以地區性個人經驗反映人類普遍生存意義的寓言。”②作者如此闡釋這寓言的內涵:“《活著》講述了一個人和他的命運之間的友情,這是最為感人的友情,因為他們互相感激,同時也互相仇恨;他們誰也無法拋棄對方,同時誰也沒有理由抱怨對方。他們活著時一起走在塵土飛揚的道路上,死去時又一起化作雨水和泥土。”③顯然,《活著》試圖闡述的,是一種以苦難命運為友的生存策略。
《活著》的主人公在經歷了富貴、別離、戰爭、饑饉以后,在父母妻女及所有的親人都相繼離世以后,仍然堅持生活了下來,并且活得有滋有味、自得其樂。“‘皇帝招我做女婿,路遠迢迢我不去,不僅顯示了一種達觀的生活態度,同時也意味了對自我身體的珍惜。注重自我的肉身、自我的感覺,注重生活的當下感,把活著作為生活的全部理由,用以對抗所有迎面而來的幸與不幸。此時“人身對自身的在世短暫性和有限性的恐懼和憂傷被一勞永逸地克服了,有限人身與無限恒在的亙古裂傷被徹底解決了”④。
《紅高粱》與《活著》,從至剛至烈到至陰至柔,在剛柔的兩極間完成了從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有關生存意義的文學闡釋。
五、在剛柔兩極之間
20世紀80年代前期,多元經濟形態的試行,思想解放運動的開展,拓寬了國人生存的思想文化空間,而這一切折射到文學創作中的一個突出現象是,在主流文學中民間社會與民間世界的耀眼登場。非主流的民間價值觀、世界觀在文學作品中一再得到作者們的肯定與認同,從《黑駿馬》到《紅高粱》可以粗略地看到民間世界在文學中的從嶄露頭角到如火如荼。伴隨著民間世界崛起的是人的覺醒。80年代“人性”、“人道主義”的論爭使啟蒙主義的人文理念融入主流意識形態體系之中,人的自信、歷史的自信使80年代的中國文學洋溢著樂觀主義的氣息,而以《黑駿馬》、《紅高粱》為代表的80年代中國文學作品則更是揮灑出人的創造歷史的激情。電影《紅高粱》讓我爺爺跪向紅襖紅褲、仰臥如大寫“人”字的我奶奶,正是用影像對80年代人性覺醒的最好描寫與概括。
但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改革的挫折和隨之而來的政治風波,同時也挫敗了國人的自信,“大寫的人”在不知不覺中悄悄萎縮成一個如當時的流行歌曲所唱的“小小的我”。而在這一時期的文學主流——“新寫實小說”中,更可以感受出現代人的逐漸萎縮。“80年代后期改革的挫折不僅激蕩起社會普遍的貧困之感,同時更深刻地引發了人對自身的懷疑,對自身的能力、信仰、道德觀念、倫理準則等方面的自信心逐漸喪失。在當下時勢的起伏變幻中,人發現自己不能改變什么,也不能把握什么,人對歷史無能為力;同時,人對自身也失去了把握,變幻的時勢沖擊了曾經的信念,人變得茫然失措,無所適從。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們的自我認同發生了危機。”在《一地雞毛》、《活著》中,創造歷史的激情消失殆盡,“剩下的只是人無法掌握命運的無力感,是歷史的無從知曉、未來亦無從把握的頹廢與傷感。”⑤
在《黑駿馬》、《紅高粱》誕生的時代,社會需要文學充當思想解放、改革開放的急先鋒,文學的啟蒙話語始終居于意識形態體系的中心地位,此刻小說中的自我主體便自信強大,勇于反叛,充滿激情,富有生命張力。然而,到了《一地雞毛》、《活著》出現的時期,一體化意識形態體系伴隨一體化經濟形態體系的瓦解而云散風流,文學在政治地位和經濟利益方面逐漸被邊緣化,文學家需要更多地直面普通人生存的艱辛,并開始趨向認同妥協的合理。于是,小林在現實生活的凡庸中拋卻了當日的理想激情,專注于買豆腐帶孩子收拾大白菜等日常生活瑣事,對比《黑駿馬》、《紅高粱》等以理想主義對抗庸俗生活的作品,我們不難看到這種自我喪失背后的是文學家話語權力的失落。《一地雞毛》、《活著》等“新寫實小說”所呈現出的主體失落表明,在90年代由于社會的轉型與話語權力的易位,文學的啟蒙話語的中心地位已經動搖,社會醞釀著新的價值選擇。⑥
從《黑駿馬》浪漫理想的青春激情,到《紅高粱》至剛至烈的生命張力,代表了80年代生命闡釋的剛性基本特征。從《一地雞毛》對荒誕生存困境的無奈與絕望,到《活著》以苦難命運為友的生存策略,代表了90年代生命闡釋的柔性基本特征。生存意義的文學闡釋在剛柔兩極之間的游走,折射著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社會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的變遷。
作者簡介:田衛平,北京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① 參見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316頁。
② 比利時《南方挑戰》雜志對《許三觀賣血記》的評價也適用于《活著》。載《許三觀賣血記》,海南出版公司,1998年第1版,封底。
③ 余華:《活著自序》(韓文版),海南出版公司,1998年第1版,第3頁。
④⑤⑥ 許志英、丁帆主編:《中國新時期小說主潮(上)》,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551頁,第524頁,第525頁,第531頁,第542頁。
(責任編輯:呂曉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