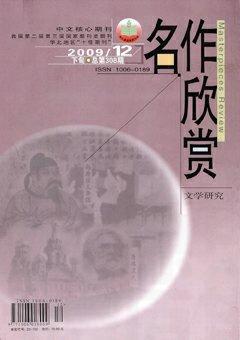卡夫卡小說美學的理論與實證
關鍵詞:卡夫卡 內在真實性 荒誕 小說美學 生存 本質
摘 要:卡夫卡認為,小說所能做的就是深入挖掘事物的本質,表現潛存于荒誕體驗中的生存真相。卡夫卡不是像近代作家那樣按照現實的本來面目來反映現實,而是對現實進行了系統而徹底的變形,他著力表現的是事物所具有的“內在真實性”。通過藝術視角的置換,卡夫卡發現并充分表達了現代西方人類對荒誕的社會現實的真切感受,獲得了空前深刻的藝術真實,表現出卓越的藝術技巧,極大地推進了西方小說美學的變革。
文學作品是作者對世界、生活以及人自身的感悟和體驗的藝術表達,它的基本特征是真實,它必須表現特定時代、特定人群的生活真相。但隨著歷史境域、社會環境的急劇變遷,文學的真實觀必然要發生相應的裂變。如果要對現代西方文學真實觀念的演變作一描述的話,毫無疑問,卡夫卡占有重要地位,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卡夫卡被公認為“現代文學之父”,他是現代小說藝術的拓荒者,變形、荒誕、悖謬、反諷、寓言、象征等現代小說技巧都能在他這里找到源頭。
在卡夫卡的創作中,西方小說的價值體系開始全面解體,傳統小說視作生命的真實觀被卡夫卡徹底顛覆。小說不再是人類感情的歷險,而只能是對人類荒誕存在的藝術觀照。正如美國學者埃利希·海勒所說:“始終無法解釋的是卡夫卡的寫作藝術:那是一種似乎暢通無阻穿過原始森林的散步,又好像在一個管理得很好的花園中徜徉;一種做出正在把結打開的姿勢,而實際上卻把結拉得更緊的努力;一種打開所有可以用得上的燈,卻同時把世界推入黑暗中去的力量。”{1}在卡夫卡看來,生存的本質是那樣的荒誕,世界的非理性是那樣的觸目驚心,以至于人對自身產生了深深的懷疑和負罪感。小說的任務不是徒勞地去摹寫這個混亂的世界,而應深入挖掘事物的本質,表現潛存于荒誕體驗中的生存真相。
為了窺得卡夫卡偉大小說藝術之一斑,這里主要以他的小說創作作為考察對象,通過對其小說藝術的分析,勾勒出卡夫卡小說美學的基本形態。
一、“內在真實”——卡夫卡小說美學的基石
西方文學歷來注重真實,美真同一是最高的審美價值。由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闡釋和倡導的“摹仿說”主張藝術的終極目的就是真實地摹仿自然。柏拉圖主張超現實的真實、本質的真實;亞里士多德認為文藝不僅能反映現象世界已然的真實,而且還能反映必然的和理想的真實。他們奠定了西方藝術真實觀的基礎。此后經過二千多年的演進,美真同一的價值觀被確立下來,真實成為藝術的生命,嚴格地摹寫自然成為永恒的藝術追求。“真是什么?真就是我們的判斷與事物的一致。摹仿性藝術的美是什么?這種美就是所描繪的形象與事物的一致。”{2}這種美真同一的價值觀的哲學基礎正是傳統的理性主義。
而我們在閱讀卡夫卡的小說時,可以一目了然地分辨出其藝術風格的現代特征來。這種特征最顯著的標志就在于,卡夫卡不是像近代作家那樣按照現實的本來面目來反映現實,而是對現實進行了一種系統而徹底的變形,以至我們在作品中所看到的都是一些在現實當中不可能發生的事情。比如格里高爾一覺醒來就變成了一只大甲蟲;K明知城堡就在眼前,卻永遠也無法走進去;藝術家竟然以饑餓表演為自己的職業等等。顯然,這類離奇的故事情節在成熟的近代小說中是根本不可能出現的。
其實,卡夫卡著力表現的就是事物所具有的那種“內在的真實性”。這種真實性與事物的外表特征并不一致,因此只有人為地對事物的外部形態進行變形,才能將其挖掘和表現出來。正是這種對于事物“內在真實性”的強調,把卡夫卡與表現主義藝術聯系了起來,同時也說明卡夫卡的藝術觀念具有鮮明的非理性主義思想背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可以把表現主義分為兩種形態:一種是主觀表現主義,強調藝術要表現藝術家的自我;另一種則是客觀表現主義,強調藝術要表現事物的內在真實,而卡夫卡顯然就屬于后一種形態的表現主義。由于摒棄了那種一味強調藝術家自我和情感的藝術觀點,因此卡夫卡十分反對表現主義詩歌喧鬧、浮躁的文風,轉而采取了一種平實甚至刻板、貧乏的語言風格。不過,在這種平實的背后卻隱藏著對于現實的系統扭曲,也隱含著卡夫卡藝術風格的全部秘密,值得我們加以深入和全面的分析。
在具體的創作手法和創作風格方面,卡夫卡以表現主義為主色調,同時又兼收并蓄,融入了一些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因素。縱觀其全部創作,可以發現卡夫卡早期作品就側重描寫形而下的現象世界,受現實主義手法和風格影響較多。《美國》就是一部現實主義風格較為明顯的作品。小說采用傳統現實主義作品慣用的流浪漢故事結構,圍繞主人公的行蹤,描寫了美國社會的貧富懸殊、勞資對立,以及工人結社、罷工游行和資產階級黨派斗爭等,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比較接近《匹克威克外傳》這類作品。作者本人在日記中說這是一部“狄更斯式的長篇小說”,它的某些篇章是“對狄更斯不加掩飾的模仿”。只是我們覺得它似乎比狄更斯更加冷靜和客觀,作品中出現了更多的怪誕畫面。
除此之外,卡夫卡的大部分作品都運用現代主義的表現手法,側重描寫形而上的抽象世界,屬于真正的“卡夫卡式”的現代主義作品。但就其藝術淵源而言,這些作品與浪漫主義風格的聯系較為明顯,其中淵源最近的當屬德國浪漫派。歌德是浪漫主義的開拓者,早在18世紀70年代,以他為首的作家所發動的“狂飆突進”運動,就發出了藝術應重視內心創造的呼聲,這些思想與卡夫卡十分合拍,卡夫卡多次表示要把歌德作為藝術典范。進入19世紀,德國浪漫派的代表人物是病態詩人諾瓦利斯、文學“鬼才”克萊斯特和善寫鬼魅故事的霍夫曼等。卡夫卡喜歡讀他們的作品,并在藝術手法上有所借鑒。{3}卡夫卡作品中那怪誕的夢魘世界、超現實的童話式情節、魅影般的人物、日益向人逼近的孤獨感和恐懼感、朦朧費解的寓意及神秘的藝術氛圍,在上述作家的作品中都程度不同地出現過。
不過,卡夫卡也沒有完全舍棄現實主義的某些手法。比如,他的小說結構相當完整,情節線索分明,戲劇性強,收束簡潔有力。如《變形記》開端突兀,迅速進入沖突高潮;接下來,人物的行為與其心理掙扎相互呼應,懸念的布置逐層遞進;小說結尾既干凈利落又余音繞梁。整個小說顯示出一種古典現實主義的質樸風格和藝術美。此外,卡夫卡的作品還表現出整體荒誕與細節真實的辯證統一,即小說的中心事件是荒誕的,但陪襯中心事件的細節大都是真實的。如《城堡》中的主人公請求批準在村子里落個戶口卻永遠做不到,這是荒誕的,但他為了實現這一目的所采取的種種行動又是日常生活中司空見慣的事情;《審判》的主人公突然被莫名其妙地宣布逮捕,這顯得違背常理,但他清洗自己“罪行”的心理動機及為此而作出的努力卻合乎邏輯;《變形記》除了“人變甲蟲”這一事件令人瞠目以外,其他有關主人公心理及他與家人關系的描寫,都符合客觀真實及心理真實。這些作品的生活環境也并非是幻想的超自然之地,而是人們常見的原野、村舍和公寓。這里沒有仙女,沒有點石成金的巫師和法術,有的只是普通人物。
當然,卡夫卡作品中也有很多怪誕的場面,它們跟現實生活有很大差異。這些奇特場景的美學效果是復雜的:其一,作為生活中極其平凡的小事,它們可以揭示現實的惡濁、悖理,并阻止讀者進入傳統小說那種人為構置的詩意幻想;其二,它又可以使讀者與現實保持一定的距離,讓他們在形而上的靜觀中獲得對現實的整體領悟。據此,英國評論家埃德溫·繆爾認為卡夫卡的寫作特點是“現實主義與寓言的交織”{4};盧卡契說,在卡夫卡筆下,“那些看起來最不可能、最不真實的事情,由于細節所誘發的真實力量而顯得實有其事……所以卡夫卡作品整體上的荒謬和荒誕是以現實主義基礎為前提的”{5}。卡夫卡正是以這種虛實對照、以實喻虛的手法,將他所表達的主體事件或中心意念表現得十分強烈,將一般真實推向抽象的、更高的真實。
二、對“荒誕”的藝術觀照
作為人對自然的關系、對社會的關系以及人對自身處境的認識,荒誕體驗一直伴隨著人類的發展。近代以來,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逐步確立和走向成熟,西方人成為物質的奴隸。物質意識的過度膨脹,使得人在巨大的物質成果面前顯得越來越渺小,人與物的關系成為一個悖論,人的荒誕體驗油然而生。而這種體驗從一開始就是現代主義作家關注的焦點。雖歷經20世紀絕大部分時間,在不同時代的作家作品中有著不同的表現形態,但對人的荒誕性的體驗和認識從來都沒有改變過。
無論是對人的荒誕性的理性認識,還是對荒誕的生存處境的感性體驗,卡夫卡都算得上是現代主義作家中第一個全面而又系統地表現荒誕這一主題的人。雖然在卡夫卡小說里很少能找到他對“荒誕”的直接描述,但這并不影響他對荒誕體驗的藝術表達。在卡夫卡看來,荒謬的事情比正經的事情更可信,因為前者是人類生存的普遍境遇。他在給女友密倫娜的信中,表達了自己對荒誕處境的驚訝神情。信中說:“這種欲望有點永恒的猶太人的性質,他們被莫名其妙地拖著、拽著,莫名其妙地流浪在一個莫名其妙的、骯臟的世界上。”{6}而這個世界是由謊言構成的。卡夫卡對這個既黑暗、又充滿謊言的骯臟的世界感到莫名其妙,覺得自己“誤入”了這個世界。他不能適應千百年來世代沿襲的社會習俗,不能和通常的人一樣過一種世俗生活——他拒絕接受這個世界。他的這一態度,在他晚年的自況性小說《饑餓藝術家》中作了曲折的表達:主人公的表演總是得不到滿足,因而他的藝術總是不能達到他夢寐以求的“最高境界”,于是決心拒絕進食,也就是把他的謀生手段——饑餓,變成了抗議手段——絕食。臨終時人們問他為什么不吃東西?他答道:“因為我找不到適合我胃口的食物。”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件他可以接受的、有意義的、能夠賴以生存的東西,所以,他的存在是沒有理由的,是荒謬的。
卡夫卡對“荒誕”所表現出來的驚愕是與他的負罪感密不可分的。在卡夫卡看來,負罪并不是個別現象,而是一種普遍的人的境況,負罪感是卡夫卡作品的一個顯著特征。從某一角度講,長篇小說《審判》就是一部關于負罪感的比喻性作品。其主人公約瑟夫·K作為一個正派的公民,從世俗的法律觀點去看,確實是無罪的。但作為一個在“骯臟的世界”里污染過的一員,他也是“臟”的,只是因為人人都臟,就不覺得自己臟。現在作者來了一個假定性的陌生化手法,突然將他從“人上人”的地位推入“人下人”的地位,讓他的境遇來一個180度的突變,讓他在這樣不可思議的震撼中激發自審意識。當他從“人下人”的地位再來看“人上人”的世界的時候,他覺悟到自己作為銀行經理,即作為“人上人”的時候,確實也曾高高在上地對待過向銀行求助的“人下人”。他意識到自己在國家法庭前固然是無罪的,但在真理或正義法庭前,他卻是有罪的。這就是為什么約瑟夫·K在被“逮捕”之初那樣慷慨激昂地為自己辯護,最后把他處決時,反而無動于衷了。因為有罪與無罪兩相抵消等于無,無即是荒誕。{7}
荒誕在卡夫卡那里不僅是一種思想觀念,也是他的主要藝術特征。卡夫卡的小說具有一個基本特征,這就是整體荒誕而細節真實。所謂整體荒誕,是指作品的中心事件是荒誕的。如《城堡》中的城堡看得見而走不到;《審判》中始終看不見法官;《變形記》中人變蟲;《上了年紀的單身漢勃羅姆費爾德》中兩個乒乓球自動蹦跳等等。在這些作品中,作者使用了一個非凡的藝術手段,卡夫卡打破了情節的邏輯真實,使小說賴以存在的中心事件顯得真假難辨,而其他生活細節和人物的聲音笑貌仍與生活原型基本相符。他的最為人稱道的小說《變形記》除了人變蟲這一神奇事件之外,其他則與一般的現實主義作品并無多大不同。在這里,對事件所作的荒誕變形只不過是假定性手段,目的是為了取得一種間離(陌生化)效果,進而達到作品在整體上的象征或比喻作用。正是出于這樣的原因,卡夫卡才囑咐出版社千萬別在書的封面上畫上那只可憐的蟲!{8}
由于整體荒誕而細節真實,常常造成虛實對照、輕重顛倒的諷刺性藝術效果。如《審判》里的那個法院,在涉及人命關天的重大案件上無人過問,昭示出它沒有法律;而兩個獄卒勒索被告財物這樣一件較小的違紀事件卻被責以重罰,說明這里法律嚴明。《城堡》中城堡對普通百姓的正當要求高高在上,麻木不仁;但一個青年女村民拒絕一個官僚的求婚,立即遭到殘酷的報復,可見其快速反應能力何其敏捷。
一般地講,荒誕作為藝術手段有兩種模式。一是基本情節荒誕不經,而細節卻意外的真實;二是從基本情節到細節處處都顯示出荒誕性。前者在卡夫卡的創作中有典型反映。例如,《城堡》近在咫尺卻始終走不到;《審判》的情節是關于司法審判,而法官卻見不著;《變形記》人變甲蟲。在這些作品中,中心事件喪失了正常的邏輯,顯示出徹底的荒誕性,情節的真實性受到懷疑,而其他的細節則一概符合生活真實。很明顯,卡夫卡小說的這種藝術結構可以使事物的荒誕本質暴露無遺,具有極大的藝術張力。《審判》中的法院似乎法律嚴明,但涉及人命關天的重大案件卻無人過問,說明這里的法律非常混亂。這正是資本主義法律違反人性的本質寫照。而直接繼承了卡夫卡藝術傳統的荒誕派戲劇則充分表現了人與社會、人與自我矛盾對立的荒誕現實。《等待戈多》中弗拉季米爾和愛斯特拉岡日復一日地等待,這里環境雜亂無章,氣氛低迷,人物囈語連篇。從基本情節到細節,在各個環節上都喪失了邏輯的鏈條。這又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信仰危機的警示。
為了充分表達自己“龐大的內心世界”,卡夫卡在藝術上進行了不遺余力的探求。然而,他到死都不滿意,認為自己在藝術上未能成功,因此要把所有作品“付之一炬”。在去世前一個半月,當卡夫卡在病榻上校閱他的《饑餓藝術家》時,他不禁淚流滿面。顯然,他經歷到靈與肉不能兩全的深深的痛苦—— 一種荒誕的感受。卡夫卡帶著強烈的使命感,通過藝術視角的置換,發現并充分表達了現代西方人類對荒誕的社會現實的真切感受,獲得了空前深刻的藝術真實,表現出卓越的藝術技巧,極大地推進了西方小說美學的變革,對20世紀西方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本文系陜西理工學院基金項目《西方文學視野下卡夫卡小說美學研究》的成果
作者簡介:吳金濤,陜西理工學院文學院教授,主要從事西方文學教學與研究。
① 埃利希·海勒.卡夫卡的藝術[J].《文藝研究》,1982,(6).
② 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上)[M].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274.
③ 葉廷芳.現代藝術的探險者[M].花城出版社,1986,162-164.
④ E·繆爾. 弗蘭茲·卡夫卡. 論卡夫卡[M].葉廷芳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52-68.
⑤ 盧卡契.批判現實主義的現實意義[J].《外國文學動態》,1984,(9).
⑥ 卡夫卡.致密倫娜書簡.轉引自葉廷芳.卡夫卡——荒誕文學的始作俑者[J].《文藝理論研究》,1993,(4).
⑦ 葉廷芳.卡夫卡——荒誕文學的始作俑者[J].《文藝理論研究》,1993,(4).
⑧ 卡夫卡.1915年10月25日致沃爾夫出版社.轉引自葉廷芳.卡夫卡——荒誕文學的始作俑者[J].《文藝理論研究》,1993,(4).
(責任編輯:水 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