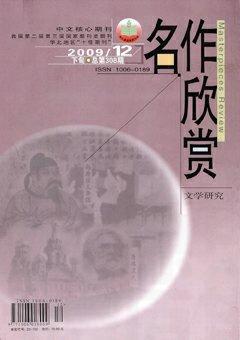迪金森與普拉斯的死亡主題之比較
關鍵詞:迪金森 普拉斯 死亡
摘 要:死亡是人類文學的一個永恒主題。美國文學史上極具傳奇色彩的女詩人迪金森和普拉斯都對這一主題情有獨鐘。本文通過分析兩位女詩人死亡詩歌的創作根源、表現手法和死亡觀之異同來研究她們獨特的審美價值。
艾米莉·迪金森和西爾維亞·普拉斯都是美國文學史上極具神秘色彩的成功女詩人。迪金森被視為與惠特曼并駕齊驅的現代詩歌先驅、美國最偉大的詩人之一;普拉斯則是美國自白派詩人中最富才情、最富詩意的詩人之一,曾獲得美國普利策詩歌獎,被譽為“改變了當代詩歌方向”之人。兩位女詩人有太多的相似之處,本文通過分析兩人死亡詩歌的創作根源、表現手法和死亡觀來解讀她們獨特的審美價值。
一、死亡之源
迪金森出生在美國馬薩諸塞州一個既有文化教養又有社會地位的家庭,自幼受到各方面的良好教育和家庭熏陶。父親是當時著名的律師和社會活動家,母親溫和順從,終日忙于社交而無暇照顧她。母親的失職、父親的嚴肅,父權制社會賦予女性的責任與迪金森對詩歌的追求發生了矛盾,使她不斷地徘徊于女人和女詩人這兩種角色之間。她熱烈而又含蓄地憧憬愛情,卻從未在現實生活中得到愛的結果,愛情的絕望、藝術追求的失意使她隱退到自己的內心世界里,從一個對生活充滿熱情的天真少女變成了一個離群索居的傳奇人物,將孤寂的生命托付于詩,與自己心靈對話,在詩歌的王國里找到了安慰和寄托。迪金森一生體驗了太多的死亡,侄兒的夭折、摯友導師牛頓和沃茲握斯、父母、親友,以及她熱愛的作家的相繼辭世,都給敏感的女詩人帶來無盡的悲傷,生活在一個悲痛的世界里。“我經常想到墳墓,想到它距我有多遠,想到我能否阻止它奪去我的親人。”痛徹心扉的生命體驗使她把自己強烈的情感訴諸筆端,對死亡這個永恒主題進行深刻而不倦的探索。
普拉斯作為德國納粹和猶太人兩極組合的奇特產兒聰慧敏感、性情怪僻,父親的暴躁和獨斷專行讓普拉斯的童年在焦慮和恐懼中渡過。一直是學校的優秀生的她,很早就展露出寫作天賦,8歲父親去世,貧困卻勤奮的她以優異成績考入全美聞名的史密斯女子學院。當時婦女對事業和婚姻的兩難選擇帶給她極大的困惑,任見習編輯時又親眼見到種種人間的虛偽與丑陋,對現實厭惡、絕望、惶恐的她企圖自殺。到精神病院接受治療后赴劍橋學習的普拉斯與英國詩人特德·休斯相遇并結婚,被譽為“天才詩人的結合”,起初兩人美滿和諧,舉案齊眉。孩子誕生后其婚姻因休斯的不忠而破裂,事業家庭中失衡的她一蹶不振更加厭世絕望。1963年寒冬,年僅30歲的普拉斯用煤氣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一生短暫卻經歷了苦澀艱辛,情感豐富、內心痛楚的她找不到生活的目標與希望。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支撐下去的普拉斯認為與其活著掙扎不如回到死亡的救贖中,于是死亡的情緒常常縈繞著她,她的詩歌與死亡不可分割,這在許多詩里得到印證。
從以上的比較中可看出,兩位女詩人的悲劇色彩都較濃,性格均細膩敏感,內心都有對愛情和美好生活的強烈的渴望與向往,都迥然相異于同輩,不容于社會,都欲擺脫男性社會的束縛而苦苦探索,都在矛盾、傷感、絕望和孤獨中守望文學,都是有生之年默默無聞,身后卻名聲大振。痛苦的人生經歷決定著作家觀察世界的角度,人生中的種種不如意,使她們對死亡這一重大主題反復思考、反復吟詠。
二、死亡之美
迪金森一生寫過五六百首關于死亡主題的詩歌。她以深邃的思想和極其豐富的想象對死亡進行了思考和探索,以獨特的視角細膩的筆觸賦予死亡各種各種生動的意象,展現一個神秘而令人震撼的內心世界。她的死亡詩與駭人、冰冷、恐怖無關,洋溢著出其不意的動感和美感。《因為我不能停步等待死亡》被認為是最出色最完美無缺的一首。詩中寫道:“因為我不能等待死亡—— 他體貼地停下來等我—— 馬車只載著我們兩個——/還有永生。”迪金森精心而奇妙地假設一個幸運的起死回生者以回憶在訴說久遠的死亡體驗。詩中迪金森賦予死亡人格化,以風度翩翩、文雅可親的求婚者出現,彬彬有禮邀請她上馬車踏上人生最后的旅程。詩人因死神溫文爾雅的儀態而感染,放下勞作放棄閑暇,共赴死亡之路。經歷了象征著少年、中年和暮年的人生階段的“學校孩子”“麥田”和“夕陽”,最終在陣陣寒意中到達房子前,“仿佛是隆起的地面—— 屋頂勉強可見——/屋檐,低于地面——”,這分明是墓穴,是安息的歸宿。從童年、中年、老年到墳墓是世人無法逃避的命運。死亡是必然的,人類無法控制死亡、支配死亡。詩人認為死亡不是人生的完結,辭別只是暫別人間,人最終駕馭死亡馬車,飛向不朽永恒的天國。迪金森以具體實在的人物把抽象的死亡形象化,使死亡如生活中最真實的一刻,讀者獲身臨其境之感。在常人看來傷感、凄涼、痛徹心扉的死亡在她的筆下沒有顯示出絲毫的痛苦和悲慟,恬淡、平靜、了無遺憾,甚至充滿詩意、浪漫、夢幻,夾雜一絲淡淡的惆悵與夢境般的超然。只有那頻繁的看似隨意使用的破折號,讓人感受到詩人內心難以言狀的激情。《當我死去——我聽見一只蒼蠅叫——》、《那些——正在死去——》等等無不是值得反復品味的佳作。縱觀英美文壇關于死亡主題的作品,或許沒有人像她那樣以纖細、典雅的筆調把戛然而止的死亡寫得那么具有豐富的意象美、飄渺的動感美,并把人的情感和思想融合得如此完美。
迪金森筆下死后的世界也是分外寧靜美麗,猶如她對白色的情有獨鐘, 一生只穿白色衣服的迪金森的世界是透明的、純潔的、獨立的、尊嚴的。《出版是拍賣》是她超越功利的宣言書:“發表,是拍賣/人的心靈……寧愿/從我們閣樓的斗室/一身潔白,去見潔白的上帝——”。她鄙視人世間的錢權交易和虛偽冷漠,寧愿清白地去見上帝也不愿因金錢和虛名去發表她的詩。如同隱居是為了追求心靈的返璞歸真,如勃朗寧夫人筆下著白衣以明志的奧若拉·雷一樣,迪金森穿上白衣以表明自己獻身詩歌藝術的決心。“我說——女人穿上白衣—— 那是莊嚴的事情。”在她看來,白衣是忠于自己的諾言,象征著對真理的求索和對世俗的棄絕,也表明作為一個女人對內心深處某些永遠無法實現欲望的填補。她選擇逃避,遠離名利場的塵囂,極力為自己營造一個與世俗隔絕的純凈空間。在她的葬禮上,她身著白色衣裙,躺在白色的靈柩里,眉宇間透著一股說不出的安詳。她就這樣結束了她平淡而又不俗的一生,從容地走向天國的樂園。在她彌留之際,只留下一個“歸”字,可見她這一生的執著與守候終究尋得心靈的歸宿。
死亡也是普拉斯詩歌的重要主題,詩人對死亡的強烈沖動為詩歌增添了震懾力,加之自身幾次自殺的親身體驗,使普拉斯在描寫這一主題更顯得得心應手。她將死視為一門藝術,并將之付諸實踐。詩集《愛儷爾》猶如死亡日記,以純粹的死亡帶給讀者強烈的震動。詩歌描繪出種種的死亡畫面和姿態。如《圖騰》中寫道,“我是瘋子/蜘蛛揮舞它眾多的手臂高喊”,蒼蠅們“在無限的網中/像藍色的孩子嗡嗡叫/終于被死亡/用許多枝條捆住”。詩人用發自內心的吶喊寫出對死亡的認知。世界彌漫著恐怖的死亡,所有的生命像小小蒼蠅一樣毫無反抗能力,都將被一只巨大的蜘蛛所吞噬。在死神的強大力量下,生命如此脆弱微小,死神以不同方式將生命可以無情剝奪。《邊緣》中“那女人已完美/她的尸體掛著成功的微笑……她的光腳仿佛在說:我們已經走了這么遠/到頭了”。“女人”走完人生的旅程,擺脫生活的壓力和束縛,死亡意味著她生命的終結,也是人生的完美,只有死亡才是她最美好的歸宿。這也是普拉斯自己的死亡觀。獨特的個性、獨特的生活經歷不僅使她生活在種種矛盾痛苦對抗中,也帶給她創作的激情和靈感,促使她形成獨特的詩歌風格。與迪金森的含蓄內斂不同,她用第一人稱寫作,采取一種所謂“自白”的形式,淋漓盡致地把人們羞于啟齒的心靈陰暗面:醫院、殘缺的肢體、骯臟的角落、恐怖的病房、破碎的玻璃……貌似恐怖的畫面皆引入詩內。普拉斯的詩通過變化多樣的意象和直白坦率、無所顧忌的語言,帶給讀者心靈深處一種震撼力。她利用詩摧毀現實生活中的存在,釋放著被人們視為非理性的瘋狂話語,對死亡的迷戀和痛苦直言不諱,帶給人真切的感受,把自我揭露式的自白詩的美學特征推向極致。
與迪金森迥然不同的是,普拉斯用黑色作為藝術底色。生活的壓抑、孤獨和痛苦使她的詩中充斥著各種各樣黑色的意象。她用生命寫詩,用黑色描述死亡藝術。她的詩中到處流露出她生存和死亡的感受,揭示她內心世界本能和情感的沖突。如《黑莓》、《雨中的黑鴉》、《橙光中的黑松樹》許多詩的主題都與黑色有關。黑色的意象也比比皆是,如“黑色的鞋子”;“從中擊破的黑人”;“黑色的電話線斷了”;“你肥胖的黑心里藏有一把利刃”,“黑湖,黑船,兩個黑紙剪出的人。/在這里飲水的黑樹往那里去?他們的黑影想必一直伸到加拿大。”黑色抽象延伸為一種異化、神秘、失望、怨恨等,表現詩人希望的破滅和痛苦。普拉斯曾說,“我的詩是我的感覺和情緒的真實流露”。她以女性體驗為出發點,通過詩歌形式以獨特的視角、敏銳的意象、大膽的寫作手法控訴男權社會對女性造成的束縛、壓迫與傷害。無邊的陰冷與黑暗真實地彰顯了她的悲傷、仇恨、顫栗、痛苦和絕望,癡迷于悲劇角色,探索死亡主題,以“非存在”證明存在,存在正在走向虛無,這成為她“自白詩”的基調,她以“輝煌的痛苦與神圣的嚎叫”立于自白派詩歌的藝術峰巔。
三、死亡之思
迪金森和普拉斯都是性格內向、坦誠真實而聰慧敏感的女詩人,她們站在男性社會統治的詩歌舞臺上,呼喊出對生命的愛和恨,對死亡的向往和思索。表面上看,生與死二者存在著極端對立的矛盾,事實上,生與死是生命的不可分割的兩部分。兩位詩人對死亡這一神秘的世界進行了深入的感性探索過程,是對人生和生命進行探求的曲折而痛苦的心路歷程,是對人生價值不盡的追尋過程。迪金森毫不回避對死亡的沉湎,她認識到生與死是一種循環過程,并以她自己的方式將死亡之謎展示在人們面前。對死亡的質疑、對死后世界的猜測及美好的愿望,都在她的詩歌中得到充分的體現。在她筆下,死亡有了自己的特點和個性,而不是一個可怕的惡魔;在她眼中,死亡是一個事實,而不是一種狀態。死亡不用再被一味否定、逃避,而用于思考和面對。她不僅平靜勇敢地直面死亡,甚至贊美死亡。通過對死亡及永生的反復思考及質疑后,找出了對生命思考的新視角,進而揭示出生命的真諦。普拉斯在痛苦無助的黑暗世界里也專注于死亡主題,在詩中歌吟死亡,“我又做了一次/每十年當中/我要安排此事”;“死去是一種藝術,和其他事情一樣,我尤善此道”。在普拉斯眼中,死亡并不意味著生命的結束,而是逃避現實和脫胎再生的契機。當陷入絕望和痛苦時,她從自殺的想法中獲得慰藉,從死而復生的真切感受中獲得快感和超然。醉心于死亡、對死亡淋漓盡致的描述使她對死亡充滿依戀,最終她迎著死神召喚而去來的結束自己內心的折磨。普拉斯以女性少有的勇氣和真誠大膽地宣布自己對死亡的看法,并最終以自身的行動闡釋了她對藝術的追求。不論生存多么有限,死亡使她們的靈魂擺脫肉體的束縛,從而達到最純潔最完美的狀態。
由此可見,兩位情感豐富內心痛楚的女詩人,一生處于矛盾糾纏之中,都痛恨這個男權社會統治的感性世界,無力去摧毀它,只有寄情于詩歌世界,寄希望于死亡的永生以達到最純潔最美好的自由境界。死亡乃是最深刻最富意蘊的生命真實,唯有死亡才能賦予人生意義和真正深度。不朽和永恒的生命只有通過死亡才能達到。她們的詩作在有生之年不得以“生”,而在謝世之后卻得以永生。為“生”而“死”,最終換來了自己永恒的藝術生命。
四、結 語
聰慧敏感、命運坎坷的女詩人一直苦苦思索女性自身及人類生命的種種問題。或寧靜、或激情、或沉默、或吶喊,字里行間蘊含著她們內心深處對甜美、溫暖和愛情的向往和對女性自由獨立人生的渴望與追求。她們都是男權社會的犧牲品,也是女權運動的先驅。通過對她們的人生及詩歌獨特的死亡之美的研究,我們加深了對她們獨特生命觀的了解,女詩人的死亡詩及其死亡意識已經超越了死亡本身,更多的是表現了詩人對生命意義深刻而又積極的思考。
本文系山西省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課題基金
作者簡介:楊曉麗,碩士,太原科技大學外語系講師,研究方向為英美文學與英語教學。
參考文獻:
[1]Thomas H. Johnson. The Letters of Emily Dickinson [M]. Cambridge. Mass:Harward University Press,1958:197 -198.
[2]艾米莉· 狄更生詩選[M].江楓譯.長沙: 湖南文藝出版社, 1996.
[3]A. Alvarez, Sylvia Plath, Review [J].9 October, 1963.
[4]Bassnett, Susan. Sylvia Plath[M].London: Mac Milan Education Ltd, 1987.
(責任編輯:水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