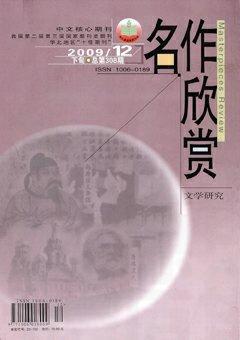《百合花》中“我”的形象分析
關鍵詞:《百合花》 同故事敘述
摘 要:茹志鵑的《百合花》小說寫了一個男人與兩個女人之間的故事。本文試從女性形象分析的角度進入文本,借助“同故事敘述”細讀文本發現作品中“我”的雙性色彩。
茹志鵑的《百合花》小說寫了一個男人與兩個女人之間的故事。但沒有演繹也不可能演繹成《青春之歌》的模式。“十七年”,是男性話語中心的時代,女性被邊緣化,甚至缺失。但是并不意味著作家放棄對女性的追問和求索。很多人簡單地將《百合花》中的“我”用“母性”和“妻性”來概括,我覺得是不準確的。本文試從女性形象分析的角度進入文本,做深層次解讀。
同故事敘述(homodiegetic),是西方經典敘事學理論的一個概念,是指敘述者與人物處于同一個層面,就是故事里的一個人物。“若第一人稱敘述者聚焦于自己的個人經歷,則構成‘自身故事(autodiegetic)的敘述,這是‘同故事敘述中的一種。”①顯然《百合花》是同故事敘事,準確地說應該是“同故事+故事內”敘事②。“我”既是敘事者,同時也是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女性人物,可是相對新媳婦來說,“我”的女性色彩不夠濃郁。作者自己也承認“要讓‘我對通訊員建立起一種比同志、比同鄉更為親切的感情。但它又不是一見鐘情的男女間的愛情。‘我帶著類似手足之情,帶著一種女同志特有的母性來看待他、牽掛他”③。這是作者作為一個女性對年輕戰士尚未獲得愛情的特殊同情,是母性的憐憫。但是細讀文本,就會發現,這種母性的釋放,其實借助了父性的外殼。
一、母性的光輝
戰爭的背景下,女性性別被壓抑著,但是無法阻擋母性——女人最基本的情感的釋放。“我”雖然已經不是“五四”時期的子君——“我是我的”,這么一個典型的女性形象,但至少是一個準女性。
在去包扎所的路上,“我”看到的是被雨水沖洗得青翠水綠的秋莊稼,嗅到的是清鮮濕潤的香味,要不是敵人的冷炮,“我”真以為是去趕集。這是一雙女性的眼睛在審視戰爭背景下的風景,甚至連通訊員步槍筒里幾根稀稀疏疏的樹枝都是裝飾點綴。一路上,青澀的通訊員,對于性別差異的羞澀,和“我”保持了沒有言語的默契。既不把“我”甩得很遠,又不讓“我”靠近,使本來有些生氣的“我”,不禁對他發生了興趣。“我”身上的女性被青澀的通訊員喚醒了,當然這種女性是以母性的面目釋放的。在“我”的眼中,通訊員是幼小的,是需要保護的,是需要憐愛的,雖然一路上都是通訊員在保護“我”。“我”的這種保護心理的蘇醒,使“我”不斷地走近通訊員,關心“我”的小同鄉,興趣竟然慢慢地升騰為親熱。
“他已走遠了,但還見他肩上撕掛下來的布片,在風里一飄一飄。我真后悔沒給他縫上再走。現在,至少他要裸露一晚上的肩膀了。”這是一個母親目送兒子離開的心情,這是母親看到孩子衣服破了而沒有來得及縫補的一絲自責。
“但是我又莫名其妙地想問問誰,戰地上會不會漏掉傷員。通訊員在戰斗時,除了送信,還干什么,——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要問這些沒意思的問題。”這哪里是沒有意思的問題呢?這分明是一個母親對戰斗中孩子命運的擔憂和牽掛。在看到一個通訊員被抬了下來,“打了個寒戰,心跳起來”,以為是自己的小同鄉,發現不是后,才稍微鎮定下來。可是血、垂危的生命再次喚醒了她隱匿的母性情懷。
“……我猛然醒悟地跳起身,磕磕絆絆地跑去找醫生……我想推開這沉重的氛圍,我想看見他坐起來,看見他羞澀地笑……”這里,母性沖破了戰士性別的束縛。白天還給自己開飯的小通訊員,孩子般的小同鄉,就這樣犧牲了,“孩子”的死,強烈地刺激了“我”的心,母性釋放到了極致,以致“猛然跳起身,磕磕絆絆”。
二、父性的外殼
劉再復提出性格的二重組合論,認為“性格的二重組合,就是兩極的排列組合”④。“我”的性格中既有母性的柔,也有作為戰士的剛。性格是二重的組合,性別也可以是二重的組合。“十七年”文學,應該有三種性別:戰士(另一種形式的男性)、男性和隱藏的女性。文本中的“我”,在性別的呈現中,時常表現出和女性、母性相反的一面,姑且稱之為“父性”。
“大概因為我是個女同志吧!團長對我抓了半天后腦勺,最后才叫一個通訊員送我到前沿包扎所去。”文中的“我”從一開始就認可了自己的女性身份。但是我們在發現她是個女性的同時,我們也會發現,作為男性話語中心的團長竟然會對一個女同志沒有辦法,抓了半天后腦勺。從某種意義上說,團長意識到她是一名戰士的同時她又是一名女性,意識到了男女性別的差異,所以沒辦法像指揮通訊員那樣指揮“我”,所以陷入了窘境,失語了。我們也可以理解為男女性別差異對男性中心話語地位的一次挑戰。“我”的反應也很奇特:“包扎所就包扎所吧!反正不叫我進保險箱就行。我背上背包,跟通訊員走了。”
這里的“我”并沒有遭遇性別差異帶來的窘境,堅定認可一個戰士的身份和性別,是戰士怎么能貪生怕死呢?“我”在不自覺中性別發生了移位,女性性別隱匿到戰士性別之下。或者說“我”對自己女性身份的認可是建立在對戰士身份的認可之上的,女性不過是戰士的附庸。
在去包扎所的路上,通訊員是保護者,“我”是被保護者。起初的節奏是通訊員定下的,“我”在后面緊緊地追趕,但是很快,“我”取代通訊員成為節奏的控制者,引導者,通訊員成了從屬者。“我”走快,“他在前面大踏步向前”,“我”走慢,“他在前面就搖搖擺擺”。顯然,在“我”和通訊員的二元世界里,“我”是占據優勢的。某個層面上可以說,在路上,“我”充當了通訊員的長輩,不,是首長這樣的父親角色。
“我”和通訊員在休息間隙的談話,本來想驅散尷尬、拉近距離,結果造成了更深的尷尬。甚至連“我”自己都覺得是在審訊。我想審訊未必夠得上,但這像極了革命電影中,首長拉著戰士的手,父親般的看著戰士,慈祥地、親切地詢問著,而小戰士感到了首長的關懷而內心激動。文中的“我”不自覺地在充當那樣一個首長,散發出父性的光輝。可是,不但沒有讓通訊員安靜放松下來,反而更加局促不安,“兩只手不停地數摸著腰皮帶上的扣眼”,大汗淋漓。顯然,通訊員對“我”的這種以女性身份充當父性角色的做法,無法接受。這或許給我們解釋當“我”讓他回團部時,“他精神頓時活潑起來了”提供一個新的思路。
“一個上了年紀的擔架員,大概把我當做醫生了,一把抓住我的膀子說:‘大夫,你可無論如何要想辦法治好這位同志呀!你治好他,我……我們全體擔架隊員給你掛匾!……”擔架隊員如此虔誠地懇求我,并不是因為我是一個女性,而是把我當成了一個醫生。醫生于他們來說,是唯一的依靠和希望。這里,“我”的女性身份早已不重要。
此外,我們還注意到,“我”對通訊員的稱呼雖然帶上了具有母性色彩的“小”的稱呼,如小伙、小同鄉、小通訊員等,但是這種稱呼還是建立在同志、戰士基礎上的。是莊嚴的外殼下親切的憐愛。
不管怎么說,“我”身上的母性被喚醒,但是這種母性呈現在讀者面前時,卻是披上了父性的外衣。
筆者以為,“我”這個準女性形象,本就是在“十七年”那個時代被政治壓抑而成的畸形女性形象。并且這個形象是貫穿于文本始終的,是政治在文本中的投影。
作者簡介:吳延生,淮陰工學院人文學院副教授。
{1} 趙一凡,張中載,李德恩.西方文論關鍵詞[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742.
{2} 陳順馨.中國當代文學的敘事與性別[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10.
{3} 茹志鵑.我寫《百合花》的經過[A].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茹志鵑研究專集[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42
{4} 劉再復.性格組合論[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60.
(責任編輯:呂曉東)